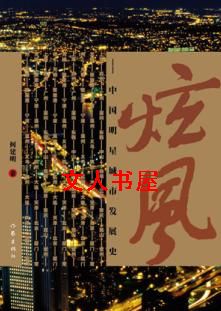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第7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太气傲。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其金黄|色的丰富并不表示春季纯洁的无知,也不表示夏季强盛的威力,而是表示老年的成熟与蔼然可亲的智慧。生活的秋季,知道生命上的极限而感到满足。因为知道生命上的极限,在丰富的经验之下,才有色调儿的调谐,其丰富永不可及,其绿色表示生命与力量,其橘色表示金黄的满足,其紫色表示顺天知命与死亡。月光照上秋日的林木,其容貌枯白而沉思;落日的余晖照上初秋的林木,还开怀而欢笑。清晨山间的微风扫过,使颤动的树叶轻松愉快的飘落于大地,无人确知落叶之歌,究竟是欢笑的歌声,还是离别的眼泪。因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所以有宁静,有智慧,有成熟的精神,向忧愁微笑,向欢乐爽快的微风赞美。
人事
曾深伶
她从部队复员分到某高校人事处工作时,还不太懂“人事”。
她第一次知道有“人事”部门。
领导找她谈话,说看过她的档案,认为她符合人事干部的条件:根红苗正,党员,为人正派,原则性纪律性强。于是她自我感觉良好,按时到办公大楼二层挂着“人事处”牌子的房间里上班了。
后来她才清楚,人竟有这么多复杂的事体要别人来管的。结婚要证明,孩子升学要家长鉴定,毕业分配联系单位,招工招干要指标,职称评定要考核,升涨工资要报表,病假事假要登记,退休要安置,甚至丧葬也归人事处理,于是她忙得不可开交。
人们介绍她时,总是说:“这是人事处的小党同志。”她在学院的各部门办事很顺利。对这些顺利她没有去细想,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
她第一次处理人的丧事,心里很悲哀,陪着家属淌了不少眼泪,同情那些遭到不幸的人们。领导对她说,人事工作要讲政策原则,不能感情用事,她便收回了眼泪和同情。
她经常和各级领导们讨论各种“人事”问题。到省级机关开会坐小车,到外地开会坐飞机。
她进步很快,已经负责处理某一方面的工作。她开始感到人们与她交往时的恭敬。她认为这是人们对她能力的肯定,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恭敬。在不知不觉中,她和下级部门的人谈话,越来越多地使用“研究研究,讨论讨论”之类的语言。
与人碰面时,常常挂着矜持的微笑。人们对她也报以微笑,但她有时却读不懂某些微笑的真实含意。
有一次,她到A同志家谈点人事。看到A家有一盆开得很美的“仙客来”。她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花,非常惊喜地赞叹:“这是什么花呀!开得这么美!”第二天,她在家门口看到了这盆花。惊奇之余,她感到有点不安。自己不过是为花的美丽所动,别无他意呀!又觉得这不过是一盆花,就留下了。
又有一次,她到一位女同志家聊家常。看到食品橱里有一种新制调料,便问起调料的味道、价钱。女主人拿起调料塞在她手里,她说自己去买,却怎么也推脱不了手里那包调料,只好收下。心里感到有点不是味,自己不过随便问问,倒像是……又有一次,又有一次……这样的尴尬事竟多起来。她开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被人所强的委屈,一种无法解释的难堪。以后到了别人家里,她再不敢轻易地表露自己的赞美和好奇。后来,看到那些非常美好的事物,赞美的话已到了嘴边,却又在不自觉中被咽了下去。她到别人家去得也少了。
渐渐地,她变得谨慎、严肃、不苟言笑,有时甚至有点“铁石心肠”。她感到人们对她恭敬中的疏远,她感到与人之间隔着一堵难以触摸的墙。
她先后谈了几个对象,都在莫名其妙中告吹。后来有人告诉她,她那副毫不动情的“人事”面孔和习惯了的政策语调,使男士们畏而止步。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心中的热情表现不出来。她有点无可奈何。
慢慢地,她发现了领导之间的微妙关系,发现了各领导与各下属之间的亲疏好恶。她不自觉地学会了察颜观色,小心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选择自己的落脚点,唯恐稍有不慎落入某种解不开的索扣中。她开始感到自己活得很辛苦。年龄不大,却开始出现丝丝白发。看到一些老教授年近古稀却有一头一丝不染的黑发时,她开始怜悯自己了。
她终于在一场不明不白的关系争斗中,被归属于败落的一派,从高空中跌落下来。开始时,她愤怒、气恼、委屈、沮丧,不仅仅为了所谓的仕途前程的挫折,更为了自己价值的失落,还为了四周射来的异样的目光。一次路遇A同志,她像往常那样,露出一个友好的微笑,却被对方那似乎毫不相识的冷漠撞了回来。那个破碎了的笑容挂在她脸上足足一分钟后又落到了她心里,成了几瓣酸涩苦辛的碎果。别人也开始对她说这些“研究研究”、“讨论讨论”的话了。她思来想去,终于悟出了“人事”的真谛。她以往的价值,并不在于她自身的能力德行,而在于那块“人事”的牌子,那间充满政策气味的办公室和她在那个房间里的那把椅子。一旦她离开了那块挂着牌子的房间里的椅子,她的价值在人们眼里也就降格得像是清仓处理的廉价物品了。明白了这些,想起老教授头上的黑发,她倒有了一种解脱感,感到一身的轻松。
她又开始到各位同事家串门了,并且由衷地放心地坦率地尽情地去赞美那些美好的事物。她开始放松地和人谈自己的感受,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穿上牛仔裤,戴上耳环,蓄起长发,淡淡地化了妆,自如地转着乎拉圈,潇潇洒洒地走在大街上,自然真诚的微笑常伴着她。虽然她已不太年轻,回头率却在增加。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开心。
她用逝去的年华做代价,懂得了一些人事,懂得了自己真正的价值。她决心重新赢得人们的微笑,那定会是一种她完全读得懂的微笑。
人是唯一会笑的动物
《羊城晚报》
秦牧
()
即使我们的岁月里有晦冥风雨,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笑声。
笑声除了表达欢乐外,有时也抒发愤怒、轻蔑、会心的理解、无声的批判……西方有一句谚语说:“人是唯一会笑的动物。”
此语不虚。
好些动物都会流泪,但人类以外的所有动物都不会笑,甚至人类的近亲猩猩,远亲猴子,有“海洋中的人类”之称的海豚,都概莫能属。
鹦鹉、八哥能够模仿人类的笑声,但是它们的笑徒有形式并无内容,它们仅仅是模仿而已。澳洲的“笑鸟”声音酷似人的笑声,但那仅仅是“像煞”而已,也不是真笑。
人既然天赋予笑这种机能,总得不时发挥一下才好。
这儿写下几则笑的小品,聊以锻炼自己的这种机能,以免面部肌肉绷得过紧,丧失天赋。
两刀相割“两刀相割”,钢质差的刀立刻崩口。理论的交锋也然,这种交锋不一定在讲坛上、会议中,有时也在日常生活里面。
听到北方有位作者说,他看到两个三轮车工人吵架,一个说:“我是你爸爸。
“另一个说:“我是你爸爸,×你妈的。”语言贫乏,吵来吵去都是这句话,无非是要抢占高地,争做对方的父亲。
忽然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一个旁观者上前说:“两位爷爷不要吵了,我是小孙子,这样,你们不是都比做爸爸更高一辈么?”周围的人听了哄堂大笑,两个争当对方父亲的人也不期然停止争吵了。
又一幕是我前些年在火车里见到的:餐车客挤,一对中年夫妇在等待一对青年夫妇进餐完毕,好候补入座。中年男子劝告他的妻子:“不用急,快完了。”不料“快完了”一语,触犯了青年男子,他作色道:“什么‘快完了’!”竟气得饭也不扒啦。中年男子略一错愕,省悟过来,立刻陪着笑脸说:“您不会完,您永远不会完。”也是引起周围的人大笑,那青年男子也争吵不下去了。
有时一点旷达,一点洒脱,竟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相信一句极平常的话寓有神奇魔力的,和不相信那一套玩意的,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在这儿交了锋,采用的是平凡不过的日常生活对话的形式。正像涂上玻璃粉的两根风筝线在天空互割,坚韧锐利的一根把对方锯断,使它突然倒栽下来一样。
谦让平心而论,我并不爱唠叨,我知道沉默的价值,简洁的妙处。但形势比人还强,事与愿违,环境常常迫我做个唠叨的人,例如:有个老掉了牙的故事,我就讲了十多次。
那天就是这样,我去一个文物部门参观,主人,还有陪客张三、李四、郑五、王六,礼貌甚周,虽说“礼多人不怪”,却也令你规行矩步,如坐针毯。
在参观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热情招呼,简直叫你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在上楼梯的时候,穿门进室的时候,情况着实使人狼狈,大群的人一到这个关口,突然停步,好像碰上大风雪都冻结了。
“请,请。”张三说。李四说:“您先,您先。”郑五伸出巨灵掌,把我一顶而上。我正要表示一点礼数教养,退下一步,不想王六又以老鹰擒鸡的姿态,从旁一手把我提了上去。天热人倦,周旋维艰,只好遵命。一次这样,两次这样,三次又是这样,因此,使我视门口为喂途,望楼梯而神慑。
上半场参观完毕,他们要我发表感想,我说:“什么都好,但是我想讲个故事。”他们说:“请,请。”于是我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从前,某地有个妇女怀了孕,那是个怪胎,十几年都没有生下,大腹便便,见者俱惊。医生终于为她开了刀。一剖腹,秘密揭穿了:原来那是双胞胎,兄弟俩,极尽人间谦让之能事。在‘大门’口彼此施礼,这个说:‘请,请。’那个说:‘你先,你先。’相持多年,胡子都长出来了。还有个补充材料,说他们是穿燕尾礼服的,但也有说是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的。”讲毕,我们大家都笑,不过,那不是开怀大笑,而是缺了点水分的干笑,下半场的参观,情形可就好些了。
这故事是老掉了牙的。可在人生旅途上,我大概还得再讲它一百次。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是个封建习气仍很浓厚,相当讲究身份等级的礼教之邦呢!
幽默制造家有些人不解幽默,但却是制造幽默的能手。
说笑话的人要自己不笑,能逗人笑方显棋高一着,有些不解幽默而能制造幽默的人在这一点上得分奇高。
在某个集会上我对这样的人物初次“识荆”。
那是在一个筵席上吧!大家谈到北京月饼之坚硬,有人说咬不下,有人说会咬崩牙齿。又有人讲了一个笑话:“某次,有个顾客买了一盒京式月饼,过马路时因闪避车辆坠落路心,车辆驶过,这人回头一望,月饼并没有辗烂,而是陷进路面去了,刚巧有人拿着铁撬经过,借来一挖,月饼弹回地面。”
这当然只是个笑话,讲罢,众人都笑。但是,有一个听者不笑,而是蹙额沉思,接着,怒形于色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月饼会那么硬,这还得了?这合乎科学吗?京式月饼店不是得统统关门了?嘿嘿,而且,故事讲的不是广式月饼,苏式月饼,偏偏是京式月饼,把这样的故事硬栽在北京头上,这又是什么意思?嘿嘿,这不是很有地方主义色彩吗?北京是什么地方?是首都!我们的首都真是那么糟糕吗?连一盒像样的月饼都制造不出来,还讲什么别的事情!这在影射什么?什么都离不开政治。这样的故事也是很有政治性的。我们不能伤风感冒,不可嗅觉不灵。这样的故事背后是有一定寓意的。就是不说这些吧,单从它的反现实、反科学而言,这样的故事就很有毒素…”讲故事的人瞠目结舌,只好苦笑解释道:“这只是个笑话,你听过形容武汉夏天炎热程度的那个笑话吗?一个武汉人死后,阎罗王要罚他下油锅,他哈哈大笑说:‘下吧下吧,我是武汉来的,还怕下油锅?’这又应作何解呢?”
批评者立刻慷慨激昂道:“这是导人迷信的故事!阴间有什么阎罗王?而且,这对武汉人够尊重吗?他们那里夏天天气热,他们就不怕下油锅?油的沸点是好几百度,武汉最热也不过是40度左右吧?根本就是不合理的故事结构……”正在评论家发表滔滔谠论的时候,我环视席上各人的表情,忽地都变得非常奇特。
我突然想起一个谜底为“厕所”的灯谜,谜面是几句韵文:“远看像座庙,近看不是庙,一个老翁在数当票,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在美味纷呈的宴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