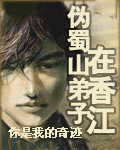香江边上的思考-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起初,英国人反对创办中文大学,并通过对财政和学位的控制,压制中文教育的发展。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推广传统儒学教育可将香港人与内地意识形态隔离开来,使其成为抵制内地的文化武器。由此,港英政府转变立场,推动新亚、崇基、联合等书院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正式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其目的当然不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为了控制中文教育。当初,在钱穆坚持下,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被翻译为“香港中文大学”,其实质是要通过汉语语言来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港英政府的操纵下,中文大学根本无力承担通过中文复兴中国文明的使命。也许是这个原因,中大成立两年之后,钱穆辞去了文学院院长职务,郁郁赴台。
中大的悲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儒家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试图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脉络中发展儒学,实现儒学与世界接轨,从而试图在香港保留并传播儒家文化,但他们忽略了儒学的根本在于中文,由此在港英政府推行英文主导的殖民教育面前失去了批判力,反而成为港英政府用来抵制内地政治的文化工具。由此,新儒学从第二期到第三期,基本上被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所蒙蔽,丧失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对立的根本问题,更忽略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文明冲突。新儒家知识分子在香港精英阶层中培养儒学教育的努力失败了,但香港中文教育却在左派基层爱国学校得到了迅速的推广。香港年轻一代大学生对香港殖民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掀起了“认识祖国,关心社会”的运动,无论是认同内地政治的“国粹派”,还是对内地政治采取批判立场的“社会派”,都强化了香港社会的中文认同,并推动了“法定中文语言”的运动,迫使港英政府将中文与英文并列为官方语言。这就构成了香港回归之前文化斗争的基本格局。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请您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名园。……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是法国作家雨果笔下的圆明园,它延续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启蒙知识分子对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向往。西方文明在其他殖民地所向披靡,唯在中国受到强烈抵制,因为中国文明的辉煌程度并不亚于西方,某些方面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因此,高扬西方文明同时贬低中国文明,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主题,也成为大英帝国所要担负的文明使命。创办殖民地大学来传播西方文明无疑属于大英帝国公开的政治教诲。然而,就帝国的使命而言,除了这些公开教诲,我相信还有一些不可以公开的政治教诲。比如说,香港会(Hong Kong Club)和马会等曾在香港政治中发挥怎样的功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九龙城寨也是另外一个秘密。就在创办香港大学时期,英军自动撤出九龙城,将其变成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地方。此时内地忙于革命,没有一个政府真正管理过九龙城,整个城寨一直保持着清王朝招牌和传统风俗,由此成为传统中国活的标本。由于九龙城寨属于“三不管”地带,自然被黑社会所把持,很快成为色情、赌博和毒品的聚集地,一切与人类美好追求相背离的东西都聚集到这里。于是,香港社会自然形成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就是港大、中大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类文明最高成就和价值追求,另一个就是九龙城寨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类文明中最堕落的内容。而在这种生活方式的背后,不言而喻隐含着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强烈对比。香港华人究竟应当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哪一种文明,选择哪一种文愚公移山化认同,在港英政府提供的两个活生生的文明标本面前一清二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儒家复兴的儒学远离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只能变成港大、中大以及英国和美国的英文大学中的文化点缀。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大英帝国对香港的治理从军事与经济手段转向经济与文化手段,其核心就是通过文明征服来培养“小英国人”实行“间接统治”。从文明征服的效果看,九龙城寨发挥着不亚于香港大学的作用。
政治的力量在于文明,文明的力量在于人心。人心的培育才是政治最高的艺术。华人政治家李光耀就颇得英国人的政治真传。当香港中文复兴运动以广东话为母语、以繁体字为标准中文时,李光耀在新加坡成功地推广了普通话和简体字,因为他的眼光已掠过历史投向了中国文明遥远的未来。我没有去过新加坡,听说新加坡有一座风景独特的印度城,这突然让我想起了香港的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史话》,鲁金著,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版;《香港教育透视》,一九八二年刊于香港《广角镜》)
主权:政治的智慧与意志——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六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4期
一九七七年,被港督任命为“经济多元化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立法局议员罗德丞开始思考关于香港地区前途的方案,因为对新界土地的开发涉及租约,他设想港府把新界土地租约续签到“九七”之后,造成英国继续租借的既成事实,继续保持英国对香港的殖民。无论是不是与这个方案有关,两年后麦理浩访京确实提出了续签租约问题。这立即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他当即表示中国届时会收回香港。为此,他责令中央尽快组织力量研究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准备用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叶九条”就发展为中央对港方针的“十二条”,“一国两制”的思想也由此形成。
当时,中国的国际战略着眼于联合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抗苏联霸权,以便减轻北方大陆边境的军事压力,从南方发起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由于中美关系缓和,邓小平借机提出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还不在当时的决策视野中。然而,英国人提出续签新界土地租约,迫使他提前思考香港问题,把解决香港问题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范例。这种决策的转变加速了香港问题的提前解决,无疑不利于英国人,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从土地租约问题入手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假如按照“澳门模式”可能又是另一种情形。
其实,英国人当时选择在租约这个法律细节上偷步,是幻想着继续维持殖民统治。这种思路由于一九七九年撒切尔夫人的上台进一步强化。
其时,冷战格局发生了有利于英美的转变: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了全球抗议,中越战争和邓小平访美,使得“铁三角”不利于苏联;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则推行自由政策重振资本主义经济;军事上里根抛出“星球大战计划”力图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而撒切尔夫人则通过马岛战役来重振大英帝国的雄风。然而,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遭到唾弃的时代里,撒切尔夫人必须为战争寻找新的理由:
福纳克(即马岛——引者)的人民和英国的人民一样,是海岛民族……他们人数不多,但一样有权利过和平的日子,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决定他们想要效忠的国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英国式的,它们的效忠对象是英国皇室。我们要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的这些权利,这是英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女王陛下政府的责任。(《戴卓尔夫人回忆录》(上),122页)
撒切尔夫人在议会中的这段演说的理论基础就是《联合国宪章》中所肯定的“民族自觉”理论。这既是威尔逊的原则,也是列宁的原则。威尔逊和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强调受殖民地统治的民族从殖民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可实际上,威尔逊希望的是这些殖民地从西班牙、英、法、德这些老牌殖民主义者中解放出来,然后纳入到美国的保护体系中,比如拉美、东南亚就是如此。而俄国则把基于民族自决理论从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中独立出来的中亚诸国直接并入到苏联。撒切尔夫人再次启用民族自决理论,不过是为了改变大英帝国从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惨败以来似乎已注定日渐式微的命运,使英国重新获得信心。正如撒切尔夫人在胜利后所言:“我们不再是个日薄西山的国家。我们已重新寻回自信……绝对不要把这场胜利解释为回光返照,决不是这样——我们感到愉悦的是,英国已经重燃过去世世代代的耀眼光芒,而且近日的荣光绝不比过去逊色。英国已在南大西洋重寻自我定位,而从今以后,只有更加奋步向前,保持这份荣耀。”(同上,172页)正是带着这份自信和傲慢,撒切尔夫人踏上了中国的旅程。
和马岛一样,英国人在香港地区问题上也有一张政治牌,这要归功于麦理浩治港十多年的成就,香港精英阶层已认同了英国统治,开始抗拒回归。但英国政府很清楚,这张牌在香港无效,因为它没有实力与中国开战。
不过,和马岛不同,英国人多了另外两张牌:三个国际条约的法理牌和香港地区已成了“生金蛋的鸡”的经济牌。于是,一九八二年九月,撒切尔夫人在与邓小平就香港前途会谈中,一开始就提出了香港的繁荣问题,认为香港繁荣系于香港人对前途的信心,而繁荣和信心系于英国的继续统治,中英双方只有在香港未来治权上达成协议,才能讨论主权问题。表面上看,撒切尔夫人打的是经济牌,但其背后却隐含着法理牌,即主张三个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英国人合法地拥有对香港的主权,由此也拥有合法的治权,谈判的主题只能是“九七”之后新界的主权归属问题。由此,通过香港繁荣这个中国政府极其关心的问题,撒切尔夫人在主权与治权问题上建立了内在的逻辑关系,并为后来所谓的“主权换治权”的谈判思路做好了铺垫。
对于撒切尔夫人的到来,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的准备。邓小平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对这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来说,马岛之战根本就算不上战争,大英帝国在马岛的胜利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他要面对的不是与英国人的军事较量,而是政治较量。这场被誉为是“铁娘子”与“钢汉子”的谈判往往被看做是主权意志的较量,但在我看来,这更多是政治智慧的较量,是话语主导权的较量。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形势,能够对整体态势做出理性判断和审慎把握无疑是政治家的第一美德,然而,如何能在这复杂形势中把握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话语,从而把握话语的主导权,把政治实力建立在正义或正当性之上,对政治家而言无疑是最高的境界。政治的基础无疑是实力或者综合国力,且军事实力是决定性的手段。但政治之所以成为一种文明的行动,而非野蛮的暴力,就在于这种实力通常要以话语上的正当性表现出来,由于这种正当性或正义原则对野蛮的军事力量起到了相当大的遏制作用,这种话语力量也就被当前的学者们热炒为所谓的“软实力”。因此,在政治较量中,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赢得了主动,谁掌握了对问题性质的定义权,也就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邓小平在中英谈判中表现出的强势不仅是政治意志,而且是他通过对谈判性质的定义,掌握着整个谈判过程的话语主导权。
当撒切尔夫人经过对香港形势的理性评估,放弃了政治牌而打出经济牌时,已经用功利主义的利益计算取代了政治的正义原则。他们预期中国经济发展对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鸡”的依赖,至少会让中国在香港的治权上有所让步。确实,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对于内地的经济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而邓小平也常常被人们看做是实用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