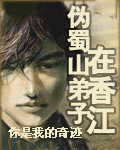香江边上的思考-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英两国外长七份信函的公布引发了香港社会乃至国际舆论的争论,一场批评彭定康政改方案“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的舆论战就此展开。在中英政治分歧之间,香港人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北京立场的被称之为“亲中派”,支持彭定康的被称之为“亲英派”,香港社会就此进一步分化。正如刘兆佳教授所言,“精英之间,精英与市民之间及市民之间,相互摩擦的状况正日显严重;持中间立场的政治力量不得不在‘亲中’、‘亲英’二者间做出选择,激进力量之间则冲突不断。……政改之争正侵蚀着港人治港的基础和条件,港督若不及早恢复自然之道,则光荣撤退只是一个梦想,而港人却要承担未来外部不和、内部分化等‘后遗症’。”而这恰恰是彭定康的政治目的,因为这场斗争本来就以香港人做赌注的(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一”)。为此,彭定康成功地获得西方世界的支持,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支持彭定康,认为推行民主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正是由于西方世界的支持,彭定康将政改方案看做是历史终结处所做的最后斗争。他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强调,英国在香港的目的不是建立机制、制度和达成协议,而是要把香港的独特生活方式“延至下一世纪”,其历史意义“不亚于法国大革命”。
当然,中央很清楚,这些美丽的政治修辞不过要掩饰英国人借东欧事变和苏联解体推翻过去的协议,通过加速民主化将香港搞成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进而影响中国的政局发展。因此,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西方世界肢解中国战略的一部分。面对这种国际局势,中央于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向香港各界陆续披露邓小平关于香港政改问题的几次谈话内容,表明中央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这个原则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原则,就是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行使“一国两制”的原则,就是中国绝不屈从于西方国家支配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按照小平的指示做好了“另起炉灶”的准备,即原来中英协议中的“直通车”计划流产,中方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单方面筹组第一届特区政府。
其实,另起炉灶的问题早就在邓小平的脑子里思考过多遍了。邓小平一直担心的是港英政府在过渡期自搞一套班子,强加于未来的特行政府。因为香港回归没有“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是“和平过渡”。在“港人治港”的条件下,港人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年突然接管香港,而必须在过渡期参与管理,熟悉港英政府的运作。而英国人肯定不让真心拥护中央主权的港人或中央信任的港人参与管理,而是培养亲英势力或让反对中央拥有香港主权的港人参与管理,这样就制造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内在矛盾,为香港回归后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增加了困难。为此,早在联合声明签署前,小平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权交接问题上。在一九八二年,他就明确提出爱国爱港政治人才的培养问题:“一般的方法,是培养不出领导人才的。领导人才要在社会里培养。最好要有一个社会团体来担负这个任务。我们说,将来的香港政府是以爱国者为主体。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组织。我们要着眼于培养人才。要找年轻一点的人将来管理香港事务。这些人必须是爱国者。”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工作是要考虑如何培养干部的问题,要考虑用什么方式来逐步参与管理。……我曾经提过,港澳工委要想法在香港搞些社团,实际上就是政党,英国人搞了一些社团,我们也要搞,可以从中锻炼一批政治人物,没有政治人物不行,这工作不能抓的太晚。”(转引自,齐鹏飞:《邓小平与一国两制》,188—189页)
邓小平思考爱国爱港政治人才的培养尤其关注其组织形式,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英国人控制着建制力量,而爱国爱港人才的培养只能在建制外进行,只有组织政团才能将建制外的人才凝聚起来,形成政治力量。工联会这样的香港传统左派组织无疑是爱国爱港的基本力量,但由于港英政府的政治压制以及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的包袱,这些组织在整个社会被边缘化,即使发展这些组织,也“远水不解近渴”,难以适应香港回归的工作重心,即通过稳定香港的大资本家来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在这种背景下,新华社香港分社全力纠正了历史上形成的“一左二窄”的工作局面,着力拓展对香港社会上层精英(如资本家和中产专业人士)的统战工作,使得爱国爱港力量从原来纯粹的地区左派组织发展为包括工商界和中产专业界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爱国爱港阵营由此也在香港被称之为“统一战线派”,与所谓的“民主派”形成对峙。正是在统一战线基础上,无论在中英谈判中,还是在基本法制定过程中,工商界人士和部分中产专业人士都成为香港回归的坚定拥护者,成为中央可以信任和依赖的管治者。
然而,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和一九九二年彭定康政改方案彻底打乱了爱国爱港人才的发展计划,使一九八二年以来逐渐聚集起来的爱国爱港政治精英发生了分化,政治力量遭到削弱,以致在一九九一年立法局直选中惨遭失败。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港澳工委痛定思痛,调整了重统战、轻选举,重工商专业界、轻地区力量的工作思路,加强了地区力量建设。一九九二年代表地区力量的“民主建港联盟”(民建联)成立,一九九三年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党成立。一九九五年,代表中产专业界人士的“香港协进联盟”(港进联)成立。就在爱国爱港阵营重新凝聚力量时,民主派阵营也加强了力量整合;一九九四年,“港同盟”与“汇点”合并,成立民主党,两大阵营就一九九四年的区议会选举和一九九五年的立法局选举展开了较量。其中,“民建联”打出爱国爱港的旗号,成为区议会的第二大党。这是香港爱国左派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之后第一次正面登上香港政治舞台,对香港政局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爱国爱港政团在港英立法局选举中拥有的政治力量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构成了一定的制约,自由党在立法局中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提出了修正案。彭定康为了使其政改方案在立法局中顺利通过,不惜透过英国政府对在香港立法局中拥有一票的英国大商家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其投票否决自由党的修改案。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在彭定康全力游说下,港英立法局通过了对立法局选举条例的修订,并以一票之差否决了自由党提出的修改方案。这意味着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具有了法律效力,中英两国政治谈判的大门彻底关上了。
就在港英立法局通过政改方案两个多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宣布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终止,并决定由特区政府筹委会筹组第一届特区政府立法会。在彭定康看来,这无疑给他的政制改革下达了“死亡通知书”。可当时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香港不可能透过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员,全国人大遂批准了“筹委会”的决定,由四百名港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六十名立法会议员,由于这些议员不是按照基本法产生的,因此立法会也被称之为“临时立法会”。此时,经历了一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非但没有瓦解,反而彻底走出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阴影,经济上持续增长,政治上变得更加稳定和自信。香港人对中央的信任度开始上升,而英国政府则失去了筹组新政府的参与权。这时,英国政府才开始检讨对华政策,外交部“中国通”们的声音重新占了上风,而随着一九九七年五月英国大选后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合作已不可避免。期间,尽管英国政府着力培养陈方安生成为未来的行政长官,可命运和机遇却与她擦肩而过。特区政府成立后,中央着眼于香港的稳定让港英政府公务员全部过渡,陈方安生继续作为“公务员之首”辅助行政长官董建华,这既是香港顺利回归的前提,也为香港后来的政治分歧埋下伏笔。而上诉法院的陈兆恺法官在马维锟案中的主张遭到了香港自由派大律师们的批评,于是两年后的居港权案中,终审法院彻底推翻了马维锟案中的推理,主张香港法院可以对主权者的行为行使违宪审查权,由此引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而在这一系列争夺基本法解释权的过程中,伦敦培养出来的普通法大律师们逐渐迈向香港政坛。
政制发展之谜(下)——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三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9年第2期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回归十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明确香港可以在二○一七年普选行政长官;待普选行政长官之后,可以普选立法会。当晚,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等连续在香港召开两场座谈会,就“人大”决定向香港社会各界释疑解惑、听取意见。乔晓阳在开场白中,首先给大家讲了一段生动幽默的“关公战秦琼”的故事,意指中央和香港社会各界对话、沟通与协商需要一个共同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就是基本法,就是基本法所确认的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具有决定权。如果香港有人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就没法进行对话,就会出现“你在隋朝我在汉,咱俩交战为哪般”的荒谬局面。这个历史典故太文雅,乔晓阳又特别举了股票交易的例子,“就像A股和H股,不同交易所,没法交换”。
香港政制发展既是英国撤退战略的产物,也是中央积极回应香港民主化诉求的产物。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坚持英式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主张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最终达致普选;而香港反对派则继承了彭定康推动的法国大革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立即实行最彻底、最开放的民主普选。在香港民主普选问题上,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分歧是“稳健民主派”还是“激进民主派”,是中央主权之下的地方民主与不要中央主权的民主。然而,在后“冷战”时期的全球意识形态较量中,香港民主派以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掌握了对“民主话语”的定义权和主导权,把这两种民主立场建构为“专制vs。民主”,从而将中央置于政治和道德上的不利境地,也遮蔽了香港民主化背后的国家主权建构和国家认同问题。
香港民主化的首要问题就是处理工商精英与基层大众的利益关系,可香港处在中、英两国主权较量的国际背景和香港回归祖国这样的结构性变迁中,工商精英与基层大众的利益分配不可避免地与反对殖民主义的“反英抗暴”、“民主抗共”和“踢走保皇党”等更大的主权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香港的民主化从来都不是单纯的香港内部利益关系调整,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国家的主权建构。从中央提出“一国两制”方略开始到要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就是要理顺香港社会内部的政治关系以及中央与香港的关系,前者要照顾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后者要确保爱国者治港。香港回归之后,无论是关于居港权的“人大”释法,还是关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中央都是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这个最高的政治原则来思考香港治理。由于工商界对“民主派”推动的激进普选持反对态度,担心“免费午餐”和“民粹主义”将香港变成高福利的社会主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二○○四年和二○○七年关于香港政制发展的两次决定中,都将均衡参与、循序渐进作为香港政制发展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功能议席与直选议席各占一半,从而维护工商专业界的政治地位。
香港民主化涉及国家的主权建构。基本法虽然规定了香港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但香港个别精英人士并不认同共产党中国,也不认同中央的政治主权,以至于法律上的国家建构已经完成,但心灵上的建国或政治认同上的建国并没有完成。之所以强调国家认同是由于基本法所建构的“一国”很大程度属于country而非state,基本法赋予中央的主权权力与它要承担的政治责任之间不相匹配。中央对香港的政治责任是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可要维持繁荣稳定,光靠驻军和外交这些权力是不够的,而必须具有一些日常性的监督管理权。可中央不掌握香港的财政、税收和司法主权,无法对香港行使日常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