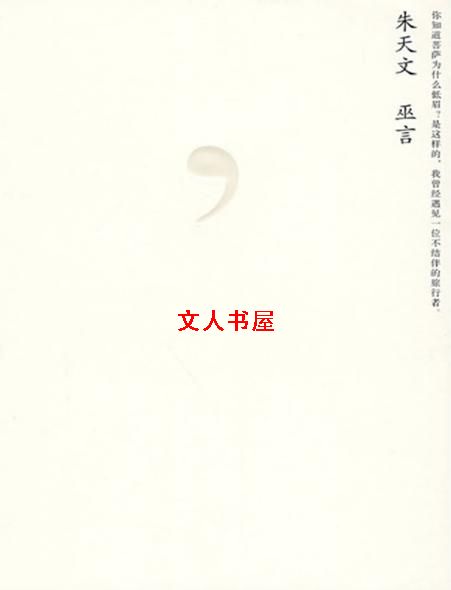巫言-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姐域内那些四处乱扔但暂时还没进垃圾筒的物件一齐拯救。我担心帽子小姐若是发现垃圾被大动手脚会羞愤吗?不,我打赌她对我所作的变动一定视而不见,盲无所觉。老实说,她似乎患了隧道症,漆暗的周遭她只看见前方亮光处,除了购物,她什么也看不见。
我渐渐嗅到,她的购物,散发出一种自虐气味。为了报复什么的,自虐。
黑夜我睁开眼睛,听见房门给带上帽子小姐出去了。我翻过身,见横敞的玻璃窗海景,照得屋里幽明。两天来我进房间第一件事,穿过边界到那头刷地拉开帏帘,脚底下,碧海晴空万丈起,眩摇。半夜三点钟吔,帽子小姐这时间出去?她的床,床罩没掀堆着杂什,她晚上回来后就鞋也未脱往床上一倒,至今?我再醒来时,有水声刷刷,是帽子小姐在洗澡。四点半了。
翌晨我下楼吃早餐,午前退房集合,我有的是时间喝长长的咖啡,看久久的维多利亚港。帽子小姐睡得沉,她只扒开被褥一隅蠕进里头蛹眠。她床罩上乱覆着无数罐高单位维他命C,E,B综合,善存,香港买固然便宜但即使是亲朋好友托带或托买,也太狂买了点。又有一大把黑加仑,此类糖果跟一些小零嘴小玩意儿总是处心积虑给安排在收银机旁边,成功诱发不少准备结账的人又掏出来更多钱。若顺两天来的轨道行事,钥匙是由稍晚离房的人持交柜台,而我为了等会儿回房不论帽子小姐还睡或也出去,遂打破规则留下纸条,告之我在三楼某厅吃早餐,集合前不会离开,如需钥匙请来找。
早餐有好丰丽的各类谷物加牛奶和各色调酱干果种子配生菜,让人不由得神农尝百草地每样都试。港湾对面天星码头,鸥在空中低回。一八八○年代,煤气灯微光颤动里的巴黎,歌剧院魅影。是的,什么没有照亮,什么被审慎照亮,怎么样照亮,于是让观众去想像没有照亮的地方。魅影从镜子背后出现,诱引姬丝婷进入镜内秘道。歌剧院地下幢幢迷宫,魅影摇颤的手提灯光簇投射出百条千条阑干,幻造出庞然一座骚动的笼子罩着魅影和姬丝婷像两只松鼠徒劳在奔跑。
穿渡歌剧院的地下湖。我已悉知这个地下湖,十寸高平台,藏有一百八十三度活门及一百五十支蜡烛,每支蜡烛其实是电动弹簧闪烁着硅胶罩内的细灯。湖面,湖底,烛焰映生出双倍的烛焰,忽忽粼粼,魅影和姬丝婷划舟而来。湖的远方,魅影藏身地。
唱:“除了这个世界以外,去哪里都好。”
唱:“不想迷路就只有认路,终结时总会到达某处……”
音乐天使之窟,姬丝婷从未亲见的无言师,以暗的部分更暗而亮的部分更亮,现身了。魅影告诉姬丝婷她一直是他的灵感,他教她声乐就是要她唱出他的作品。魅影戴着一张光所变形的面具,如诉如泣。
我待到必须上楼取行李了。等电梯时,见帽子小姐据着一间电话,仅仅一瞥,我也感觉到她一定是打了很久而接不通的十分懊丧。她全部人,那埋藏在钟形帽底下的半张脸,那戳键的手势,那从顶到脚一身新行头光鲜无比,全部的,都是忧烦。
我进房间拿行李,收好那袋帽子小姐当做垃圾却被我救下来的字纸们。同时那遍地遭帽子小姐劫后的余生,无二话我都一一救走。如今,我行李里有三分之一装载人家的弃物,搭机提回家,取出放在廊角旧报纸篮内待收废纸的人领去。每次我千里迢迢带回来自己的,室友的,同行者的垃圾,不是隐喻亦非象征,它们真的就是扎扎实实会占据行李空间的实物。除非没见到,见到了,我无法见死不救,这已成为道德的一部分。
最后,登机前我跟帽子小姐在免税店专柜与专柜间狭挤的通道遇见了。同居两夜,这回,我们才算初次遇见。我意思是,我们的眼睛,正正式式看到对方的眼睛,我们已从物,恢复为人。不会,不会再有交流的机会了,所以我们放胆拉起眼睛的帘幕,坦白望向对方,竟如一对老搭档哥俩好,一对嫖友狎黠而笑:“瞎拼喔。”
“唔,瞎拼。”
我们的招呼,我们的道别。不结伴旅行者,首度抬起来目光互相见到时,一点也不用担心,因为天堂陌路,前头便好投胎自去了。轻若鸿毛之生,互相看见了,顿时变得好重好重。我感觉自己的行李越来越重不是办法,必须学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该,垂下眼帘,眼不见为净。
我徘徊在学习的门外,东张西望,一不注意便身陷感情交流的进退维谷中。看啊湖的远方,魅影要姬丝婷选择,或永远留在他身边,或目睹未婚夫被绞死。然而时刻到来的瞬息,魅影放手了,命姬丝婷二人离去。缉捕者追临,已不见魅影,空无一物的舞台上留下了骨白面具。
唉结果魅影还是放手了。那时,黑暗消融了,然而光亮也没有了。没有亮,没有暗。那时,放下眼帘,目光低垂,死神一袭长袍如曳着沉香木浓浓的绿荫行过大地,所经之处不见生灵,无有兴灭。那时好寂寞。
匿名戒酒协会里有个戒酒满九十天获得满堂彩的孩子也是演讲人说:“你知道九十天以后跟着的是什么?第九十一天。”
那时,轮到另一名戒酒人站起来说话。他说:“我叫马修,我今晚只听不说。”
没错,那时我只听不说。
菩萨低眉
怕与众生的目光对上,菩萨于是低眉。
兽医江医生就是。
任何人,拉开玻璃门跨进他的小诊所,一概智商当场减半,情绪商数亦陡降至近乎精神病。这些抱猫抱狗的人类,不分愚智贤肖,全部一个样,都被他们手上的小动物控制了。
一位不戴隐形眼镜绝不出门的美貌股票分析师,忧心忡忡顶着厚重眼镜出现,只顾她怀里的约克夏而任眼镜搁浅于鼻翼,使她不仅像戴老花眼镜老了十岁,亦焦距不良引起的脸相不良显得至少无知了二十岁。配合这张脸的,是一连串自暴自弃式的蠢发问,期待换得医生的劝慰和鼓舞。
江医生维持他一贯的酷,不回应顾客们不当的期待。他把自己调到恒温状态,不多不少,不热不凉。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法,他受不了顾客把他诊所当成小庙来求签问卜,起码的常识和理智全部放假当他是通神灵媒来依托。他不涉入,不威权,不温情,他只对他们陈述事实。
而且他得忍住,各方面的忍住。
这位美貌股票分析师,有一双稠密长睫毛,如此稠密,遮得什么也看不见惟薰溢出醚味先将自个蒙倒了,以致每回在电视上分析股票,不但观众不怎么信,她自己也不信似的屡屡报以凄迷笑容。而那些受邀来对谈的专业人士,大家皆笼罩于醚味之中摇摇晃晃,恍惚在谈星座,论运势,倒成就了她变成算命师的报明牌。
江医生得忍住,不露出一丝儿迹象他认识股票分析师。虽然这次他诧异发现股票分析师的烟视媚行状,烟视,原来她是个大近视眼,错觉为媚行,冤枉她了。
照例他也不认识这位偶像歌手由女助理陪同亲自把白色安哥拉送来,自称把拔(爸爸)或拔,是偶像歌手跟猫讲每句话的发语词。这很普通,来诊所的人类皆自认是小动物的双亲,对它们发明出各种狎呼昵喊而不以为耻。不寻常的是,分明马麻(妈妈)怎么叫做了把拔?为此江医生趁隙注意了一下,没错,是马麻,外观上不折不扣的是。
女助理负责说东问西,永远知道上司何时要启了便身子一斜耳朵凑高去,将偶像歌手嗡嗡嗡的蚊子语听见后向医生复诵一遍。偶像就是偶像,排场得!一定不能第一手和群众接触不然就破功了。江医生得忍住,才不致让眼睛鼻子嘴巴面皮总之一脸嘟噜骚动的笑泡泡冒出来。
江医生给猫肚皮脓肿成瘤的地方剃掉毛,划开瘤口挤净脓,打了一针消炎。过程中,偶像歌手不避秽也不管妨碍到医生作业一径贴近猫颊说尽猫语,女助理袖手在旁发着嘶嘶齿冷声。从这里就看出来,谁是父母,谁不是。
待知道猫儿子必须住院给脓囊里灌药,观察一日,后日出院,偶像歌手恨吐口气不语了。这是严厉的责备,女助理蜡黄脸默默承受,忽而朝江医生谄媚一笑解释:“布朗娣怪我没有早点带它来看医生。她出国期间都是我照顾猫嘛,这次出国又比较久。”
女助理深信国人皆是她上司迷,故不时透露点小隐私,小逸事,小典故,当做恩宠赏赐于人。江医生得忍住不接腔,实在,他跟偶像歌手间有段难忘的经历。
他南下高雄,因惧搭岛内线飞机便乘国光号。车上初闻某歌,明明唱的国语却如何也听不懂词,那旋律努力要拉住词亦仍然分崩离析,剩下舞曲节奏的强拍,与歌女的无邪奶腔,播了一回又一回,循环于长途密闭空间里敲敲打打,打得乘客昏困无力都成顺民,竟没有人起来反抗。他听到第几遍唱时几乎呕吐,分不清是否晕车,魔音穿脑跟住他到友人婚宴上,尽责扮完介绍人,夹尾巴直奔机场逃回台北。他震惊于六小时五十分的车程去,五十分的飞程回,从此敢搭岛内线。
他得忍住不对女助理脱口唱出来:“太阳不升,月亮不落,啊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那是后来他出诊到大牛妈妈家,忽闻此歌,很失态地搁下处理中的大牛耳朵,四望寻歌,看见综艺节目正在打歌,他就那样不顾一切傻看着荧光幕上列现的词,把它跟歌像多年失散的兄弟总算互相寻得了。
大牛妈妈挺热络附和医生:“偶像歌手喔。”
偶像歌手蹲笼子前和猫儿子话别,眼泪汪汪弄成一场伦理剧,女助理更苦了。江医生得忍住不告诉她们,这只白色安哥拉是半个聋子。它吊插的杏仁状眼睛看似斜视但不是,惟呈现出对人间事充满惊异。白色安哥拉若蓝眼大多是聋子,土耳其传说里,国父凯末尔转世为聋耳白猫。这只左眼翠碧的安哥拉,左耳是聋的。
江医生得忍住每次出诊,大牛妈妈亲昵地跟他讲客家话,临走又非要塞给他福菜,酸菜,萝卜片干等客家土产,认定他识货极了知道如何烹调它们。事实上,他跟验光师老婆绝少开伙。他还年轻,年轻得其实他对父系客家语只能听(母系福佬语),不能说,勉强说时不会比他的破烂西班牙语好些。大牛妈妈并且认定因为同是客家人他必然少算了出诊费(其实他没有),遂把他报出的药钱非要多添两百元。他推辞,她执意,完全是在君子国。每次的行礼如仪,他不否认也不承认,他只是,大牛妈妈既然派定了他做客家小同乡他便按谱奏曲罢。
他亦得忍住,花鬼主人把摺耳猫花鬼朝疗台一放,久病成良医的说花鬼流鼻水了,要拿金黄八角形药,拜托医生帮忙先喂四分之一颗,因这种苦药即使藏裹在花鬼最爱吃的鸡肝里也骗不过它了。还请医生配两瓶甜甜会沉淀白粉的药剂,乃家中黑鬼最近老吐舌尖又是牙龈肿溃,黄鬼也有轻微牙周病可一起服用。花鬼主人手下尚有狸鬼,灰鬼,白鬼,虎斑鬼,来来去去的流浪猫。
“江医生,我要一瓶Ear Mite。”沉缓如绿苔的女低音突然现身,花鬼主人下班绕路过来。
“Ear Mite ?”
“滴耳疥虫的。”
“不一定是耳疥虫哟。”
“是耳疥虫。”
“说不定是耳发炎哟。”
“耳壳里面黑黑的,是耳疥虫。”
江医生沉吟了。
“耳发炎药我有,就是瓶嘴尖尖长长的比较贵的那种,上次我们家狸鬼耳朵流水,江医生说是中耳炎,就拿那种药。江医生说如果是黑耳朵,今天擦干净明天又变黑的话,是耳疥虫。”
有记性。让医生对自己的言论并非耳边风居然被听进耳了的,得忍住安慰之色。
狸鬼消化不良时,他调配药,桃红色浆剂,桃红得令人想起一九五○年代的塑胶杯若盛热水会化学变化产生毒素。花鬼主人很吃惊:“以前是乳黄色药。”
好记性。
花鬼主人抱只刚长全牙齿的黄斑小鬼来打虫,他交助手处理,先上秤,却听花鬼主人嚷起来:“不对,不是这种,是药水那种。”“啊?”
“江医生是用药水。一向是药水。”
“没有吧都是用这种。”
花鬼主人决定不以助手为交涉对象,把江医生从里间的忙碌中硬是唤出来,气不忿儿道:“这么大的药片,给它吃四分之一!你看流鼻水药那么小颗,大猫吃每次也只吃四分之一。江医生你说猫对药物很敏感的吔。”
“基本上,单位不一样,剂量也不一样。”
“可是这么大药片看起来很恐怖。”
“还好吧。”
“为什么是药片,不是药水?”
“药水早晚吃对不对,吃几天。药片吃一次就行了。”
“听起来更恐怖。”
“基本上,这药片算温和,没问题。”
“那为什么以前用药水,不用药片?”
“基本上打虫药很多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