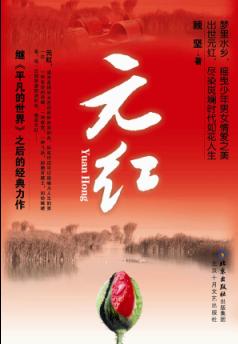元红-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老师要为唐月琴穿上衣裳,被粉香一把抢过来,说:“这裤衩还能穿啊?”
张老师一拍脑袋,说:“瞧我,呆了。”便从床头叠好的衣堆里另找了条内裤,替唐月琴换上。
正穿着,粉香咋呼起来:“这杨剌毛不可能是从树上飘下来的。张老师,这绝对是哪个阴鬼使的坏!”她把裤头举到张老师面前用电筒照着,“你看你看,这绿汁!——没得命,这粘着的不是杨剌子头嘛!”
张老师凑上去一看,心里顿时沉了下来。
《顾庄》第四章6
这晚陆校长在学校小食堂里设宴,招待乡里派出所郑所长。郑所长是专门来学校处理一件棘手事儿的。顾庄中学原本是建在一块乱坟滩上的,农村建学校往往就建在这些腌臜地方——偌大的校园怎能占上好田亩呢。比如说有名气的吴窑完中也不过建在废窑滩上,那地方解放前是专门处决犯人的刑场。
十几年前建学校时,庄上把那些无主的坟墓都平了,有主的移到了集体公墓。哪想到时隔许多年,有户人家从外地回来了。解放前逃亡出去的,一直音讯杳无,庄上人都以为他们全死在了外头,哪晓得现在又还乡了。那户主一回来就找父母坟墓,却看到当年的乱坟滩已变成了红墙青瓦、树木蓊郁的校园,他父母的坟早就夷为了平地,上面种着学校的蔬菜,不禁悲从中来,在父母下葬的约摸方位哭得昏天黑地。哭过后便在那地方堆土为丘,插起纸幡,烧起大钱来了。学校哪里肯依,这青葱整洁的校园里弄出两个坟茔来成何体统,看了人心里多不舒服啊,倘夜里走到那里别说孩子们怕,大人心里也发怵呢。双方纠缠多日没得结果,学校只好打电话请派出所来人解决了。
郑所长是顾庄初级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现在的陆校长就是他当年的班主任,所以听到陆校长的求援电话当即就赶来了。在学校办公室进行了调解。他本来就长得牛高马大,一脸的络腮胡子,又加上穿着一身制服,黑着个脸走进来,那造坟的主儿心里就怵了三分。他在外面流浪了小半辈子,深知派出所的人最是不能惹的,当郑所长盘问他这么些年来到底在外面做的什么勾当,并暗示他重新回来落户口会有诸多麻烦时,他顿时了下来,自己找坡台往下滚了,说其实他也记不起父母埋在哪旮旯儿了,堆两个土堆也是想有个念想,清明过冬烧两张纸表表心意,既然学校不方便,也……也就算了。郑所长说,咋个算了,你公然在学校这样的公共场所烧纸,大搞迷信活动,对我们的学生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可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啊!敢情“文化大革命”都结束好几年了,郑所长的政治语言还用得蛮活泛的,吓得那人脸都白了,连连说:我、我不对,我、我去铲了!向大家作作揖,连忙溜了出去。
那人一走,办公室就热闹了起来。陆校长如释重负,大着声吩咐食堂主任张国楼上街办菜,晚上大家陪郑所长好好喝一顿。几个老师又是敬烟又是奉茶,连声赞郑所长有办法有水平,说晚上定要多敬所长几杯。郑所长说喝酒就喝酒,但晚上必须赶回乡里,那边还有事——要喝就请早吧。陆校长就要两个年轻老师马上陪国楼一起上街,拣好吃好喝的快点买来,早点开席。
酒喝到八分账上,郑所长看看表,说“得罪了”,要走。大家劝他再喝几杯,他说不了,有事,下次一定尽兴!一干人也就不硬留。陆校长说:“我送送你。”大家站起来,想校长要与郑所长有私话谈,也不跟上去。等两人走出门,一齐坐下来,继续玩筷子功。刚才两个“头脑”在,毕竟不敢放肆。
《顾庄》第四章7
两个人都喝得微醺,手搀着手亲热地边走边谈,这时候,晚自修第一堂下课的铃声响了,陆校长见好几个女生不是往厕所走,而是“叽叽喳喳”往宿舍跑,感到有些蹊跷,便拦住一个学生问:“干啥呢你们?”
那个女生说:“我们班唐月琴被人暗算了,这会儿医生正帮她看呢。”说着急急追上前面的同伴。
看来世上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个孩子嘴不紧,还是把这事儿传了出来。
陆校长听了那个学生的话,一时间不知就里,惊得酒都变成汗了,忙拉着郑所长的手向女生宿舍走去,还没进院门呢,就听到张海珍老师训斥的声音。几个女生一窝蜂地溜出来了,差点儿撞上了他们。
张老师在院里的路灯下和种道、粉香说话,看到陆校长他们来了,脸上顿时有些局促起来。那粉香和郑所长是初中同学,见了面很亲热,喋喋不休地把事情说了,听得郑所长眉毛都扬起来了,说:“咋?一个初级中学就有这样的事了?”
陆校长显然有点气急败坏了,声音就有些发粗,对张老师说:
“张老师,你这班上咋的了?怎么尽出些说不上口的事来!”
张老师脸涨得通红,眼里有了泪,强忍着,嘴里嗫嚅:“我、我……”
“好了,别说了。”陆校长发现自己有些失态,声音柔了下来,指着门问张老师,“能进去看看吗?”
“能……衣服穿起来了。”张老师哽咽着回答。
门推开,见唐月琴已能坐起来了,昏黄的电灯照在脸上,映着未干的泪痕。见校长等人进来了,脸上就有些惶,楚楚可怜的样儿。
“好些了吗?”陆校长问,声音里充满了慈爱。
“好些……不疼了。”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那就好,”陆校长舒了一口气,“那你就好好休息吧,晚自习就别去上了。”
一行人走出院子。郑所长说:“老校长啊,现在的学生可不像我们当年单纯了嘛!”
陆校长气恼地说:“谁晓得呢?以前从没这些事。”又说:“兴许真是桃园里的杨剌子毛飘上去的也不保定!”
“不可能。果真像粉香说的那样,肯定是人使的坏。你想想,别的衣裳上为啥子没有,单是个裤衩?而且,还那么多?”
“是哩是哩。”走在后面的粉香附和说,“杨剌子头都泥上去了哩!”
“这事不行!”郑所长突然站住脚,“这事得查查。老校长,现在有些学校确实已发现学生有犯罪下流活动,圩里(车路河南面地区对该大河北面的习惯称呼)有所中学流传一种叫《###》的黄色手抄本,是香港那边过来的,弄得学生没得心事学习,已引起县里的注意,说是准备查呢!”
“那、那怎么办?”陆校长声音里有些慌慌的。
“没事。”郑所长转身对张老师说,“带我上你班上,说不定这个使坏的学生就是你班上的。”
“可是……可是……”张老师有些迟疑。
陆校长也接上来:“郑所长,事情不要哄得太大啊。”
郑所长正色说:“这事非查不可的。”他顿了顿,“陆校长,这事不查出来,以后会出大事的——到那时候大家都不好收拾了。”
陆校长只好不吱声。种道和粉香说,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家去了。
张老师上去对粉香说:“上庄不能丝风(方言:透露)啊。”声音里有些凄惶。
“哪能呢,张老师。这我们懂。”
《顾庄》第四章8
张老师把郑所长引进教室,对大家说:“这是乡里派出所的郑所长,在百忙之中来帮我们学校解决问题的。正好听说我们班上出了一点儿事情,专门来看看,希望同学们配合郑所长做工作。”说完,对郑所长手一伸:“郑所长请!”
郑所长走上讲台,双手撑在讲台两边,板着一张大红脸,红丝蠕蠕的眼睛在全班同学的脸上扫了一遍,也不开腔。足足过了一分半钟,他清了清嗓子,说:“同学们晓得我为什么要到你们班上来吗?”
没有人回答。大家都被他那威严的架势镇住了,没有人开腔,教室里安静极了。陆校长点上两根烟,自己叼一根,上去递给郑所长一根。
郑所长接过来,眼睛盯着大家,在嘴上“扑哧扑哧”地深吸了几口。香烟的火头往后直退,起码玩掉一小半。隔了好一会儿,两股浓浓的烟从他鼻孔里喷出。坐在前排的存扣被呛得咳嗽起来,在教室里响亮着,忙用手蒙住嘴,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我是到你们班上逮坏人的!”郑所长突然“嘭”的一拍讲台,大家被吓了一大跳。
“你们在座的有这么一个人,他居然逮了杨剌子碾在女生的裤头上,让那个女生饱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
他用指头“咚咚咚”敲着桌子:“这是彻头彻尾的——流、氓、犯、罪、行、为!”
“事情已经发生了,捂是捂不过去的,蒙混也是蒙混不过去的。我希望这个人现在能主动站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会看你的态度从轻处理——你们还是学生,不能一棍子打死嘛!”他嘬起嘴唇吸烟屁股,不意烧上了手指头,忙不迭扔掉了。有同学在下面“咕吱”笑出声来。
“谁在笑,啊?有什么好笑,啊?你们没人敢承认是吧?你们以为我挖不出这个人是吧?”他又“嘭”的拍一下讲台,吼道,“大家统统坐直了,拿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郑所长瞪着一双红眼在同学们脸上逡巡,和一双双十几岁的眼睛在碰撞。没别的声音,只听见粗重的呼吸。有的同学脑门上已流下了汗水,却不敢抬手去擦,唯恐会引起他的注意。
教室里空前的压抑和沉闷,这压抑和沉闷让人感到窒息。郑所长离开讲台,在行子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停在哪个同学旁边拿眼盯着,那个同学就更加正襟危坐,两眼望着前面,努力保持面部的庄重和坦然。
存扣趁郑所长走到后面时注意到陆校长对张教师附耳说了句什么。她听了微微点点头,就朝后排望去,那目光里就充满了忧伤。
这时候,教室的一隅却传来了放屁的声音。想必忍得久了,也想拼命地压抑着不想让它出来,可还是憋不住了,终于一点一点放出来。那声音就有些怪异,羞羞涩涩,结结凑凑,小心翼翼,到后来干脆一放了之,一了百了,一泻千里,喷薄而出,声音嘹亮婉转而悠扬。
这是个好屁,来得真是时候——在它应该来的时候施施然来了。好像突然掀开帘子的黑屋,放进来满室灿烂的明媚;好像一阵清凉的风儿,吹散了混沌的溽热;好像一支燃着烟火的大香,点爆了一挂三千响的鞭炮,总之,这个屁的尾声甫绝,教室里便盛满了欢快的笑声。同学们笑得花枝乱颤,笑得眼泪直流,笑得高潮迭起,仿佛要用笑声把刚才所受的惊吓和压抑送到爪哇国去。
但,最终,笑声渐渐势微,零零落落地收场了,大家重新回归到现实中来。但心情蓬松了,脑袋和身体的转动又恢复了自由,有谁,有谁能扼住少年自由的天性?——不能。但是当他们把头转向站在教室后面的郑所长时,笑脸凝固了。
郑所长正两眼盯住保连。保连坐得毕恭毕敬,双目看着前方,脸色煞白,头上汗珠直滚。郑所长敛着声音对他说:
“大家笑,你为什么不笑?”
“……”
“你是笑不出来?”
“不是。”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
“你会不会笑?”
“会……”嗫嚅。
“那你笑一个看看?”
于是,咧嘴,变脸。比哭难看。
教室里又恢复了原先的死寂。
“好了。”郑所长脸上倒浮现出怪异的笑来,声音温柔得让人吃惊,“你陪我上办公室来玩下子。”背着手先出去了。
保连站起来,面无表情,往外走去,走了没几步,竟一个趔趄,差点儿跌个跟头。
张老师没有马上跟过去,把椅子挪挪好,坐在上面对着大家,半晌没有言语。
不一会儿,远处的办公室传来拍桌打板凳的咆哮声。
《顾庄》第四章9(1)
事情真相大白了,真的是保连干的。
早读课上,张老师显然还是顾及了保连的面子,没有点出他的名字。保连惊惶之中不由对老师心存一份感激,准备课后找时间偷偷向老师承认一下错误,写张检讨了事。哪知梁庆芸的一张快嘴马上粉碎了他的如意算盘,给唐月琴写情书的秘密全被同学们知道了。他觉得他努力维持的尊严刹那间轰然坍塌。他像一个输光了银子的破落户,一条失去关爱和注目的丧家犬——倾家荡产了,一无所有了。当那些男生“噢噢”着一个个离他而去,把他晾在讥笑着愤怒着鄙视着他的女生那儿时,他的头脑中一度空白,接着又被无名的愤怒所填充,一股邪火就在心中燃了起来:他要报复!他要借报复来扳回心理上的平衡,他要把报复化为一场滔天暴雨,浇灭他心中升腾不息的心火。
他在家里吃中饭的时候就盘算着如何实施第一步报复行动。他是个有心计的人,一旦他的仇恨有了目标,他就要无休无止地去蚕食对方的精神和情绪,如影随形如同鬼魅般缠住对方,把对方拉入一塘无底的泥淖,而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