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离开以你为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弊大于利,因此我杀了孔洁。”我这样说完,他跟踪记录的笔也兴奋地蹦跳起来,最后重重戳在笔记本上。然后他站起来,像科学家配置出新药水,文学家写完代表作,陷入到创造的巨大喜悦当中。如不是警察阻拦,我想他会将我严严实实地抱住。最后他几乎是用了极大的痛苦才控制住这种喜悦,故作忧伤地说:“你啊,你就是典型的失宠王子。”
“不,我是救世主。”
我对他掸掸手,心里交织着无尽的嫌恶和失望。
两天后,我被再次带进会议室,那里架着一台摄像机。我感到一种庄重的压力,就像自己站在高台之上,被风刮动衣襟,底下有成千上万人翘首以待。我将习惯塌着的腰身挺直,表现得既不颓丧,也不轻佻。我在刻苦表演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消解紧张局面的是对面的女记者。会议桌早已搬开,她和我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她留着烫起的短发,皮肤白皙,脸庞微胖而圆润,穿麻灰色西服、黑蓝色套裙,正倾着上身,将交叉并拢的十指落放于跷起的膝盖上,微笑着看我(就像微笑是作为器官长在嘴角一样)。她的头是抬着的,因此目光略微仰视于我。她的目光从不脱离我。
我像被施了魔咒,突然涌现出强烈的诉求冲动。我在等她的指示。她点了下头,说:“不要老想着镜头。”
“嗯。”我甚至变得羞涩。她的牙齿洁白而整齐,语调缓和,像轻拂树叶的风,低沉而富有磁性,每个字都能让人清晰地感触到。她递给我一张当天的报纸。那位教育学会副会长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我杀人:一、家庭教育的失败;二、高考的压力;三、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同时他认为应该用三句话来防范此类事件:一、了解和理解;二、细心和耐心;三、平等和对等。
她问:“你怎么看?”
“放屁。”我已经揣摩到她的意思,她果然宽和地笑了。
“那么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排解,我想排解。”
“排解什么?”她点点头,眼神放射出鼓励的火光,这让我更加迫不及待地往下说。我确实说了一句两句,但会议室突然闯进一位中年男子(就像一只陌生的雄狮悍然闯入我和一只母狮的领地)。他递上纸条,她看过,斜靠在椅子上,和走出去的他极为默契地对视一眼。这让我觉得她和我不再有什么关系。
我住了嘴。
“排解什么?”她忧心忡忡地问,并没有记住我刚才说的。
“没什么。”我说。
接下来我又说:“我一度觉得你像我表姐。”
她似乎很感兴趣,将头倾到前边来。我感到没有比这更虚伪的事了。我本来觉得她像表姐一样值得信赖,但现在却看出,她的一切真诚都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她在试图骗取我的答案。她每一步都是为着这个,甚至于连早上怎样化妆也是为着这个。一旦我交代完毕,她便会毅然决然地离开,与同事击掌相庆。
“接着刚才的说。”她说。
“没什么好说的。”我说。
场面因此陷入尴尬,这大概也是她没预料到的。随后为完成任务,她开始不着边际地发问:“寄居在别人家里是种什么感觉?”
“我可以告诉你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并不总是充满火星。”这个回答几乎是我对她最后的仁慈了,但她没有把握住,她仓促地接着问:“为什么没有找到灭火器?”
“灭火器?”
“我指的是消除杀人冲动的灭火器。”
“不存在灭火器。”
“为什么?”
“因为整个土壤都在燃烧,即使有灭火器也无关紧要。”
“你就让火着得更大?”
“我没有让它着得更大,是它必然会这么大。”
我们似懂非懂地说着,她似乎凑够了时间,撇下我,一个人对着镜头声情并茂地念纸条:
灿烂的花季 怒放的美丽
忽然间 变成如此的结局
我的心啊 是何等何等的痛惜
孩子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听到 听到妈妈带血的哭泣
孩子 我感到痛惜
我真的 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哭。如果知道最终会有人写这么糟糕的诗,我宁可不杀人。
第十五章 坐监
在这间无所事事即使有点事也会很快办完的狭小牢房里,我总是清晰地看着时间张大手臂走过来。
此后便没什么人来找我。我端着脚镣、手铐,像熊一样长时间待在牢房。有时坐久了,就觉得自己粘在阴凉的地上,成为建筑物的一部分。以前听说囚犯可以和一只蚂蚁玩一下午,最终能分辨出公母,但这里什么虫儿也没有。因此我总是将手放在裤裆,大约可以了,便抽送。精液流到手上,有鱼市的腥气。我将它们擦在脚板上,无尽灰凉。我知道这么做不是为了收获什么快乐,而仅仅只是无事可干。
我向看守索要魔方,被拒绝。我说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他说:“我要是给你了,那关你还有什么意义?”他拉上小铁窗,我便猛敲它:“玩魔方跟关我有什么关系?”他没理我。等到下次送餐时我又重复这个问题,他说:“玩魔方就是你想要的生活,给了你,我们怎么惩罚你?”我想想也是。
此时让我耿耿于怀的倒不是窗外自由的天空,而是在青山被捕的时刻。那时我完全可以推倒刑警,夺路狂奔,捡起石头或菜刀伤害行人,如此便可被当场击毙。而现在我却不得不独自面对庞大的时间。人世间所有的事情,行路、劳动、战争、求欢,都是阻挡肉身与时间直接接触的屏障,但在我这里,在这间无所事事即使有点事也会很快办完的狭小牢房里,我总是清晰地看着时间张大手臂走过来。它孔武有力、无懈可击、无所不在,没有任何肉身都会有的情感;它既不会听你的求饶,也不看你的哀伤,它就像是不停砸下的泥石、不停涌来的浪潮,塞满整个房间,淹没你、凌迟你;它淹没你让你感到全身被重量重压时它是囫囵的,它凌迟你,让你感到每寸肌肤被刀锋掠过,它是凌厉的。它让你无法抵抗,让你极缓慢地死亡。一想到这里,我又想起爸爸,便热泪盈眶。
爸爸死前,所待的病室和这间牢房差不多,逼仄、阴暗、潮湿,地皮像一张鼠皮,散发着安静的恶臭。有一次他昏迷很久,悄然醒来,拉住我的手说:“我总感觉墙角坐着一位穿白袍的男人,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他在吃着简单的一个苹果,或者说他在简单地吃着一个苹果。你听到他嘴里发出的吧唧声没有?他正背贴着墙,微闭着眼,一门心思,吃着吃不完的苹果。他好像在等待一个时机站起来,他站起来后会将果核扔到地上,用脚掌将它踩平。他在等待这个时机,你不知道这个时机是什么时机。”
“他是死神。”他接下来说,“我想告诉你,死亡并不是闪电,并不是惊叹号,并不是一个瞬息到来、凶猛刺入的点。它是一个过程,一个所有器官排队失灵、一个热水袋变成霜的过程。没有比忍受它慢慢到来更痛苦的事。孩子啊,现在我最期待有个人躺在对面,和我一起死。但在人类史上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我看到的都是健全的、生长的你们,你们故意皱着眉头,让眼泪流出来,实际上你们的骨头却是轻浮的,散发着活泼的气息,你们身上的每个细节无不像雨后春天的小树,生机勃勃。而我早已衰竭。你们来,只为加重这个事实。你们就像是将我锁进囚室,而自己在外边像幼儿园的小孩子那样欢快地围着圈嬉闹。你们嬉闹的笑声像巨大的铁砣从空中一遍遍压下来,将我压在地面上动弹不得。你们让我感到羞耻,我们相隔万里。你们滚吧,或者你们有把枪,将我毙掉吧。”
这个一生不遂的诗人叹息数声,最后几乎是厌恶地将我掸开。我走向门外,委屈得想喊,生、老、病、死,人啊人,全他妈是一种耻辱,没一样不是。可是等到妈妈一走进去,爸爸便滚进她的怀抱,没完没了地哭起来。妈妈可是连一句安慰话都不会说。
牢房生涯,起先我还会试图与外界同步,蘸地上的灰,在墙上画横杠记日子,后来就懒得记了。人都要死了,记有什么用?时间因此变得极其混沌,有时几天过去好像只一天,有时一天又变成无数天(就像玻璃在地上碎成无数块);有时我渴望夜不要来,有时又渴望它早些来,尽管那时很可能已是黑夜。我开始无休止地做梦。有一次在梦里,我躺在床上,想爬起来去见一个人,却动弹不得。这个唯一的人被我挂念,也挂念我,我们彼此心无芥蒂,他却是没有面目,也没有名姓。我在世人里痛苦地排查,发现并无这样一个他。但当他擦着云层、树丛以及偶尔刺下的闪电,一路展翅飞来时,我却觉得再没有比他更熟悉的人了。他抖动身上的鳞片,抖出一地清水,说:“我梦到你,因此来看你。”
“你是谁?”
“我是你梦里的人。”
“那我是谁?”
“你是我梦里的人。”
“你是否在这个世界存在?”
“不存在。”
“那我呢?”
“你也不存在。”
“但你掐我的手,我感觉到真实的疼。”
“我们并不存在。”
“我要死了。”
“是我梦见你死的,我也可以梦见你不死。”
“那你梦见我不死吧。”
“都一样。”
醒来后,我觉得很好玩,又开始设想自己是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我想到一个作家微微驼背,坐到台灯前,在白纸上写下我的名字,然后以此为中心,添加衣着、居所、学校、街道、熟人、性格、事件、命运,编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我则反过来编织他的一切。每当我想得快一点时,我就命令自己慢下来,因此最终细致到连他写作时听什么歌都想好了。他从曲库挑出几十首歌,一首首听,直到听到这首《银色喷泉》(Silver Springs)时,才感觉找到了写作的节奏。他写了几句,感觉并不爽利,因此大声朗读,一不合适,便似暴君般将之涂抹。直到他自己也觉得残忍了,才停下来,对自己说:“就这样,就这样吧,你要学会原谅自己。”如此,他斗胆往下写,好不容易来了灵感,正准备像投身大火那样任自己燃烧下去,朋友的电话来了。他想出很多下作的理由推阻,却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窜进话筒指责他,因此他长嘶一声,气急败坏、仇深似海地去应酬。他虚与委蛇到深夜,终于逃回,稀罕的灵感却已跑得精光。他长久地坐在案前,试图唤回哪怕那么一点点,却什么也没有。因此他张开空空的双手,欲哭无泪,遗憾得像丢失了一片大海。他对纸中的我说:“我白天上班时,智力和体力本已损耗殆尽,回来后好不容易蓄积一点力量,又被那帮狐朋狗友搜刮一空。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给我干净的一天?为什么?”
我说的却是:“你既已将半条命倾注于我,何苦又要将我弄死?”
“你只有死才可以活得更久。”
“那好,我现在就将你杀死,反正我已杀死一个了。”
“不。即使你将我杀死,我也是不会出卖自己的原则的。”他鼓紧腮帮,张开的鼻孔不停冒出正义凛然的气息。我感到无比好笑,摸摸他的脑袋飞走了。
我依靠这样的互搏游戏,打发走不少时间。有时我想在我们人类背后,在那看不见的另一维度,存在一个久睡的人,他生产我们。我试图用性来否定这种繁殖程序,很快发觉性也是梦出来的,他说要有性,于是人类便有了性。有时我想人类早已灭亡,我们今天之浩大繁复,不过是明朝或宋代一个巫婆投放进镜中的幻象;有时具体而细微,我想我是十万个我之中的一个,我几乎能在每个码头碰见另一个自己,他们有的麻木地做着木匠,有的搭乘飞往圣保罗的飞机,有的跟着行刑队等着看热闹;有时我又想会有一位未来的子孙开来直升机,将我捎离肖申克,他说如果不将我带走,未来他就不会存在了。在飞机上他一直若有所思,飞到顶点时恍然大悟,他说:“其实我只需要带走你的精子就可以了。”
我就这样整日整夜躺在复杂而无限的线条里,兴奋到不吃不喝。谁要是此时打开牢房将我释放,我说不定还要大发雷霆呢。我会告诉他,到哪里去找这么安静的地方?不用工作不说,还白吃白喝。我是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思考人类和宇宙的了,然后我在连续失眠的尽头痛哭出声。我开始后悔没有在作案之前就想到这样的招数,如果那时便这样,我便能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无毒无害地度过整个人生。可是很快我又想,我现在之所以如此自足,也是因为我明白自己总是要死的,而且被管制得无处可去。
后来看守出于同情给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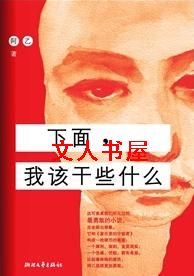
![[HP]耽美大神,我错了!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7/706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