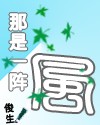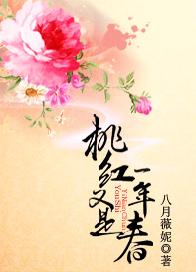悲愤是一种病-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拿说娜肥钦庋荒切┚薮蟮娜巳核莆盏摹�
然而对于疯子的地理位置,他的记忆中还有另一个答案。那就是他自主地选择了这里。的确,人类历史上的疯子大多有两种处境,一种是他们被人群唾弃,他们被人们发配了。另一种是疯子自我发配,他们自己离开了人群,孤独地来到了人群无法看到的地方。他们对人群失望了,因而,他们来到了大柴垛上,在天穹下过着疯子的生活。他们在冥想中度过余生。
葛朗台的意志力
小说中,吝啬鬼的形象,过去,总是被人嫌弃的。读者大多将他们看成是笑话,作者也大多将他们当成反面人物加以嘲讽。例如,葛朗台,这个人物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显得那么可笑,那么可悲。作者让他穿得破烂、吃得穷酸、过得拘谨。几乎是有点儿可怜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葛朗台的吝啬是出于他自己自主的选择,完全是他自己的意志力的产物,由此,我感到葛朗台的吝啬倒是有一点儿值得我们钦佩,至少,他不是因为外力的强制而选择了吝啬。另外,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此巨大的意志力的,能将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信念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这种选择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种吝啬。这会儿,我们都看到了,私人购买摩托车、汽车需要缴纳附加税,私人购买空调要缴纳增容费,如此等等,用电超额要加纳加倍的电费等等。一个无形的力量正在限制着个人享受生活。反过来就是说,这个无形的力量正在用外力使人们选择吝啬的生活方式,不是私人汽车、摩托车,不用空调等等等等,反正享受生活的事情要尽量的克制。实际上,这会儿,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人都是〃吝啬鬼〃,然而,他们的吝啬要比葛朗台在人格上差劲十万八千里。
为什么?葛朗台是自己选择了吝啬,而我们这些可耻的人是被迫地选择了吝啬。我们这些崇尚享受的人,正出卖着自己的意志。葛朗台的吝啬是得到了自己的意志,而我们的吝啬是出卖了自己的意志。
引一段似乎与上文无关的引文。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那种认为社会比个人更关注未来的观点,其所具有的含义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这个论点并不只是认为只有整体社会才能够满足诸如安全或者国防等某些未来的需要,而且也是指社会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将其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为将来提供储备的工作上去,而且投入的资源应当比个人分别决定者要多……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除了那些主张这种做法的人的武断判断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佐证这个观点。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我们不仅没有理由要求过去几代人应当为我们提供多于他们已提供的东西,而且也同样没有任何理由为个人开脱其对未来的责任。上述认为社会比个人更关注未来的论辩,由于这样一个常被人们征引的逻辑荒谬的论据而变得毫无意义,这个论据指出,由于政府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借代,所以它能够比个人更关注未来的需要。〃
由此,我们在想任何一个自由的社会,都没有权力强迫人们为〃未来〃支付罚金。未来应当有个人来掌握。从这个理由出发,我们就可以说,任何使人成为被迫的吝啬鬼的做法都是不符合人道的。
癫狂的女性
中国现代 小说的第一个人物形象是一个疯子――狂人。中国新文学是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的,这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癫狂〃――这种人类精神的极端状态在中国文学中有了自己的正面表达。在鲁迅的小说中,狂人是作为人性解放的先驱、精神自由的战士、反抗礼教压抑的猛士而出现的。他以他癫狂的外表,给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带来了冲破礼教罗网,获得解放的预言,这里癫狂是先知的别名。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狂人在精病理上属于狂噪症类型。那么郁达夫笔下的则出现了病理上的忧郁症患者。《沉沦》主人公是患有严重忧郁症的留日学生,他在饱受了失眠、酗酒、异性的歧视、对故国的思念之后,因为对情爱以及祖国的绝望而自杀。作者对这个精神上的非正常人给予了极端的同情,将忧郁症患者的病理性自杀解释成了对社会的反抗,从而再次为中国文学塑造了正面的癫狂人物形象。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女性写作正是从这个背景中展开的,首先映入我们的眼帘的是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这个因患病而陷于严重忧郁的年轻女性,对忠心爱她,对她唯唯诺诺,长相委琐的苇没有兴趣,而对玩弄女性的高手,长相俊美的凌吉士却含有性幻想,渴望征服凌吉士,得到凌吉士。但是当凌吉士真的被她征服,吻了她时候,她又厌恶地推开了他。这是一篇在五四时期引起巨大轰动的小说,其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赤裸而细腻地表现了女性的性意识――一个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无视陈规漏俗的癫狂人物。
但是解放并不能一蹴而就,在莎菲女士的癫狂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礼教的影子,这个影子追随着即使是处于忧郁症状态而陷入癫狂中的莎菲,她渴望得到凌吉士肉体的爱,但是当凌吉士要给她这种爱的时候她退却了,这种退却是礼教给她的,是一种理智的胆怯,她并不能真正地走到爱的癫狂状态中去。
中国文学史上〃五四〃作家对爱情的描写是破天荒的,他们对浪漫炽情的热衷也是破天荒的,其中情感中心的意味不言而谕。胡怀琛《第一次的恋爱》和吴江冷的《半小时的痴》均以调侃的口吻讲述理性主义者突然间一见钟情地陷入对女子的痴迷之中〃情感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嘲讽了理性主义的虚弱,肯定了情感的伟大。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情感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的说法在〃五四〃男性作家笔下尚可成立,而在女性作家那里则多少要打一些折扣。她们首先追求的是女性社会身份的解放,因而在走向自由的征途上,〃五四〃女性尚不能接受真正的〃情〃而〃性〃。
但是这种情形在80年代以后的女性写作中得到了逐步的改观。首先是王安忆的〃三恋〃,在王安忆的〃三恋〃中,我们看到女性主人公性意识已经不是那种羞羞答答、欲言还羞的了,她们选择了肉体的快感,因为对肉体的快感的渴望而真正地陷入癫狂之中。进入90年代则出现了陈染、王静依、林白、海南等新生代女性作家,如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以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在北方某出版社的另一个版本中,它被取名为《汁液》)。在《与往事干杯》中,氵蒙 氵蒙 在性上的缭乱局面就是一个象征。她先是接受了老巴父亲的性爱,进而又神使鬼差地和他的儿子老巴发生了恋情──这是一个在性上失去自控而陷于癫狂的主人公。在这一代女性叙事中,性意识成了隐伏在女性主人公身后的中心,小说试图展现因为性意识的觉醒而觉醒了的女性,性是她们游戏诸神的无往而不胜的秘密武器。在她们的笔下,性成了反抗压抑的手段,成了争取解放的工具。但是她们笔下的性就是人类应当的性吗?一个正常的社会,绝对不会用它的体制性力量来压抑人的正常的性,同时一个正常的性意识中,也不会将性的放纵理解成反抗压抑的手段,性就是性本身――它不是女性自我解放的手段,也不是社会压抑女性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将目光拉到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批70年代生作家身上来,他们是魏薇、周洁茹、棉棉、卫慧等,在她们的笔下女性的癫狂状态已经不再是反抗压抑的手段,而仅仅是自我放纵、自我接受的产物。90年代的癫狂症候在她们这里获得了文学的表达:嬉皮士(责任重构)、麻药文化(身份重构)、俱乐部制(亚文化重构)、另类方式(少数者重构)、摇滚、感性本位……这些既是癫狂的内容,又是癫狂的产物,进而成了70年代生女作家写作中的核心景观,她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存在的空间,找到了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症候的温床(或者说我们构筑了这样一种文化空间):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空间,在这里人们释放感性(肢体在摇滚节奏中疯狂地独自起舞仿佛不再受到智力的控制),驱逐灵魂(灵魂在酒精的作用下糜醉了睡着了)。癫狂成了70年代生中国女性写作最好的舞台。
现在,癫狂已经失去了它反抗的意义,而只是放纵、恣意的结果。这一点上新生代作家王静怡的写作可以和她们比较。王静怡在小说《反动》中所展示的是〃虽然已经开始腐朽,却如此强大自信的生活。〃因而可以说,王静怡小说的核心景象依然是理性的,在王静怡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她的成长过程里,欲望被视成罪恶,压到最低点,她一心只偏激地注重柏拉图式情感的精神,即使在两个个体杰出的那个层面上,她神经质的脑袋里充满的也只有思想,另外,顶多还有一点让她羞于承认的浪漫情调。〃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主人公在恋爱的过程中紧紧地提防着自己和对方的身体,她拒斥那种〃只要稍不约束,便可随处遭遇的激情〃,因而她愿意将恋爱限制在电话里〃以控制爱情的盲目性〃,防止自己因爱而癫狂。而这一切在70年代生女作家的身上就极为不同。魏薇在《一个年龄的性意识》中写道:〃我们是女孩子有着少女的不纯洁的心理。表现在性上仍然是激烈的拚命的。我们反而是女人,死了,老实了。〃这种情况在卫慧的《像卫慧一样疯狂》中也可以见到,作者在写到手淫时如是说道:〃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趁我还年少时的激情,我愿意!〃这种对性快感的直接认同在其他场合也比比皆是。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生女性写作对王静怡、林白、陈染们构成了挑战。癫狂已经是癫狂本身,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理由。又如,棉棉《九个目标的欲望》小说流动、飞翔、迷乱、慵懒而又颤栗感觉,这是一种由饥渴感、失措感、失控感武装以来的癫狂美学。
当然压力并没有解除,意识形态话语并没有在以〃性〃为武器的癫狂面前土崩瓦解。中国女性写作依然在旧道德的攻击之中。瓦解旧道德不是感官的力量就可以达到的,只有道德可以和道德为敌:这里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是否在她们的书写中建立了另一种新的道德,以便和旧道德抗衡。
纵观上述过程,我们发现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癫狂史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以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为代表的为了女性社会解放而佯装癫狂的阶段,佯癫实醒的莎菲女士形象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忧郁症患者哈姆雷特的东移,它是〃五四〃启蒙文学大潮风起云涌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以陈染《与往事干杯》、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为代表的为了女性的身体解放而佯狂实癫阶段,它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它以性为突破口,将缭乱的性当成了女性实现身体解放的秘密武器;以棉棉《九个目标的欲望》、卫慧《像卫慧一样疯狂》为代表的为了癫狂而癫狂的阶段,它是女性癫狂写作的极端化,癫狂已经不再是追求〃人性〃解放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是为了追求极限体验、高峰快感。在此,中国女性癫狂写作由追求解放的产物变成了追求放纵的产物,走到了自身的反面。
穷人的道德地位
而历史已经在这个过程中遗忘了二者的因果关系―他们到底是因为道德上的欠缺而贫穷还是因为贫穷而在道德上有所欠缺。常常人们认为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但是,历史上,穷人在道德上居于劣势。例如贫穷在大多数的时候被认为是懒惰、愚钝甚至赌博、嫖妓、滥吃、酗酒等道德恶习的结果,因而,穷人意味着道德上的次等。
这一点在经过马克思主义的颠覆以后就变了过来。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天平上穷人居于优先地位。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富人的富裕是来自于他们对穷人的剥削:一方面这意思是说,富人在富裕之前就已经在道德上犯下了罪孽;另一方面则是说,穷人越勤劳意味着他越是贫穷,因为他被剥夺得更多。因而穷人为了达到富裕,首先要做的不是勤劳,而是不勤劳―消灭劳动―消灭了富裕阶级赖以存在的剥削劳动,那么他们就消灭了自己贫穷的基础。因为不是勤劳将使他们富裕,而是消灭勤劳。
这就是鲁迅在他的《一件小事》中所阐释的思想。车夫的道德对知识分子构成了拯救。穷人在道德上优于富人。
钱钟书是个反启蒙的高手
最近看了《当代作家十批判书》,对其中关于钱钟书的批判颇感兴趣。我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