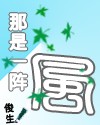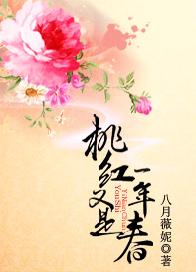悲愤是一种病-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王朔呢?他恰恰相反,他无视一切文化人的自我优越感,他对一切〃孔一己〃主义者都给予无情的嘲讽,他自称是最没有文化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饰、浮泛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他使文人斯文扫地。他常常对〃教授〃这个称呼不屑一顾,甚至充满敌意,他的小说没有诗、词、曲、赋,他也不在小说中谈论音乐、绘画、文学,他自己在做文学可是却将文艺看得一钱不值,他只写生活本身,从来不在他的小说中塞上不伦不类的〃文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主义者。
金庸用一种半文半白的语体写作,对于中国大陆的阅读者形成了一种语体上的陌生化效果,猎奇主义的阅读者自然对此感到折服,而实际上,金庸是在以此炫耀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他在用一种知识分子的语言写作。而王朔,他以一种真正的民间的口语写作,他是老舍,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语言大师是的当代传人,他将一种京味的、民间的语言搬到了小说中来,他毫不做作,在这方面,王朔的小说在语言上完成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一种即不同于意识形态体制语言,又不同于知识分子书面语言的小说语言在他那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就语感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南方作家在汉语语感上大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要么是欧化味道太重,读起来像是翻译作品,要么是方言味太浓,巴金、鲁迅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金庸就更不用说了。
王朔,我得说王朔是语感极好的作家,他的语言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他的语言是诞生在城市民间的,是丰满的、健康的,富于生命活力的语言,没有假士大夫的腐气,没有假知识分子的酸气,没有小女人的鸹气,也没有老男人的霸气。他的颠覆性写作完全来源于他对语言的良好直觉。这一点金庸是比不上的。
在金庸的笔下是见不到平民的身影的,金庸只会描写各种各样的大侠,杨过、张无忌、陈家洛、令狐冲、郭靖……这些远离人间烟火在空中飞翔的英雄们的确让一部分人感到振奋、感到豪情激荡,金庸那越过凡人的头顶投向宇宙的视线的确使一部分人找到了寄托,仿佛神圣的精神境界,英雄的神勇气概,尊严的生活面貌一下子就来临了。但是,当我们放下金庸的书,这些又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于是乎,要欣赏金庸就得成天生活在金庸的小说里,要拿着金庸的小说手不释卷,当我们从金庸的虚无世界中跌落出来,我们会发现金庸原来给我们的只是一块充饥的画饼。与之对立的是,王朔的笔下总是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小人物,他们没有骄人的武功,没有惊天的伟业,但是,他们是脚蹋大地的人,他们生活在〃生活〃之中,王朔正是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关心的是是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底层,被这个世界压迫,有些失措,有些虚无,有些百无聊赖、不知所以,但是却真诚、热切、善良的人,王朔的笔触在嘲讽和讥笑中包含着深切的同情,例如他的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隐就死》、《我是你爸爸》等,无不如此,――这些都是小人物的生存悲剧故事,写得非常感伤,作者是让人含着泪笑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读小说的,在王朔那里虚无只是反抗压抑的手段,痞味只是反抗道统的武器,而他们却将王朔本人读成了虚无主义者和痞子,在我看来王朔正是那些道德虚无主义者的敌人,政治痞子的敌人。我常常能从王朔的笔下读出痛苦来,王朔对小人物的生活的观察和描写是多么的深刻,对小人物的情感状态的分析是多么细致,没有对底层的真切认同,他怎么呢写得出来?
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绝大多数是不愿意面对严酷的现实的,他们更愿意躲在金庸的桃花园里自我陶醉,也不愿意来到王朔的现实中面对自身,他们不是没有鉴赏力,就是缺乏勇气,因而他们选择金庸这个花枝招展的桃花园主,而不愿意选择王朔这个将生活的面纱撕碎,让生活赤裸裸的面对我们的人。带着真理而来的人将为我们所唾弃,而带着迷汤而来的人将大受欢迎。
从纯文学的角度,我们说金庸没有摆脱古代武侠小说的范畴,在小说结构方式上没有摆脱章回体小说的格局,在语言上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贡献,而王朔却创造了他独特的王朔体语言风格,他在描写文革后一代青年、小人物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方面对当代中国文坛是有独特的贡献的。所以,笔者在社会价值观上对王朔取理解的立场,在文学观念上站在王朔一边。但是,就金庸和王朔的争论,就事论事,我反对王朔的刻薄,赞成金庸的雍容大度,王朔有理由存在,不等于说金庸就必须被罚下场。
再谈王朔
今年年初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是比较金庸和王朔的,我的看法是金庸是个贵族主义者,他笔下最有神采的形象都是些奇人、伟人,平民生活的场景是没有的,而王朔是个平民主义者,我的理由是王朔的读者一直是在底层的大众中,王朔一直没有得过什么来自体制的奖项和夸奖,王朔的立场是站在平民方面的,他只是写大众和平民的生活,那些在社会的底层生活着的小人物,如果这样的人还不叫平民主义者,那么谁是平民主义者呢(读者有兴趣可以翻阅《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卷》2000年第3期转载)?
最近看到王彬彬兄发在《粤海风》杂志2000年9、10月号上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流氓文化之王朔正传》,对于文中的有些意见不敢苟同。
对于人类来说,流氓和英雄本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历史上刘邦、陈胜就是由流氓而英雄的例子。这方面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有过相似的看法,鲁迅和周作人、林语堂都感到正人君子是不可信赖的,而青皮到反而有点儿可爱之处;如果我们细细品位一下福科――这位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家,我们会发现他的思维倒是和上述三位中国思想者有点儿相象;这些隔着大洋,甚至隔着半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看法?理由很简单,在文明进化的历史中,那些异质因素,常常会被正统定义为流氓,然而没有这些异质因素,没有他们对〃正统〃的不断的颠覆,历史就不可能进步。
古往今来,那些为正统所承认的正人君子其实都是因为维护正统才得到正人君子的称号的,人类如果只有这些人,如果只有维护正统的正人君子,而没有颠覆正统的流氓,人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难以想象,但是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人类文化永远只能停滞在某个〃正统〃中,永远不会有什么变化和发展。
想一想,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时候,他的脸上写着什么呢?流氓。想一想张志新,被割断了喉管的时候,她的脸上被写着什么呢?流氓。对于正统来说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是流氓。流氓是正统加给这些人的最高侮辱,也是最巧妙的侮辱,以至于常常这些人所挚爱着的人民也认可了他们〃流氓〃的称谓。然而对于平民来说,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英雄,〃流氓〃是英雄的化名。
其实文化流氓和文化英雄只是一墙之隔,问题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有的时候,文化流氓就是文化英雄的别名。
不过我还是想暂且尊重一下对〃流氓〃这个词汇的传统用法,以便能和王彬彬兄在同一个语义下讨论问题。王彬彬兄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论证王朔没有〃平民意识〃,而是〃大院文化〃的继承者。他的有些理由是用不着反驳的,例如他说王朔〃出身于大院〃,这是典型的唯出身论,出身于〃大院〃并不是王朔的耻辱,甚至出身于〃大院〃还是王朔得以摆脱〃大院〃立场,同时又超越一般下层平民,为下层平民鼓呼的提供了可能,平民自身之中是难以生出自己的代言人的,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就是这个道理;又王彬彬说王朔描写的大多是〃自己这样的大院子弟〃,这个论据是不成立的,其实王朔的小说真正以〃大院子弟〃为主人公的并不多。进而言之,即使是以〃大院子弟〃为描写对象,他也是用平民的眼光、视角来写的,他正是以此写出了平民的意识。
我想王彬彬兄还混淆了〃平民身份〃和〃平民意识〃两个概念。
〃平民身份〃和〃平民意识〃是两码事,不等于说有平民身份的人就一定有平民意识,进而平民意识也不等于说就是认可自己平民身份的意识,事实上恰恰相反。真正的〃平民〃,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最底层的人其实并不想做一个平民,只有那些不是平民,也不会做平民的人才假道学地说自己想做一个平民,对于假道学来说,平民只是一顶炫耀自己的帽子,而对于真平民来说平民身份则意味着要被户口定死在某片土地或者某个街区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地在大地上行走,仅此就够了,更无谈贫穷、屈辱、艰难、苟且、无望、无奈、无聊等等这些平民注定要面对的东西了,所以真正做一个平民是很痛苦的,它一点儿也不光荣,相反耻辱得让人想死。王彬彬兄来自〃大院〃,他说对〃大院〃有点儿了解,而我要说我来自农民,我对农民也有一点儿了解,农民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平民,但是在农民的心目中,他们的平民身份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他们倒是以摆脱平民身份为骄傲,谁家的子女上了大学,谁家的子弟转了干,他们无比欢欣,简直要谢天谢地了。
真正的自觉了的平民,其平民意识是以摆脱平民身份为中心的。如果一个平民,他认定了自己的身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身份,他对自己的处境一点儿不满也没有,一点儿改变自己的处境的动力都没有,要么就是他已经在精神上被〃贵族〃彻底地奴化了,要么就是他天生就是个做奴隶的胚子。当然,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大多数时候是生活在〃做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两种处境的交替之中,不做奴隶的欲望是很少的,所以中国人的平民意识从反义的方面说就是奴隶意识。从这点出发,王朔试图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境遇,试图通过造反摆脱平民处境正是正面的〃平民意识〃的体现,这恰恰说明王朔是个平民,甚至他还是一个具有先进平民意识的平民,他还没有被奴化,还没有甘于平民的地位,他的灵魂还活着,也就是说他还有一点儿人性。
王彬彬兄对王朔的第二个批判是,王朔鄙视知识分子,这似乎充分说明王朔是个流氓了。老实说,我也是个知识分子,我有博士学位,我有副教授头衔,然而我比王朔更鄙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妥协、屈从、委琐、怯懦、动摇,没有立场等等的代名词的时候,〃知识分子〃这个词用来骂人还可以,我不知道王彬彬兄何以对知识分子这个词耿耿于怀,想一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以及角色形象,难道这个词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王彬彬兄自己不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我没有记错吧)吗?那篇文章的批判精神我是完全佩服的。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只有李逵这样的人才能做文化英雄,只有《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才能算文化英雄,如果我们将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正面的词汇,那么请允许我说王朔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代表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有的最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为什么?两个理由,他对平民精神品质中美好之物的热爱,他对权势力量的李逵式反叛。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一下王朔,我们就会理解他在爱什么,在恨什么,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王朔和王小波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他们正好代表了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战斗风格,鲁迅在当代有什么传人的话,一个是王小波,一个是王朔。只是王朔,他隐藏了自己,他痞,他流,然而,如果没有这些,王朔,他能干什么呢?他就真的成了王彬彬兄所希望的知识分子了。而那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王朔却只有一个。
是〃后现代〃还是〃后理学〃?
虽然没有王岳川先生那样作〃后学大师〃的资格,但是我自忖英语还会读一点,对后现代理论也就知道那么一点。可是也就那么一点点就使我觉得王岳川先生的后学有些不对劲,无奈水平低想不通其中的结症,听到邵建先生〃后现代不是主义〃的说法才恍然有所悟,后现代是反中心、反元叙事、反霸权,主张边缘性的,怎么可能是〃主义〃呢?我终于有些开通,原来王先生是一不小心将后现代搞成了一种中国式样的〃主义〃了(〃在思维论上,'后'主义似乎更应……〃(见王先生《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南方文坛》1997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