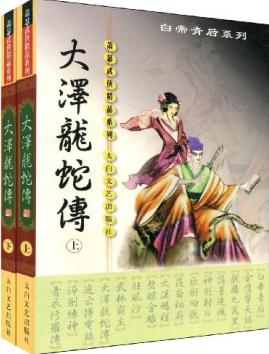阙影十二剑-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年前,他就曾被五鼠误会过。涂善既是存心挑拨离间,该承受的自然是躲不过。世事纷繁复杂,过后也就忘了当时的苦楚。反正入了公门,在刀口上滚搭的,不只是身,还有心。
然而即便是让他现在回想,能记起的,也已经不再是几只老鼠冷嘲热讽“三脚猫”的语调,亦或遭到怀疑后,自己面对同道中人却百口莫辩的狼狈样子。这也许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或者说,更有意义的记忆应该是怎样更快地摆脱类似的被动局面,让江湖朋友重新信任他,而不是去纠结那些过往。
……何况,那些被误解的记忆,也并非全都那么糟糕,比如……
展昭想到这里,侧目看向一旁。白玉堂正在三尺之外,借画影光芒打量着这间店铺,忙里偷闲,信步悠悠。自从认识这只老鼠以来,他一直就是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世人皆知猫鼠不合,然而当他挡开四鼠护我,当他两次救我于负伤之时,当我们并肩御敌,同进同退的时候,倒让人生出错觉——想是这猫鼠之争,也该到此结束了吧;也许有一天,不必为什么救太子、查冤案,闲时街头遇见,亦能相邀同饮几杯,天南地北谈谈说说呢。展昭并非刻板无趣之人,白老鼠,若我仍在江湖,定要交你这个朋友的。
……可惜了。
柳青峰一出现,你便如此轻贱于展某,那些能让我略感欣慰的过往,仿佛不曾有过一般。罢了!庙堂与江湖既然殊途,也必定不能同归。只怕是你至亲之人,一旦进了官府,也是一文不值的。展某人被冤枉,既然已不是一次两次,又何必再去计较。
不过,这一回,不知为什么,心中竟比当年被阿敏误会还要不是滋味。日间,二人与柳青峰在茶楼喝茶,自己好心好意地提醒那人,小心中毒。这份警觉在自己是不能吃第二次亏,可到了他那里,倒成了小人之心!这家伙喝完茶后还得意洋洋地“姓展的,毒在哪里,哈哈”,真个笨老鼠!似这般蒙蔽下去,小命儿什么时候没了都不知道。
也就是这一声“姓展的”,勾起了展昭的怒气和傲气。如果说两年前遭到误会后,是用不作为来应对的,那么今日,他竟是要有所作为。
白玉堂却没发现展昭在盯着画影自个儿较劲。他溜达了一圈,复又坐回窗口,只听雷声隆隆,大雨将至,街上一个人也无。四哥多谋,巧得是猫儿偏也那么多心机。柳兄与展昭,一个是豪气磊落,一个是心事重重。五爷我见了那个便觉得爽快,见了这个便觉得憋闷。这不,刚才那一本正经掏令牌的动作,比两年前更顺溜了。官府的狗腿子。
雨来了,衬得葫芦镇宁静异常。
白玉堂拍拍大腿:“白等啦,走吧!”
“这是你四哥之计,你若不信的话,随时都可以离去。只是五鼠互不信任,令人笑话。”
又等了一会儿,柳青峰终于来了,却又被缠住了。白玉堂几次想现身,都被展昭拦下。
白玉堂见柳青峰不入当铺,心下轻松不少:“你和四哥都猜错了,柳青峰根本不会进来。”
“好戏还在后头呢,”展昭轻拍他的肩膀,“再忍耐一下。”
每到关键时刻,白玉堂总是轻而易举地信了展昭,就好像之前全然没有轻而易举地鄙夷他一样。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心底最佩服的,便是关键时刻的展小猫。就比如现在,猫儿扶住他肩的时候。
那一头,蒋平按捺不住,跳了出去,朝柳青峰呼喝起来。
“四哥柳兄要打起来了,我一定要去劝。”
再一次被展昭按住:“放心,柳青峰绝对不会在双双姑娘面前出手的。他贼得很。”
不一会儿,辛苦等待便收到了回报。柳青峰没入当铺,可是毕竟有人闯进来了。眼见得那所谓媒婆、新郎低声交谈中,冒出一句“柳大人”,白玉堂几乎蒙了。柳青峰果然可疑?他不禁望向展昭。
猫儿接过他的目光,不客气地白了一眼,伴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白玉堂心里咯噔一下,说不出什么感觉。似乎不全是被嘲讽的尴尬,而是带上了落寞滋味。
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到魔女教基地那深深的谷底。那是一个千岩万转,云雾缭绕的清秀山谷,渌水澹澹,林木葱郁。假使白玉堂不是心中怀着无数疑虑和不安,假使展昭不是想起了上次身陷此处的不快,这景色应该是完全值得迷恋的。
白玉堂眼中看到耸立的汉白玉人像,耳中听到“新郎”的解释以及展昭那句“若不是有个双双,你早就死在柳青峰的手里”时,那憋闷的感觉呀,比跟这刻板展小猫在一起的憋闷还大一千倍。
直到柳青峰果然现身之时,所有的疑虑和憋闷,才有了爆发的机会。苍翠密林中,一队黑衣人头戴面具,在柳青峰的号令中杀将过来,白玉堂青筋暴起,画影出鞘,忽然发现身旁巨阙亦是堪堪同步,相依相佐,心中顿时有了安定感觉。方才的焦躁情绪被压住了,剑招重新狠辣凌厉起来。
喽罗打退,面对正主儿,双肩一并,一瞬间竟似有暖流入胸。忽然觉得,不论胜负生死,若能留住这一瞬,倒也不错。至少此刻,展小猫既不刻板也不嘲讽我,站在一起觉得舒服多了……
这只不过是白玉堂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却不料老天还真和他开了个玩笑。柳青峰金蝉脱壳,苗疆毒雾一出,猫和老鼠又像上次黑林中一样,双双栽倒。
……
寒冰谷中,昭白二人被重重摔到地上。
若是在平时,白玉堂身上受辱,嘴上一定要骂几句,至少会狠狠地怒视敌人。可是今日,虽然尚有力气,却是一点使用力气的意愿都没有。
展昭却开始察看这里的形势。寒冰谷处于山地至阴之地,地势比山外平地还要低出许多,寒气自然封在谷底。山间溪流,除了流向外河的,都汇聚到这低洼处,渐渐凝成坚冰。不过这个洞穴倒像是人工开凿的,不仅方整有形,下宽上窄,而且顶上通透,甚至,透过高高的洞顶上浮动的云雾,依稀能看到青翠可人的山色。从谷底仰望上空,好似羊脂白玉与玲珑翡翠相接……这个美丽的冰宫,竟用来当牢狱,真是玷污了她。
正察视时,他隐然感到不对劲。
白玉堂倚在冰凌上,也察觉到了寒气中的异样。“苗疆的人,哪里都忘不了使毒。”话刚一出口,对着展昭的眼神,便又无语了。此刻展昭只是担心他从“新郎”身上所过西域剧毒未解,又中新毒,因而眉头紧蹙;在白玉堂看来,却想起茶肆中“姓展的,毒在哪里”那句话,心下歉然。
展昭不知道他的心思,只道:“白兄,你我此时须得养气祛毒了。”
白玉堂也试着静下心来,眼观鼻,鼻观心,聚集内力,不再同展昭说话。可是意念刚到,不知怎的,头脑忽然一片混乱,眼前浮现的尽是柳青峰那神定气闲的模样,完全无法入静,甚至牵动内息,胸口一阵憋闷,不禁“啊”地一声叫了出来。
展昭扶住他,“你怎么了?”
“好像是新旧毒力同时冲击脏腑。不碍事,只是不能运功了。”
展昭一急,就要帮他,被白玉堂拦住:“你自己也是病猫一个,还怎么助我。你自祛你的毒吧。”
无奈,展昭自己入定。白玉堂无心打坐,索性懒散地靠上冰柱,不再去关注寒毒,头脑中所想,尽是柳青峰。从救双双时初遇,到陷空岛还剑种种情形,这会儿回想起来,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即使是替自己解毒的事,也是江湖人常会做的,何况当时竟那么巧,完全值得怀疑。真说起来,他们无非是萍水相逢,“意气相投”罢了。要说情谊,自己多少朋友不比他强?比如多年相伴的几位哥哥,再比如……
他看向身旁。这张面孔已经很熟悉了,而且,平心而论,并不那么讨厌。
展昭将大小周天运行一遍,知道仍身处毒中,不能从容调理,便住了。睁眼一看白玉堂,吃惊不小:这白爷颓然坐着,面色苍白,一手支颌,惨笑着望向自己,全无斗志。
“白兄!你这是……”
剔透的冰晶把白衣衬得愈发空灵。浅笑凄然,却仍不改风流韵味:
“五爷只怕,今日猫鼠要死则同穴了。”
“胡说些什么。”展昭用猫眼狠狠地盯着这白老鼠,气不打一处来。冤枉了这么些天,刚刚解除误会,这人却说出如此要死要活的绝望话,简直是有意和自己作对。见白玉堂嘴唇干涩,中气不足,展昭心中一动,把手按在他督脉上。
“你干嘛?白爷说了,管好你自己就……”
展昭才不管他说什么,硬是运息一探,心中方才了然。这家伙根本不是什么“新旧毒力同时冲击脏腑”,而是心念庞杂,真气走了岔。若不是因为中毒后功力大减,只怕早就走火入魔了。
“展昭,白玉堂有愧于你。”
忽然听得这句话,展昭一愣。这一本正经的语气完全不似陷空岛白爷的风格啊。
又听他道,“那人纵然狡猾,我也难辞其咎……那天夜里,在姓柳的面前,我指着你说卑鄙之徒。现在想来,柳青峰一事,恐怕是白玉堂这辈子最大的笑话。”说完,双唇一抿,脸色更加苍白。展昭看见,知他是内伤加上气郁,正强忍着不吐血,于是连忙帮他顺气。
此刻白玉堂竟说起这些个颓丧话。展昭一转念间已然明白:这分明是交待后事的口气啊。看来,要打消他心中的自责,非得花点心思不可。一边心里想着,一边道:“你放心,蒋四侠知道内情,只要他有所察觉,应该会说服众人前来相救。”
白玉堂苦笑着摇了摇头。“四哥势单力薄,而大哥他们因我之故,已深信柳青峰而不疑。此地隐蔽,谁人来救?”
展昭本来想说“包大人定会设法”,自己又觉出不妥。眼下转移这耗子的注意力要紧。他抬头一望,冰壁上倒垂的两条长长的冰凌映入眼帘。于是对白玉堂道:
“白兄说的也是。看来这次想要脱身是不能了,左右是一死,展某也是无心运功。只可惜此处无酒,否则与白兄大醉一场,也不枉此生了。”
“嘿嘿,若是此时有一坛女儿红,我便醉死在这里,也不冤枉。只是猫大人被我所累,死了不值。你还是赶紧坐下调息吧。”
展昭不应,上前把那两条冰凌扳了下来。
“没有酒,有剑亦是美事。与白兄多次交手,却没有机会细细切磋。此时难得空闲,白兄,肯赐教否?”
巨阙和画影都已经被人连鞘收了去,这虎落平阳,临死时身旁无剑,确是一件憾事。白玉堂仰头一笑:“猫儿,真有这样闲心啊?”
展昭也是微笑不语,眸中明澈见底,一幅不容置疑的样子。臭猫难得这么可爱,老鼠也被他逗乐了。“行,白某奉陪。”
“不用调动内息,你我坐着比划就好。”
白玉堂笑。看看两把“剑”,虽然短了点,外形倒还够格。“这个亮些,像画影,我要了。”
展昭便擎起所谓的“巨阙”,盘腿坐好,倒转冰凌,向前一拱,道:“请!”
白玉堂忍住笑,也是照样学样地揖了揖,两个人便面对面交起锋来。
昭白二人平日所持宝剑,都是非常沉重之物,配合上乘内功,得心应手。此时他们身中慢性毒药,内力损失不少,尤其是白玉堂真气已岔,更是一点内息都调动不得。这会儿坐着耍这冰条子,倒是相配。
白玉堂本来抱着游戏心态,可是展昭的剑招却是层出不穷,虽不凌厉,却一招一式甚是认真。原来南侠对于武学有很高热情,只是自入公门以来,殚精竭虑,没有功夫悉心钻研。平时动武也是见招拆招,一点儿也不考究。这会儿他却一反常态,举手皆有法度,方寸之间丝毫不差,白玉堂不由得暗暗称赞,也即认真起来。眼看拆了三十余招,双“剑”仍没有相碰,而展护卫似乎有意要让白五爷多动点脑筋,手上没有一剑重复;白五爷呢,本就是率性之人,既然开打,便也迎难而上。一时间,冰谷中战气腾腾,宁静中自有一份激情。
再拆二十余招,白玉堂不占上风,心下渐急,不知不觉用上了内力,“咔”地一声,“画影”削在“巨阙”的“护手”附近,展昭手中冰凌应声而断。
“猫儿,你输了。”
二人同笑。
白玉堂自然知道,手心热度下,冰凌不能持久,“护手”处必然是这冰剑的软肋。他如此取巧,只是不想再跟展昭认真斗下去。得了便宜,自然笑了出来。
可是他也有不知道的,那便是展昭的笑。他这颇有法度的剑法,乃是师门所授“罡宿剑”,又称“养剑”,共三十六招,每招皆有七种变化,是一套繁复至极的剑法,对敌效果非佳。然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出剑和拆解之中,自然调息养气。以往每每有弟子练功不当,内息难以直接导入经脉之时,只要专心使出“养剑”,须臾就能脱险。白玉堂虽然不知此剑,但是拆解一番,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