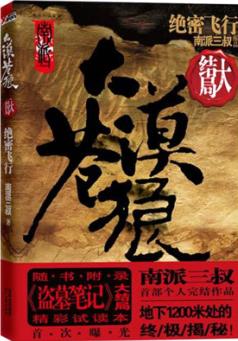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东京人用湿抹布、沙袋和水桶把自己武装了起来,以对付334架造价60万美元的轰炸机扔下数百万磅的致命汽油弹。
桥本良子记得,3月9日这一天刮风,天气很冷。北风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刮着,凶猛似春季台风。正当B—29空中堡垒朝日本帝国飞去的时候,无线电操作者调到东京玫瑰电台。飞行员听到“烟雾迷进了你的眼”这首歌曲时,都相互交换着眼神。接近午夜,一位帝国总司令部发言人在电台上提醒东京居民,第二天,也就是3月10日,要举行建军节的庆祝活动。在东京市中心将举行游行。他鼓动听众提起精神,最后他说,“黎明前最黑暗。”
几分钟后探路轰炸机到达东京,在500英尺上空呼啸盘旋,扔下了汽油弹后,整座城市被勾画出一个燃烧的X型图案。
他们挑选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充当先遣队员,提前45分钟出发,然后轰炸机组的成员才出发。在谈到探路者时,飞行员查列·菲立普斯说道:“他们在地面上画了一个燃烧着的X型,将其分割为四部分,我们到达之后,便在指定的一部分中投下炸弹。”
此后轰炸机3架一组到达,对准起火点X型轰炸,B—29轰炸机有一种定时装置,叫做定时曝光控制器。每隔50英尺便投下500磅燃烧弹,这样每架飞机的载弹量可以覆盖350英尺宽,2000英尺长的地带。”
334架飞机扔了8519枚炸弹;每枚500磅重。这些炸弹在东京上空2000英尺处爆炸后,释放出49。6万枚装有凝固汽油的6。2磅重的管状燃烧弹。这些管子带着小小的降落伞,慢慢的向下飘落。
在关岛,柯蒂斯·勒梅正坐在指挥室里抽着雪茄。
他对助手说:“我正在焦急地等待。”“会出现许多问题,我睡不着。通常我睡眠很好,可今天晚上不行。”
接着,关于轰炸的消息传来了:“清晰地命中主要目标,看到大片的火海。高射炮火力不强,没有飞机拦截。”直到第二天晚上侦察飞机携带照片返回,柯蒂斯才知道详情。他看着照片咕哝着,像是从嘴角挤出来的声音,“看上去不错。”然后,动了动雪茄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17岁的竹市美代子听到防空警报就跳进了家用防空洞。“我看见美国飞机就像下雨一样投掷燃烧弹,天空像礼花形成的尼亚加拉瀑布。”她说,“在防空洞里还有人说‘真好看!’”远处,耶稣·索非娅大学的山上,古斯塔夫·比特神父在想那些燃烧弹带着降落伞下落的情景,就像“银色的幕布,从天而降。就像在德国圣诞树上悬挂的银箔那些银色的飘带一触及地面,红色的火焰瞬间燃起”。丹麦的外交官拉斯·蒂里兹后来说道,燃烧弹“不是直接落下来的,而是慢慢飘下来的,像银色水流的瀑布。一枚炸弹就能炸毁大片区域。炸到哪儿哪儿就寸草不留。”
千百处大火燃烧起来,“风就像火上面的盖子,将热浪压低,迫使烈火向四处蔓延。而不是向上喷发。遍地是浓烟和火星,白热化的阵风顺着狭窄的小巷,呼啸着吹来。”一团团的烈火瞬间融会成火的旋风,像龙的火舌四处翻腾。30分钟内消防队全垮了,“在一个消防站,只剩下烧焦的尸体和一辆被火烧焦的消防车。”一名消防队员回忆道:“我们进入爆炸区域时,到处灯光闪烁,像白昼一般明亮。”
柯蒂斯的预感是正确的。
“原来日本早就配置了大量的防空炮火,但是射程只有5500英尺,”飞行员杰宁斯说,“他们还有许多防空设施,其射程可达1万英尺~2万英尺,甚至2万英尺~3万英尺之间,但他们根本没有建造射程在5500英尺~1万英尺之间的防空设施。谁会发疯在那种高度飞行呢?”
空袭开始时,桥本良子正熟睡着,身边还有一岁的儿子、三个妹妹和父母,她丈夫去值班了。她听到空袭警报,立刻抱着孩子跑进自家的防空洞,父母亲和三个妹妹,一个19岁,一个17岁,另外一个14岁,也跟了进去。
她父亲立刻感到此次空袭与以往东京所经历的小的空袭相比决然不同。“待在这儿很危险,我们快跑!”他对妻子和女儿们喊道。
“我把孩子拴在背上,盖了一件孕妇服。”桥本良子告诉我,“拿着尿布、牛奶,以及重要的家庭证件。”她还没明白,这是一个逃命要紧的夜晚。
全家躲在高架铁路下面避难,但几秒钟后,她父亲叫道,“快跑!”
“我朝西看,那里红彤彤的一片,就像日落,”桥本良子说,“我看见许多火柱拔地而起。许多架B—29轰炸机在扔炸弹,飞机飞得很低。我想会不会击中电线杆,飞机个头那么大,机肚都被火光映红了。”
“几天前B—29轰炸机在天空中拖着一条尾巴像小不点。”她告诉我,“可是那天晚上它们那么大,那么多的汽油弹投向地面,燃烧弹听起来像火车呼啸而过,城市黑夜如同白昼。”
“火随风四处蔓延,”她说,“是一场夹着火焰的风暴朝我们袭来。”
19岁的妹妹惠子决定在铁路下面守护家里的财产。
六个家庭成员全从奔腾的烈火中逃了出来。桥本良子背着她的小男孩儿,她的家人“全都奔跑着逃离大火,穿过浓烟,有些地方烟浓得看不到10英尺之外的东西。他们边跑边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她觉着她应该拉着妹妹悦子的手,但17岁的妹妹双手紧抱一罐大米,以解家庭燃眉之急。她跌倒在后面。在人群的推拥中,桥本良子喊道:“小悦子;你没事吧?”
“大姐,等等我!”悦子喊道。
“我们离得越来越远,”桥本良子流着眼泪对我说,“我在人群中把她丢失了。我现在已经81岁了,但仍能听见她的声音,‘大姐,等等我!’”
桥本良子一家七口现在只剩五口。良子背上的孩子不停地啼哭,风和热浪使铁皮房顶整个掀起,铁皮像飞碟般从空中掠过。火花、烧焦的衣服从旁边飞过。
火炮手戴维·法古阿在火焰的上面飞行,他记得“执行任务时要飞行那么低,火燃烧得又十分迅猛,一些物体燃烧的碎片常常飞到我们的炸弹舱里——墙板的碎片、杂物、或其他燃烧过的物体的碎片”。巨大的热浪将飞机冲击到火焰之上5000英尺的高空。“湍流使飞机翻转过来,机组人员身体全部倒过来,”飞行员哈里·乔治回忆说。“想像一下一张纸夹在一大堆树叶中是什么滋味,”“射击手爱德·里凯特森说。“现在想像一下整座城市。”“我的椅子用固定螺栓拴定在地板上,我被安全带固定在椅子上,”无线电员乔治·格莱顿说,“当冲击波袭来时,椅子从固定拴弹出。我被贴在天花板上,身上还拴了一把椅子。”
火的温度很高,“在大火冲近之前,热浪就已经把人击倒或致死,而不是被大火烧死。”热浪温度高达华氏1800度。孩子在母亲背上炸开。街上的汽车“烧焦后像一团卷曲的纸。”
石川记得他和40人一起被困在火中。“这一场烈火,简直是火的地狱,我身旁一位年轻父亲丝毫没有察觉到背上孩子已经着火”,石川说。“外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们被火苗呛死。”
火像波涛一样在街道上翻滚。河道沸腾,人体燃成火柱,像一根根燃烧的火柴。人的脑壳在热浪中爆炸,脑浆在裂开的脑壳中沸腾,闪着令人恐惧的荧光。逃难的人群用脚踩着那些从眼眶里鼓出来的眼球。
美穗跑到一座庙宇中避难。她记得当时的情形,她看到庙里有“许许多多保人平安的神灵的塑像,和庙外的塑像一样,我突然意识到,那是些烧焦的人体仍然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19岁的仁惠看到一个母亲和孩子在跑。“突然火焰像伸出手一样抓住他们,他们的身上着火了衣服烧了,他们趔趔趄趄,然后跌倒在地。没人停下来帮他们一下。”
笠多和两个孩子冲进八信学校,该校因一个大游泳池而闻名。他爬上了屋顶,屋顶上的烈火也向他们袭来。学校教学楼里面,成千人被烤死。“看上去,他们像模特,有的人的面孔呈粉红色。”笠多一直记着游泳池里的景象。“真是令人惊骇,我们估计有1000多人挤进游泳池。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时,水池子里的水漫到池沿。这时里面已经干枯,只有大人和孩子们的尸体。”
桥本良子背着孩子和父母及最小的妹妹跑到河边,他们在热浪卷起的广告牌和土块之间躲来躲去,终于到了桥上。
“人们在桥上被活活烧死,”桥本良子说,“衣服会燃成烈火,大家都用脚灭火,我的头发也着了火,大家都在尖叫。”背上的小男孩趴在她背上像别人一样大哭大叫。
“突然,我听到他厉声尖叫。”桥本良子告诉我,“我转过身来看他,发现孩子嘴里着了火,一团红,我赶快用手将他嘴里的火苗抠出。”
男婴是全家的宝贝。桥本良子把他放在地上,用身体挡住他,她父母亲上去护住她。他们自己用孕妇服盖上,外套也着了火。“
“我们都会死在这儿。”桥本良子记得他父亲这样喊道。
“那时我真想自己快死了,”她告诉我,“那时想到自己要死真是难受。”
“桥本良子,赶快跳进河里!”他妈妈尖叫,“跳,跳!”
“正是三月,河水很冷。”她回忆说,“我抱着孩子,不敢往河里跳。但是,我不得不跳。”
桥上的铁栏杆早已经拆掉,拿去炼铁作了武器。栏杆换成了木头的,也起了火。要跳进去,桥本良子就要先把脚伸到火里,她犹豫不定。
“我母亲把她的防火面罩拿下来套在我头上。”她告诉我,“我们家四个女儿就生了这一个男孩。大家都很爱他。我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大家的情绪很糟。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是我妈惟一的乐趣。我还记得她的头发被热浪吹得竖了起来,附近的火光映红了她的脸,我永远忘不了她那张脸,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良子踏上燃烧的栏杆,抱着孩子跳进河里。
“我从热气中又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她说,“孩子睁大着眼睛,水那么凉,而水上面像火炉。你知道将东西放进火炉里会立刻着火的,当时的情景就是那种样子。”
“我用一只胳膊划水,另一只胳膊抱着孩子,一只木筏漂了过来。我把孩子放在木筏一角,我还划着水,反复用水浇在他头上。我把头浸在水中,不停地又往孩子身上泼水。
“就在木筏右边有一条小船,上面有两个人,我朝他们叫:‘请救救我的孩子。救我的孩子,不要管我。’他们划近木筏,拽上我的孩子,也让我上了船,我们漂向下游。”
这两人救了桥本良子和她的小男孩。她一夜时而醒来,时而昏迷过去,船载着烧焦的躯体缓缓前行。
“我整晚听到哀号,”她告诉我,直到现在我仍然幻听到他们的哀号,哀号呻吟像饥饿的蛤蟆。在我的后半生,我讨厌听到蛤蟆发出那样的叫声。”
康介是一个22岁的学生。他父亲是当地空袭警报员,他坚守岗位,以身殉职。康介跑着,“我朝天上看,看到B—29轰炸机在盘旋,”他回忆说,“他们的飞机被火光映得都变成了红色,那些飞行员看到下面像蚂蚁一样乱跑的人群,一定感到好玩。我几乎都能看到美国飞行员大笑的面容。魔鬼,婊子养的,我痛不欲生。从那以后我开始从心底里恨透了美国人。”
但是这些美国魔鬼飞行员在价值60万美元的飞机里并没有发笑。实际上,他们没有在想伤亡人数。
“我们没考虑平民,”罗伊·科林伍德后来告诉我,“我们担心我们能否驾驶B—29轰炸机赶3600英里的航程,那些飞机并没有某些人想像的那么可靠,我们还担心日本人把我们击落。”
“我们并没有多想我们到底在干着什么,”艾德·里查德森补充说,“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努力干完我们的事情,然后回家。我们只是按上司的吩咐做,我们没有什么疑问。”
“我们没想往人身上扔炸弹,”科林伍德这样解释,“可是当你在3平方英里的区域轰炸21个军事目标时,你不可能既击中目标又炸不死人。”
“在5000英尺高空上,你能闻到血肉烧焦的味道,”切斯特·马歇尔回忆道,“一种香味。我问:‘闻到的是什么气味?’有人回答:‘是血肉烧焦的味道。’”飞行员哈里·乔治反驳道:“血肉是一种焦糊味,很难闻。”
“大概在地狱里看到的情景也不过如此吧。”哈利回忆道,“我们心里很难受,要赢得战争只能这样,特别是全面赢得战争。”
3月10日凌晨两点三十七分,有了清晰的信号。飞行员在东京上空扔了2小时40分钟的汽油弹,他们飞回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