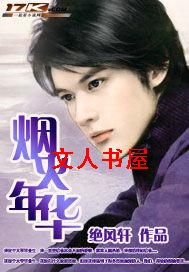������ʮ��-��6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պ������Ļء�������Զ¥��Ϊ�Ͼ��������ڵأ������������ԡ�����������ǰ�����֮���ơ���ʱ��ͯ�����˼������������Ѯ�����Ժ�����ȣ�����ͯ�����ж�ʮһ�ο��еĻ����أ�
��Ȼ����ʮһ�����ϣ�һ�˰��壩������ڱ��ʮ���꣬��������Ƥ������ݿ��ȥ�͵��ص������꣬һ���̳����������������Բ��ۡ��������ֹ�ȥ�ˣ����Ƿ�����ڱ���ڱ��������Գ����֣������ڱ���ͬһ��������ǹ������ġ����ơ��ɡ�����ͯ��������������ڡ���������һ���������������꣩���ˣ�һ�˰˾ţ�����ʮ���꣩��ʮ�����У���ͯ���������ܡ����һ���Ը����ߵ�֪ʶ���ӵ������Ĵ�����Dz�������ģ���������������Ժ����ġ����Ҳ��첻�������ˡ�����Ϊ���Ѿ���Ƴ�������ɽ�֡��������в��������Ĺ�ĸ����ʮ���ҿ�ʼ�عѣ��������ǿ��ѹ����������ʮ����ʱ��һ�˾���������Ҫ���Ÿ���������������һЩʮ��������������С��Ϸ���Ŷ�������ݿ���������һ�ε���������Ȼ��־�ߣ��¾��ɡ�����Ϊ��һ�Ρ��о١��ˡ�����ǰ�����˶�ʮ��ġ���ͯ���������ʱ����ת�����Ƽ��ڡ�����֮�����ڱ��������ԡ����У���Ȼ���ˡ���ʿ����������֣������˵�ģ�������ѵ�����ȥ��һϴ���������ߡ������������ǿ�����š�Ӻ�����ˡ�Ǭ¡��ʿ����
ѧ����ʧ�������ջ�
����Ϊ���������ս�������������ֿ������Բ��ۡ��������ɾ��˿���ʿ������һ�����ã���ƾٿ�����Ҫ����һ�����ˡ��գ���ʵ����ʤ��֮�䣬������н��͡������ԡ����ԣ�����ţ������ԣ������ˣ���Ҫ�����IJ�����ѧʶ������ѧ��ŵ��������ټӵ㡸���������˹��ģ���ѵ�����Ϳ���Ӧ���ˡ��ʶ˳������项���������Ϳ���ʮ�����ѧ������ţ�ʮ�����о��ˡ����о�֮���ǡ�����֮�ⲻ֪��ѧ�ʡ���������ʦ����Ϊ�����෴��������ѧ�ʶ����IJɡ����������Ҫ�������еط��ԵĿƳ��ˡ������н������㺲�֣��⿿�����Ͳ����ˡ��������ܵ��е����ʵѧ����֪�Ƽ������Կƾ�ʱ������ͨ�ľ��ˣ���������ʷ���ϵķ��������洦���У���ƨ�Ľ�ʿ���������Ҳ�����Ͼ��ǹ��ҵ����ѧλ����Կ���Ϊ�����ڡ����ԡ���һ�������ԡ��������ԡ���Ԫ�������Ե�һ���������ˡ�
�ǵ������ʴ���ͳ��ǰ��������˵�����ʱ����ְҵ���ٶ��ǡ�ͩ��Ͱ��������װͩ��֮�⣬���Ƿ����ʵ�ƾ�ʱ����ʿ�ӣ�Ҳ��ͩ��Ͱ�����顢���ԡ�����֮�⣬Ҳ����һ�á�����Ҫ�ƾٳ��������Լ����Բ�����Ԥ���ٿ�������֮��Ҳûʲô��Ԥ���ġ�����Ҳ������ʿ�ӣ�����Ԥ������֮�⣬��Ϊ���������ġ�������Ҳ�Ϳ��Ա��һЩר��ѧ�ߡ�ר��ѧ�߸�����ͣ��ȡ���˹������ͳ�Ϊ��ѧ�ʵĴ���ţ�����Ԫ������������֮��������ר��ѧ��ʼ�տ����������ģ�Ҳ����������Ȫ�ֻ�Ц������ġ����¡�����ʱ��Ѫ������Ҳ�ɸ�������������ġ��ϻʵ��项����ʱ���й���Ȼû��̫��Ĺٰ�ѧ�ã�����Ҳ����ѧ��У�Ϳ�����ͽ��������ѧ��С�ľ���������ġ����Ҵ���ʦ����֣���ž����˰뱲����ʦ����ѧ�ʴ�ľͰ�˽����ѧ������Ժ�����ġ�������ʡ����γ�����ġ���¹������������ĸ�����Ժ�ˡ�
����Ϊ��������������һ���������������꣩ʮ���꣬��һ�Ρ����Բ��ۡ�֮�����˺ܴ�Ĵ̼�������һ������ʦ֮����Ͷ����ʱ�����Ľ�ʿ����ѧ���������������ѧϰ������һλ��ѧ�ߡ�����Ϊ����ѧ�˲��ٶ�����������������ѧ������һѧ�塢���껹�ǿ����˹��������Լ��ġ�ѧ�ʡ�ȴһ����ش�������������ѧ����ѧ���ӷ�ѧ����ѧ������ʮ�꺮������Ȼ��ɵ�ʱ�����ͨ�Ĵ���ֽ¨�����������ʦ��һ�˰˶��겡��֮����Ϊ��һ�����Բ��ۡ��ڼ�������һ������ͯ��ʦ֮��Ҳ��������������С��Ժ����ͽ��ѧ�ˡ�
����Ϊ��ʱ�����Ƚ��������θۡ�������������ͷ����ר���γ��ǡ��������ý�ɽ�¡��ƺ�¥����¹������ʤ�ż���������顢������·�������չ㡣������˶�塢��ٹ���֮�䣬��ѧ���ģ����۹��£�����λ��������ÿ��ͬٱ֮�ϡ����Ӿ��ˣ���ȻҲ�ĸ�ʱ����ż�����ϼ����ʸ�̶�����ѧ����Զ��ѧ�ӣ����ŷ���Ľ������ЩĽ����֮�䣬��Ȼ��һλ���в������¿ƾ��ˣ�������Ϊ��ʥ�˵�һ�Ŵ���ͽ����������һ��������һ�Ŷ��ţ�����һ�ǡ������ʦ������ѧ�����Ĵ��䣬��ʹ��ͯ������ʮ���ˡ�
������Ͷʦʼĩ
ǰ������֮���㶫�»��س�������������ʮ�����ѧ����ʮ����о١����������䣩����ͯ�����ڿ��о���ʱ����������ʱ������������˗������ˣ��˰������������������Ϊ�ޡ��ⲻ��˵�ǵ�ʱ���黪�ϵ�ʦͽ�ѻ������������Ǵ����ģ���֪������λ�¿ƾ��ˣ���������֪�������ӣ����������һЩ��������֮�⣬�����ж��١�ѧ�ʡ���������ھ�������ʢ��֮�������ǿ��ϸ��һ�⡸�ϻʵ��项��һ�˰˰ˣ�����֮��������Ͷ�����£�������Ϊ�ĵ�һ�Ŵ���ͽ�ˡ�
��֮�˿��������������о١�������ͬ����ڣ���һ�꣬����ʮ�����������Ԫһ�˾ũ��꣬ʱ����Ϊ��ʮ���꣬����ʮ���ꡣ������������˵�����Լ���ʱ�ǡ�����Ƶڣ�����ʱ��������֮ѵڬ����ѧ��������֪����մմ��ϲ���������ϡ���ʮ�����������Ǵ���ѵڬ�������֮Ϊ�����������þ�ѧ������ʦͽ����ʱ�Գ��������ʱ�����磨�����ߵ��ӣ�һ��̸֮���������ü�ֱ�ǡ���ˮ��������ͷһ����һ����ʧ���ݣ���Ȼ��֪�����¡���ֱ������Ϧ�����¡����Ӵ������˾;�����ѧ��ȥ����Ŵ�ͷѧ���ˡ�
�������ˣ������������һ�����£����婖�������ijϦ����������ʦ����֮����̸ѵڬѧ����������Ū����Ϧ�����µij̶ȡ��������Сʫ���ף��о�Ի��������Ϊ̽���������̹����ɱ���ᡣ����֮ʦ��������ƪ���롶����ƪ��ʱ����ʮ���ꡣ��˸�̾ʱ����ʮ���ꡣ�����ܻ������������������Ծ������������þ�ѧ����������Ϊ֮����Ϳ���ӡ�����֪��ʮ����Ŀ�ʥ�ˣ��ೢ���˸п�Ҳ������
������Եô˸�ͽ���������Ĵ��������꣨һ�˾�һ������ʮ���꣬��î����������������ӵ֮�£����ƾӹ��ݡ����������ʽ���ƽ�ѧ������Ǻ����崫���ڵġ���ľ���á��ˡ�
��ʷ�߽�֪������ľ���á��Ǻ����������䷨���۵��´���Ҳ������䷨�ĸɲ������������ǿ���Ϊ��ʦ�������������á������Щʲôѧ�ʺ������أ�������������ı�Ҫ��
ʥ��֪�����١���ѧ����
����Ϊ��ʱ�ڡ���ľ���á��У�����������ѧ��������ѧ�ʣ��ܵ�˵���������������ࣺ����ѧ���͡���ѧ������ɽ����������ԺԺ�����ơ�ɽ����������δ�ô�ͷ�֣��������ֽ���Щʲô����ѧ���أ�ԭ���������Թ��ݳ����ֱ��ϣ�ȥ�����μӡ�˳�츮���ԡ�ʱ��;����ۡ��Ϻ������ȵء���硹���������˹���֮��������·֮���ࡢѲ��֮���ܣ���֪�����ι��з��ȣ������Թž�֮�ĵ���֮������������������֮�࣬�˴�����ѧ֮�飬DZ���Ķ�����֮Ҳ�ͱ�ɵ�ʱ���еġ���ѧ���м��ˣ��������Ϻ��Ա����ס��������ꡢ��ʮ������ڣ�������Ϊ���־�������ᣬʵ�ں�����ɽ����˺��ֵĹ۸���ȫ��ͬ�����������Ҳ����Ϊ��ĩ�ᳫ��ѧ�����������ֲ�Ѱ�����Ļ����飬�����ڵص�ʿ��������Ī���ˡ�
������Ϊ�����������ʱ���루�����������룩���飬�������ޣ����������Ϊ���������Ʒ����Щ��Ʒ�������ܵ�ʷѧ��ѧ���������ȿƵ����ݣ����¿ɱ��������˶��Ժ�ġ�����ѧ�̿��项�ij̶ȣ�ë��������̶ȣ���������̸�������������Ȼ��ѧ����̶���Զ�ڡ����С�֮���ˡ���������Ϊ�Ͼ���λ�С�����ʿ���̶ȵ���Ҵ�ѧ�ߣ����dz�����ѧ��ѧ�����¼ң��ر����������������ij���ġ����ļҡ�������һ֪ʮ����һ������������������壬�Լ�����֪�䲻֪���Ͷ�����������д�䡶���ӡ�����ƪ�ˡ�
��ʵ�ⲻ�ǡ����ӡ�һ���˵�ë���������Ļ�ת����˼��ҵ�ͨ�����̿�����֮��ֱ�����յİˡ��ũ������Ϊʱ����Ϊ��ѧ��ʦ��������ʥ����ڼ��ѧ�ˣ�Ҳÿÿ�Ծ�����������Ҫ���ꡢ���Ҿ�Ҫ�����ߣ����Ǻ��в�������֪��ë����������̫�������Ҳ����ҹ������ѡ�������䡶��ͬ�顷δ�����ھ���̾�����������������������ʦ��Ү��Ȼ��˼�۴������ǣ���θ��ϱ��ι������ι���Ϊ��ʦ��������㶥����ɽ��ӡ���Ψһ�ɡ��⡹֮�����Ǿ���ʱ���Ĺ�ϵ�ˡ�������Ҳ���DZ��߳�˵��Ц�������۶ԡ�����ѧ�����˽⣬�������Ҳ�Ȳ���̨����ͷ��һ��Сѧ���ˡ�
��������������ÿ̾�����й�֮���ˣ���û�в���һ���������Ĵ�˼��ҡ��Ľ������νȻҲ��������ŤתǬ�����쵼�����壨ˡ�ҽ���һ�ס����ļҡ����ĵ�����ͨ������������������¡���ƽ�����롸̫ƽ��������һ�������͵ġ��ִ�ת���ڡ�����������һ������ʥ���ͣ�����ɳ��֮�ϣ��ֲ��;�������˼�������֮��ν�����塹Ҳ����˼�롹Ҳ����Ҫ���������ġ����ߡ���wisemen�����ͳ��ˣ�ordinary people���������������š���å��Ʀ����ū�����ۺϡ����项����˼�롹����ʵ�����������项�ȹ��̣���������ۺͿ۵ġ����ˡ���chances��& opportunities�������ڷֶΣ����۶�����֮Ҳ������ר��һ��λ��˼��ҡ��أ�
д�����������Ҳ��Ҫ�桸ʵ�����塹�Ǹ����֮�ڵ���ʷ��ѧ�ң������Ƕ��������ʡ���Сƽʦͽ�����ۣ�˵�㹫�����ˡ����ǡ�ʵ�������ߡ���Ϊ������ѧ������֮�ڣ���ʵ��Ȼ��ѧ��γ���Ȼ������û��ʲô���ռ���������ultimate��truth���ġ��������������ڲ������죬�Ͳ��������ij���֮�С�
��ʵ�������������͡�����ɽ������һ����ѧ�������Ǹ㲻��ġ���һ���������ף��Ϳɲ������ԭ�������ĸ�֮�ࡣԻ��ʵ�����塹��experimentalism��Ҳ��Ի��ʵ�����塹��pragmatism��Ҳ��Ի���������塹��opportunism��Ҳ��Ի���������塹��instrumentalism��Ҳ��
�����ġ�ʵ�����塹��ʵ���Ǹ���ʵ�鱨�桹��lab report�����������������ʵ�����У���������ʵ��Ľ���������ܽ�����������conceptualized��֮��
���ʾͲ�Ȼ�ˡ�����û�н���ʵ���ҡ��������ص�ֻ�Ƕ����ij�������̸����������Ƕ�̸�����塹�������ġ����塹��ȴû�д�����ʱ�й���ʵ�ʡ����⡹�����������ס�ʵ�����塹���ܿ�ľ���λ�ˡ�
�ҹ���ʵ�����塹�ġ���������Сƽ����ġ���è��è�ۡ�����ʵ����һ�֡��������塹���������ǿɱ����ˣ����������塹ԭΪ��ʵ�����塹�Ļ�����ֻ�ǡ�ʵ�����塹���ڡ�ʵ�项���κ�ʵ��������������������ġ��㡸��֮���������ѵ�ʵ�顣���Ե˹���������ֲ��ǡ���������������̫�����Ǹ�����ţ�п�ġ�ʵ�������Ρ���lab��director����ʵ��ɹ���ɼ��������������������У���ŵ��������ʵ��ʧ�ܣ���ֻ�õ���������ȥ�������ˡ�
�����ڱ�����д��ټ��һƪ�ƺ��������ص����ۣ�Ŀ��������ָ����Ҫ����ҹ����������Ļ���̬���йŵĶ���ʽ��ת�����ִ�������ʽ���Ƕ�ô���ӵ��˶�����ʷ����̫�أ�����Ϊ���������е���һ�����ѧ�̶ȵ���ѧ��ʶ����䷨ά�£�������ݺ���������ʧ������֮ǰ���Ѿ����ˡ�����ؿ�����䷨�����ڲ�������Ҳ�����ǿ�ʥ������ѧ�ϵĻ��Ͳ���ô���ˡ������רƪ��ϸ��֮��
��*ԭ����̨����������ѧ������ʮ��������
��������ѧα�����͡��йŸ��ơ�
����Ϊ�ڡ���ľ���á������ڵġ���ѧ�����������ڽ����й�����ʷ�Ͽ���ٵص������Σ�����Щ��ԭʼ�������ԵĶ�����ֵ���ö��ī�ʣ�������ƪ���������һ�ʴ�����
����ľ���á���ѧ�Ƶ��ص㣬��������̡�����ѧ�����Ϳ����ý���ѧ�۵�����չ�����������̿��顶���Ӹ��ƿ���������ѧα�����������Խ���ѧʵ���ǿ��ϱ䷨�ġ�����ν�ĸ������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