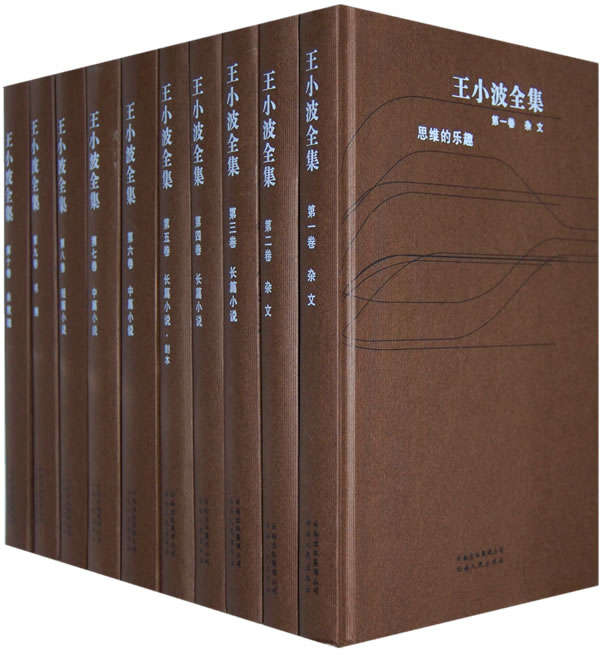牛小冒似水柔情-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然大多东西都已不合时宜,却依旧是难以抹平的记忆,如果讲出来,或还在这世上有一个意义,如果不,那就什么意义也没有了。
()
这张油画没有名字。
画上的这个女人,曾是那个画家的情人。
女人在那个画家死去的当夜失踪。
那个夜晚,到处是黑暗,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
这个画家死时,脖子上忽然呈现出一道绽开的血口,血液从喉管里喷出,他的脸来不及扭曲和狰狞就倒在了地上,连恐惧的表情似乎都已经来不及发出。
能够想象的是,在这股血冲出来的那刻,他是立即就死了的。
正是春天,柳絮满天。
黑夜里,这种物体依旧悬浮在空气中,乍看起是惨白的,泛滥的,令人感到一股难忍的压抑。
同时,在这飞絮背后,万物苏醒,动物和植物静静骚动着。
这种情境更像一个无法解释的古老预言的开始,这样的夜晚,更像是。
再有几年,他大概也该出生了。
与此同时,他的母亲,五十多岁,容貌却已毁了。
她离开他时,他用一种坚定的眼神看着她——这眼神里面充满了渴望——她看着他,举止仓促,不由自主惊慌起来。
他对她说,如果她离开,他就要死掉,在她面前立即死掉。
她对这样的情景似乎并不陌生。
她像关心一个弱者一样和蔼的看着他,满含微笑。
她以这种笑容面对任何人,司空见惯。
他对她说,他相信她。
他又说,他的命是由她决定的。
他拿起一把裁纸的剪刀,对准喉咙处剪了下去,随之他的瞳孔发生惊变,向外猛烈的突出。
但她却毫不犹豫的离开了。
这是结果,必然的结果。
她走的时候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惨烈的尖叫,却因喉管的断裂细若游丝。
这尖细的叫声令她为之所动了。
但她没有胆量回头,随着匆匆离去的脚步声,这尖叫亦消失在茫茫暗夜里。
她身后落满了属于整个春天的白色飞絮。
它们依旧是惨白的,泛滥的,没有丝毫的改变——你可以发现,它们年年如此。在这短暂的星球上,任何事物显得千奇百怪,却依旧按它自身的规律走下去。
任何事情都不可想象,不可猜测,他们虽然重复,但每一次的发生都像初始一样,充满着新奇的色彩。
她感到恐惧,逃走了,不像她的一贯做法。
是的,她的确老了,没有哪怕再多一点情感来投放,不不不,这一切也许从未有发生过。
她这一生躲在这美丽的面孔下太久了,太久了,最后,再也不敢露出任何真实的感情了。
她说。
她满目愁容,看着自己的儿子,久久的看。
她的儿子也抗衡不了这岁月的摩挲,稚气已脱,成年了。
他的母亲现在是一个苍老妇人的模样。
她笔直的身躯端坐在他面前,仿佛正准备接受他的数落一样。
但他没有任何理由埋怨她。
这些不该由他讲。
他问她,还记得后来一段时间,她去往他住的那间屋子吗?
她指着那幅画对他说,不要摘下来,美丽的女人总能够避邪,留着就好。
他说,他从来不信这些,虽然后来知道那是他的母亲。
她冲他温柔的笑着,对他说,都由你,但是留着最好不过了,因为留着它至少还有些纪念的意义。
这些回忆如同影子一样跟在他的身后。
她不像一个母亲,倒更似一个可怖的巫婆。
隐藏在虚伪的面具背后,将她所有的卑鄙挡在儿子面前,对他说,这都是他应该承受的。
此后,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女人的*之下。
他问她,若你不说,我可能将永远也不会知道。
有一天,他得知那是他的母亲;有一天,他惊讶的发现一切他所追本溯源的谜底,竟然是这么荒唐。
这一天真是荒唐的根源,一张画像正对着他的床尾——每天,当他起床,这个女人用仿佛鬼魅一般的表情紧盯着他;而他灭灯即要睡去,她依旧专注的打量着房间的一切。
那是他的母亲呢,直到他搬离那个城市,搬离那个住所。
他的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
他说,令他感到奇怪的是,每个白昼和夜晚,似乎总是缺少了些什么。
那和切的眼神?
这些时间,他时时被一种无形的探索影响着。
然而多年以后,他大概要把它忘记了,岁月如梭,而记忆则更加模糊。
他想起那期间,无所事事独坐在他的房间,他扫视整个屋子,然后感到一股难过,特别的,悲伤的。
他直视着那幅画,忽然哆嗦了一下,一阵阵惊恐侵袭了他,胆小的他想要将它摘下来,却始终没有勇气。
尽管他不相信那些虚幻的东西,但他似乎更没有胆量做出任何改变来。
虽然这也不能说明他的胆怯。
但他必定是犹豫的,永远是犹豫的,对任何事物是一样犹豫着的。
2、如今,他已结婚生子。。。。。。
2、
如今,他已结婚生子了,他母亲的青春,仍似一幅绝美的油画躺在他卧室的大床下面。
他估计直到他死的时候,大概也不会重见天日了。
本来,这都怪他的母亲,这些往事,本该不是这样子。
但事实总与之相反。
他这软弱的性格总令他不由自主去接受,接受一个被时代抛弃的、饱受摧残的历史记忆。
他被这件事所深陷,所残杀。
这件事令他永远不可忘怀,他该将发生在他身上所有的事件连成一线,然后才得以安稳入睡。
可是那些片段总要迷惑他,不仅是他,甚至迷惑了所有牵扯到的人。
他同他们是一样的,他这样感觉到,甚至又感到自己是特别的,他是那种毫无差别中特殊的人,在他所听到、看到这一切之后,他所感知的亦是同样的无所适从。
这说明他在整个事件中只是一个小角色。
这个角色在陈述中异常的强烈,甚至即使靠得主角那样近,却总没有任何事发生在他身上。
这种紧迫感促使他逃脱,深恶痛绝,他宁愿永远诅咒这种感觉也不愿只是站在角落里看着那一切。
仿佛又是一贯的开始,一贯的往复,跟他亲身经历了似的,她的母亲限制住了所有的出口,把他关在一个没有光的囚房里。
但事实与之又绝不雷同。
那些往事丝毫不留余地的将他推向自我的毁灭,虽然主角同样是一个人,事情同样是一件事,但总令他失望、绝望、甚至令他想要不顾一切的去制止。
令他不可忘怀的是,这仿佛已很陈旧的故事早已迈进了遗忘的边缘,却又奇迹般活过来了似的。无法更早一步,更早一步,或者又变改了,不后悔了;而他依旧脆弱,忍耐的灵魂没有更多解释,另外,所有的故事都该有个结局,这个结局,他永远也猜不到。
因为事实上,它已发生了。
从一开始发生,它就是不可安排的。
他的母亲,她给他讲这些故事。
那时,她的笑容依旧慈祥。
那时,她已步履蹒跚。
她对他说,她快要不行了,过不了多久就会死掉。
她又说,有些故事总要讲给你听,若是不讲,带进了坟墓里去也心有不甘。
于是,她开始慢慢对他讲,她要他听,要他在她的膝前坐下。
听她讲。
很投入的讲。
最后,她终于讲完了,她对着他满含深意的笑,她说,最怕讲在半路就死掉了,现在她不怕了。
她又说,这些往事,若是能够一丝不漏的回忆几年那该有多好。
()免费电子书下载
他看着他的母亲。
她似乎并不善于表达感情,她面容的苍老如同语言的苍老,她的面容不足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真实。
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故事他仍旧耐心的听完了——任何事情,只要涉及他自己,他总是抱有极大的耐心。
他说这真长,这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而他母亲闭上眼睛,养神去了。
年老了,怕死得很。她说,但同时又是随意一说似的,那令她渴望已久,令她惧怕的死总是离她很近。
可是如今生和死对她都不再奏效了,这两种心境在她心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虽然两者同时迫使着她思考,却不再有什么意义了。
而她似乎已习惯这种状态,习惯已久了。
在知道这些往事之前,他不知那是他的母亲。
他的姐姐更不会知道。
他从未与她提起过。
他的姐姐从未来过这里,也不知道这里。
此后她曾找过他,两人互以为不过是旧情人,彼此却仍不能释怀,然后她对他说不爱他了,他无言以对,就看她匆匆离开了。
他从头至尾都是一个倾听者。
不论是谁都可以把故事讲给他听。
只有他。
因为他是这样认真的倾听,从不感到厌倦,这真适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