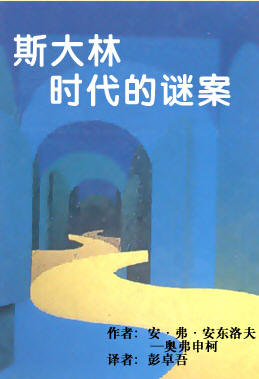斯大林肃反秘史-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欣慈魏尾乱伞淮耸钡哪箍疲涤兴饺似档南怨笠丫簧倭恕S捎诔晒Φ靥隽丝死锬妨止橇钊酥舷⒌幕肪常械胶苄腋#月潮ㄐЧ业娜惹椋度肓搜啊!�
的确,对斯大林来说,允许自己的妻子与普通公民来往,这是一个大错误。在这以前,她都是通过报纸和党代会上的正式发言去了解政府的政策。而在那些报纸和发言中,无论什么事,都被解释成是党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无比关心。当然,她也知道,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人民应该做出某种牺牲和放弃很多自身利益,但她还是相信那些有关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正逐年提高的政府公告。
可进了学院之后,她不得不做出这一切都是谎言的结论。这使她大吃一惊,因为她了解到工人和职员的妻子及子女被剥夺了获得食物购买证的权利,也就是说,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食品。她还了解到,无数苏联姑娘——打字员、办事员和其他小职员,为了免于饿死和接济丧失劳动力的双亲,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一些被动员去进行集体化的大学生们对阿利卢耶娃讲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实:成批的枪杀、驱逐农民,乌克兰的严重饥荒,成千上万个沦为孤儿的儿童流浪全国以乞讨为生。她以为斯大林不了解国内情况的全部真相,就将学院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丈夫和叶努启则。斯大林却尽量回避这些话题,并斥责妻子“在收集托洛茨基分子的谣言”。
有两个从乌克兰返回的大学生告诉她,在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已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他们亲自参加过一次逮捕行动,从被捕的两兄弟家中,搜出了几块准备拿去出售的人肉。阿利卢耶娃又怕又惊,回去就将此事转告了斯大林和他的卫队长保克尔。
斯大林决定结束自己家中发生的这种敌对情绪,在极其粗野凶狠地骂过妻子之后,他宣布不再让她返校。他命令保克尔查出那两名大学生,并加以逮捕。这项任务并不困难:保克尔派去保护阿利卢耶娃的密探,本身就有义务监视学院里与她来往和交谈过的人。通过此事,斯大林还做出了总的“组织结论”: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各大专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进行残酷的清洗,特别要注意那些被动员去参加过进行集体化的大学生。
阿利卢耶娃几乎有两个月没能回自己的学院。后来多亏了她的“保护天使”叶努启则的干预,她才获准读完那一学年。
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去三个月后,有一次,保克尔访客。席间,人们谈到了逝者。有人惋惜她的早逝,说她从不利用自己的显赫地位,始终是一位谦和、温柔的妇女。
“温柔?”保克尔尖酸刻薄地反问道,“可见,您并不了解她。她非常暴躁。我真想让您见识见识,有一次,她突然发作,冲着他的脸大骂:你是个虐待狂,你就是这种人!你虐待自己的儿子,折磨自己的妻子你还迫害全体人民!”
阿利卢耶娃同斯大林发生这样的吵架,我还听说过一次。那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夫妻俩准备去高加索度假的前一天晚上,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发了脾气,跟往常一样,用污言秽语把妻子大骂了一顿。第二天一早,阿利卢耶娃就忙碌着为出发做准备。斯大林出来后,他们就一起用餐。餐后,警卫员把斯大林的小皮箱和皮包放到车上。其它物品事先已经直接送到了斯大林的专车上。阿利卢耶娃拿起帽盒,吩咐警卫员放进她装东西的皮箱里。斯大林这时却突然宣布:“你别去了,就留在这儿!”
斯大林钻进汽车,坐在保克尔身边,走了。惊惶失措的阿利卢耶娃却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她的帽盒。
很明显,她没有任何摆脱这位独裁者兼丈夫的可能。整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能保护她的法律。对于她来说这不是夫妻生活,而是囚笼,要想解脱只有寻死一途。
阿利卢耶娃的遗体没有火化,她被埋在公墓里了。这一情形也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惊奇,因为在莫斯科已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党员死后都应该火化。如果死者是位重要官员,就把他的骨灰盒砌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宫墙里。级别较低的官员的骨灰,则长眠在殡仪馆的墙壁里。阿利卢耶娃作为伟大领袖的妻子,当然应该是在克里姆林宫宫墙里得到一处壁龛。
然而,斯大林却反对火葬。他命令亚果达操办隆重的出殡仪式,将死者安葬在古时特权享有者的新处女修道院的墓地里。那是古代皇族的陵园,安葬过彼得大帝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姊姊索菲亚,以及很多俄罗斯贵旅的代表人物。
斯大林要求跟随出殡灵车走完从红场到修道院的全程,也就显说,要走近七公里。这使亚果达大吃一惊,暗自惴惴不安。二十多年来一直负责“主人”人身安全的亚果达知道,“主人”历来都极力避免冒风险。虽然周围卫队如林,但为了自身安全得到更可靠的保障.斯大林总是要想出一些新措施,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在大权独揽之后,他就一次也不曾冒过在莫斯科街上走一走的风险。当他打算去参观某座新建成的工厂时,他就会下命令让工人们放假,并在整个厂区布上军队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亚果达还知道,即使在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从自己的住宅走到办公室的途中,如果意外地遇上个克里姆林宫的职员,保克尔就必然会遭到一顿臭骂,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而且经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反复审查和甄别。所以,一听斯大林说要随同灵车在莫斯科街头徒步而行,亚果达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关阿利卢耶娃将埋葬在新处女公墓的新闻,直到出殡前一天才公布。莫斯科市中区的很多街道都很狭窄,弯曲,而且谁都知道,送殡队伍行进缓慢。如果有刺客从窗口认出斯大林,并从高处扔下炸弹,或用手枪甚至步枪向他射击,那可怎么办?葬礼的准备工作,亚果达在一天中要向斯大林呈很好几次,他每次都试图劝斯大林不要冒险,想说服他在最后一刻直接坐车去公墓。却都未能奏效。斯大林可能是决心向人民表示一下他对妻子的爱,并以此粉碎那些对他不利的传闻。但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不管怎么说,是他造成了自己孩子的母亲的死亡。
亚果达和保克尔不得不动员起莫斯科的全部民警,并把成千契卡人员从别的城市紧急召到莫斯科。送殡行列要经过的每幢楼房都派去了城防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将住户全都赶到不临街的房间里,并禁止他们从那里出来。临街的每扇窗口旁,每座阳台上,都站立着哨兵。街道两侧布满了由民警、契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士兵、动员来的共产党员组成的“老百姓”。整个行进路线的街道两侧,从清晨就禁止通行,清除了行人。
终于,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三时,送殡队伍在骑警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部队的护送下,从红场出发了。斯大林确实跟在灵车后面,由其他的“领袖们”和他们的夫人簇拥着。看来,为了斯大林免遭任何暗算,确实采取了一切可能采用的措施。然而,他的勇气并没保持多久。十多分钟后,刚走到途中要经过的第一个广场时,他同保克尔两人就离开行列,钻进了等候他的汽车。于是,一支车队簇拥着斯大林的汽车,飞快地绕道驰向新处女修道院。斯大林在那里等来了出殡的队伍。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当阿和卢耶娃嫁给斯大林时,她弟弟巴维尔·阿利卢耶夫也一块住进了斯大林的公寓。婚后头几年,斯大林十分宠爱娇妻,对她兄弟也象对家里人一样。在斯大林家中,巴维尔认识了很多布尔什维克,当时他们都还不怎么显赫,但后来都担任了国家要职。克利姆·伏罗希洛夫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成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待巴维尔很不错,经常带着他去参观部队演习和空降兵检阅。显然,他希望激起巴维尔对军人职业的兴趣,但巴维尔却更愿意从事某种安静点儿的工作,想当一名工程师。
我第一次遇见巴维尔·阿利卢耶夫,是一九二九年初,在柏林。当时,伏罗希罗洛夫让他参加了苏联商业代表团,来柏林检查苏联国防部向德国订购的空军装备的质量。巴维尔·阿利卢耶夫当时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他妻子在外贸部门工作,是位东正教神父的女儿。阿利卢耶夫则是个工程师,并是基层党组织的一名普通党员。在苏联驻柏林的庞大的使团中,除了个别领导,谁也不知道阿利卢耶夫是斯大林的亲戚。
作为国家检查机关的工作人员,我的任务是监视商业部门的一切进出口业务,包括在德国的秘密军事定货。因此,巴维尔·阿利卢耶夫在工作上属于我管,我和他一起共事了近两年时间。
我记得,当他第一次走进我办公室时,他和他姐姐在相貌上的酷似使我感到无比惊讶——也有一张线条匀称的脸,一双东方人的,郁郁寡欢的眼睛。当时我就确信,他的性格与他姐姐一定十分相似——正派、真诚和极其谦虚。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他还有一个为其他苏联官员所少有的优点:如果对手赤手空拳,他就决不会使用武器。作为斯大林的内弟和伏罗希洛夫的朋友,他无疑是个很有影响的人。但是,如果代表团里那些不知他底细的职员出于往上爬的动机或者纯粹出于品质不好而诽谤他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向他们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我记得,阿利卢耶夫手下有位工程师,参加审查和接收德国厂家制造的飞机发动机。有一次,他向代表团领导打了份小报告,说阿利卢耶夫与几位德国工程师的交往令人生疑,还说他屈服于德国工程师的影响,在检查运回苏联的飞机发动机时,马虎潦草,不认真负责。告密者认为有必要加上一条:阿利卢耶夫还看过白俄侨民办的报纸。
商业代表团领导把小报告交给了阿利卢耶夫,同时表示要把造谣中伤者送回莫斯科,开除出党,并从外贸部门除名。阿利卢耶夫却请求别这样做。他说,那个人对发动机很内行,工作也非常认真。除此以外,阿利卢耶夫还答应要同那人单独谈谈,劝他今后不要再诬陷他人。由此可见,阿利卢耶夫是位品德十分高尚,不愿向弱者报复的人。
在两年的共事中,我们谈过很多事情,唯独对斯大林谈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对斯大林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已足以使我打心眼里厌恶这个人了。再说,关于他,巴维尔又能说出些什么新情况呢?他有次对我说,斯大林喝醉了酒以后,往往会高唱宗教赞美歌。另外有一次,我从巴维尔那里听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索奇的别墅,斯大林扭曲着愤怒的面孔走出餐厅,把餐刀往地板上一扔,高声叫喊道:“即使在监狱里,给我的刀也要锋利得多!”
一九三一年,我被调回莫斯科工作,与阿利卢耶夫分了手。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没再见过面:有时,我在莫斯科,他在国外;有时则相反。
一九三六年,他被任命为装甲兵部队政治部主任,顶头上司是伏罗希洛夫、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读者已经知道,就在第二年,斯大林控告图恰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犯有叛国罪和密谋颠覆政府罪,并把他们枪毙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底,我在西班牙收到阿利卢耶夫的一封热情的来信。他祝贺我荣获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但信尾有几句附言,内容非常奇怪。巴维尔写道,他愿意再次和我一块工作,还表示,如果我能主动地请求莫斯科,委派他来西班牙,他将随时准备动身。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要我来提出这个申请,要知道,要办成此事,巴维尔只需把自己这一愿望告诉伏罗希洛夫就足够了。经过反复推敲,我认定阿利卢耶夫写这一附言完全是出于礼貌,他提出希望重新和我共事,是想从此再次表达他对我的好感和友情。
这一年的秋天,我出差去巴黎。我决定去看看那里的一个国际展览会,包括里面的苏联陈列室。在陈列室里,忽然有人从后面抱住了我的肩头。我转身一看,是巴维尔·阿利卢耶夫,他正向着我笑呢。
“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惊喜地问。当然,我说的“这里”不是指展览会,而是泛指巴黎。
“他们派我来展览会工作。”巴维尔搬着嘴冷笑着回答,并说了自己在苏联陈列室里担任的无足轻重的职务。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