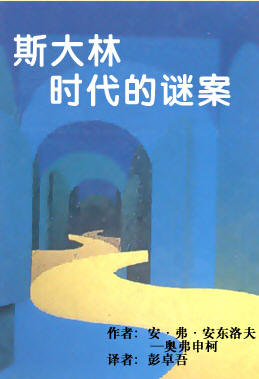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关要求他在什么供诉上面签字,他就在什么上面签字,甚至还帮助侦讯人员修改自己的假供诉。
赖因霍尔德与奥利别尔格相反,根本不过问自己可能被判处什么刑。他把一切都寄托在斯大林和叶若夫的人品和良心之上。下面我们就将看到,赖因霍尔德为内务部准备虚构的审判提供了多么大的帮助。在法庭上,他不仅是内务部时主要武器,而且还是检察长维年斯基的得力助手。在被利用的人当中,赖因霍尔德发挥的作用之大,是奥利别尔格远远不能相比的。作为一个外国人并常住在国外,奥利别尔格不可能成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老一代党的领袖们的“敌对活动”的直接见证人。相反,赖因霍尔德身为苏联政府高级干部,却完全有可能参与同原反对派领袖的秘密会谈。
赖因霍尔德甚至在这样一份认罪书上签了字。作为托一季组织的成员,他曾准备杀害斯大林,并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巴卡耶夫的亲自领导下,“创造性”地展开了犯罪活动。除此之外,赖因霍尔德达作证说,杀害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手策划的。恐怖活动不仅针对斯大林,而且还将危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领袖人物。
他这个“证人”的作用之大,竟使审判闹剧的组织者们决定突破先前的设想。让他的口供不仅仅局限于陷害加米涅夫和季偌维也夫。现在,有他签字的供拆几乎涉及到所有的老党员,这些人往后统统将被送上法庭。按叶若夫的要求,他还在供诉中污蔑了原苏联政府首脑李可夫,原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托姆斯基,并对伊万·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帕尔·瓦加尼扬进行了诽谤。
赖因霍尔德与侦讯工作领导人的合作走得太远了,竟使他们一时忘记了他也是一个被告。使此,在赖因霍尔德时“证言”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这些供诉听上去似乎不是出自于一个不久前还蓄意杀害斯大林的死不悔改的恐怖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一个义愤填膺的公诉人之口。他无比愤慨地将他参与过的所谓阴谋组织说成是“不择手段破坏国家强盛的反革命集团和由杀人犯组成的匪帮”。
赖因霍尔德的供诉经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隆诺夫以及阿格拉诺夫的仔细审查后,由亚果达转给了斯大林。第二天,斯大林批准了这些材料。并在上面做了一处使内务部领导人极度惶恐的修改:赖因霍尔德在供诉中说,季诺维也夫坚决主张杀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塞洛夫.可是,斯大林亲笔将莫洛托夫的名字划掉了。
亚果达不敢多问,只得吩咐侦讯小组负责人在提取被告有关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供对,别再提到莫洛托夫的名字。显而易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间出现了裂痕,因此,莫洛托夫随时都可能从国内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就象斯大林以前的宠臣,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席司尔佐夫的下场一样。内务部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斯大林任何事情都做得出来。今天,他从阴谋分子所要杀害的牺牲者名单中把莫洛托夫一笔划掉,那么明天,就会将他列入这个阴谋参与者的名单里,说他蓄意杀害“领袖”。
鉴于这一插曲有助于说明莫斯科审判,是斯大林的整个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专门加以揭露。
斯大林还对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作了另外一些修正。有的修正还象样,但更多的改动却显得不论不类,内务部领导们在反复诵读时,往往忍不住要露出嘲讽的冷笑,要不然就低声嘻笑一番。比如,赖因霍尔德在供诉中交代说,季诺维也夫坚决主张杀掉斯大林和基洛夫,而斯大林在读过这一段之后,又附了一笔:“季诺维也夫声称,光砍掉大橡树还不够。周围长出的小橡树,也必须连根拔掉”。
后来,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在法庭上把这一比喻有声有色地重复了两遍,讨得了斯大林的欢心。
在另一段供诉中。赖因霍尔德污蔑加米涅夫曾极力论证采用恐怖手段的必要性。斯大林在此又加了一句仿佛是加米涅夫本人说的话。“斯大林的统治,象花岗石一样坚硬,所以盼望这块花岗石会自行破碎的想法,是愚蠢透顶的。换言之,就是必须去砸碎它。”
审判组织者手中还有另一件武器,那就是里哈德·皮克尔。他不是老党员,侦讯小组之所以需要这个人,仅仅因为他担任过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主任。叶若夫和亚果达认为,这一情况必然会使皮克尔诬陷季诺维也夫的供诉具有说服力。
我十分了解皮克尔。他心地善良、待人和气,生来多愁善感,年轻时还写过一些抒情诗,后来改写散文,是苏联作协的成员之一。
皮克尔曾积极参加过国内战争,是第十六军政治处主任。他与赖因霍尔德一样,也加入过反对派。但时间不长,与反对派决裂之后,他就再也没得到重用。被捕前,是莫斯科室内剧团的经理兼党委书记。皮克尔爱好戏剧,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他远离政治活动,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搞文艺创作。同时还搞一些有剧团青年女演员参加的风流事。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扑克迷,而且主要是与内务部的一些重要干部玩牌。这个圈子里的人都很喜欢他。把他称为牌场高手和“好交际的小伙子”。而且,他还受到这些人的妻子的热心关照。
星期日,皮克尔常常在这些身居要职的契卡工作人员的郊外别墅里厮混,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的专用汽车和其他生活福利。一九三一年的整个夏天,他都是在莫斯科州内务分局局长那幢邻近斯大林府邸的别墅里度过的。由于内务部这些朋友的关照,他曾两次到国外作愉快的旅行。一次到欧洲,一次去南美。
皮克尔的朋友们得知叶若夫和亚果这决定要把他作为被告送上审判台时,都为他感到由衷的难过。他们极力为他求情。但毫无作用。不过,当亚果达告诉他们,皮克尔不会去集中营服刑之后。他们也就对必须逮捕他的决定听之任之了。亚果达也没说空话,皮克尔后来被送到内务部管辖的一个大建筑工地去当了个施工主任。
皮克尔因突然被捕而吓得丧魂落魄。不过,他尽管生来脆弱,但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抗拒侦讯员的逼供。亚果达决定求助自己手下那些与皮克尔有交往的部下。这些人都是内务部各处的处长,如盖伊,沙宁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于是,从那以后, 审讯在皮克尔看来意象是过家庭生活一样, 再也没有人凶神恶煞地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参加反对派有多长时间?”再也没人要他坐在内务部人员的面前, 称后者为什么“侦查员公民” 。他完全可以随随便便地叫他们的小名:“马克”、“舒拉”、“约希亚”。如果再往桌子上放一副扑克,那一切看起来就跟他没被捕以前一个样,可以病痛快快地玩玩牌。然而。此时坐在“马克”、“舒拉”、和“约希亚”对面的皮克尔,毕竟是犯人。他们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他们无法救他出狱,因为这是“上面的要求”,但如果他愿意帮助内务部,以自己的供述来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就敢为他担保:无论祛庭判他什么刑,他们都不会让他去集中营,而保他“监外”服刑,到伏尔加河边一个大工地去当主任。
皮克尔屈服了。他只请求让他见见亚果达,以证实这一切许诺。亚果达同意与皮克尔谈话,并十分慷慨地保证一切许诺都将兑现。这以后,皮克尔被转送到米隆诺夫手下,后者为他拟了一篇供诉,并要他签字。在米隆诺夫的办公室里,皮克尔同以前的老朋友赖因霍尔德见了面,后者也属米隆诺夫差谴。就这样,皮克尔接受了在未来的审判闹剧中担任一定角色的任务。
在米隆诺夫为他准备的供诉中,皮克尔承认在季诺维也夫的一再坚持下。他和巴卡耶夫、赖因霍尔德一块进行了刺杀斯大林的准备。他还为赖因霍尔值的一项供词作证,说原托派分子德雷采尔企图策划对优罗希洛夫的暗杀。但皮克尔供诉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季诺维也夫的。
皮克尔踢赖因霍尔德不一样。赖因霍尔德是时刻准备在一切要他签字的供诉上签字,并相信这是在完成党的任务。皮克尔则相反,他基本上拒绝做假口供去加害其他被告。指控季诺维也夫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亚果达的许诺的交换条件。也曾有人要他作证诬陷其他被告,但皮克尔为自己订了一条规矩。如果被捕者已经“坦白”,或者已经被其他被告诬陷,他皮克尔才同意证实这些供述。同时,他坚决拒绝诬陷那些连内务部都还没掌握其黑材料的人。赖因霍尔德是以其特有的干劲,全力以赴地帮助侦讯人员,皮克尔则相反,表现得消极、冷漠。他逐渐失去了好交际的天性,变得十分孤僻,意志消沉到了极点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皮克尔被指定扮演直接诽谤季诺维也夫的角色,因此,侦讯领导人开始为他的心理状况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他会失去理智。所以亚果达命令皮克尔的那些老朋友常去狱中看望他。向他表示关心和同情。皮克尔被转到一间较舒适的囚室。沙宁、加伊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常常去看望他。他们总还要随身带上一副扑克,一些火腿面包和饮料,在他那里一直坐到深夜才散。他们的探望使皮克尔的情绪稳定了一些。他又开始提起精神,象以往那样说说俏皮话有时甚至忘了自己身在狱中,但有时又突然清醒过来,十分严肃地嚷道:“哎,伙计们,真可怕呀,看你们把我扯进了一个多么肮脏的勾当里。等着瞧吧,今后你们再也不会和我这个高明的牌友相会了!”
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伊萨克·赖因霍尔德和里哈德·皮克尔的供诉,为内务部领导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帕尔一瓦加尼扬和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起诉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为开庭审判打下了基础。现在,审判组织者所面临的工作,是利用这些假供诉来讹诈原反对派的首领,从他们口中掏出有关参加过反政府阴谋的“认罪书”。
其实,仅有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证词还是远远不够充分的。为了达到既除掉反对派须袖,又镇压反对派一般成员的目的,斯大林要求在审判大厅内让人民看到,反对派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州、市几乎都有反对派的恐怖小组在活动。
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反对派成员从远处的监狱和集中营被押到莫斯科。按照斯大林的意图、这些人应被指控为恐怖小组的成员,内务部侦讯人员应该先从这个“宝库”中挑选一些人,对他们进行“加工”,让他们在审判闹剧中扮演普通角色。
但是,如果说内务部头头们比较轻松地获得了象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这类人的“坦白”的话,那么,在中间环节同时开始行动的侦讯人员却是费尽心机也没取得应有的成果。与他们打交道的犯人。坚决否认参加这恐怖活动。而且,大部分人都有不在现场的铁证——他们多年来一直被关在监狱里、集中营里和偏远地区的流放地。莫尔恰诺夫经常催促侦讯人员,而后者的自尊心也因不能获得上司所需要的结果而受到伤害,同时,他们的精力也几乎消耗殆尽。最后,他们意识到再这样搞下去已没希望,便在莫尔恰诺夫主持的一次例行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缺乏强有力的手段使“被告屈服”,从其口中挤出供诉。亚果达那条禁止使用威胁和许诺的密令,实际上解除了他们与受审人作斗争的武器。
莫尔恰诺夫故作惊讶,他不相信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有多年“机关”工作实践的契卡,竟会如此死板地理解人民委员的命令!他说:
“契卡人员不但应该是优秀的侦讯员、而且还应该成为内行的政治家。”接着,他又弦外有音地补充道:“应该善于判别什么与他有关,什么与他无关,什么是他必须的,什么出于最上层人物的理想而一时不能执行的。”
“可究竟该如何判别呢?”一个侦讯员问道。“命令是人民委员亲笔签发的,而且是专门发给我们的!”
“您马上就会明白该怎么判别!”莫尔恰诺夫打断了他的话。“我以人民委员的名义正式命令您:去找您的受审人,把他们好好收拾一顿!把他们踢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直到他们坦白交待为止!”
到会者都知道这一无耻之言是出自谁的口。早在一九三一年。原内务部经济局局长普罗科菲耶夫向斯大林汇报有关被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