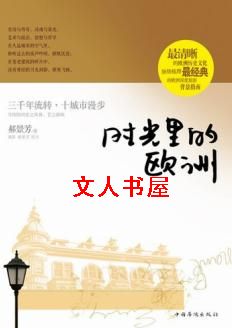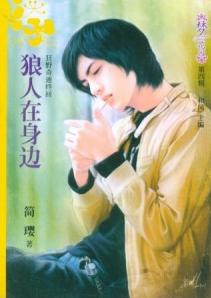����ŷ��-��2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г��������ˡ�������æ�ſ���ߣ���æ�ſ��·�����������ү��������
�����ס�
����������ͬ־���������Ǯ���������������
�����������ƺ�˭ѽ��˭��ͬ־ѽ����һ���ź����������������Ƶ��ʡ�
������������㣬����Ϊ�����Ϻ������͵��ϱ��۸���
�����������Ǹ���ô�ƺ��أ�������ϸ��ϸ���ء�
����������ѧ��������������˵����ѧ�����ٿ��ڣ���
���������ҷſ����ӵ��֣��ߵ�������ǰ��˵��
�����������������ھ����ң�����ô�ƺ�������
�������������е���Ծ�����ǿ��˵��
����������ѧ����������
���������������ھ���ѧϰ������˵�����ҹ�ִ��վ�š�
���������Ա��Ѿ�Χ��һȦ���ˣ��ſ����ֵ���ϲ��
�������������ƺ���֪��˵ʲô�ã����Σ��۾�ע�ӱ�ĵط���˵��
���������������������ҽ��㡣��
���������Աߵ��˳ԳԵ�Ц�������ҡ�
������������������������ƽ�ӣ�һ����һ���ֵ�˵�����㣬�������ʸ�
��������ǣ�غ��ӵ��֣�������ǰ�ߣ����룬�ֻ�ͷ������˵��
���������������ӶԴ�����ˣ����涪�����˵�������
��������Ȼ������һ���������糿�����˸߲��ҵض���˵��
��������������ȥ�г��𣿡�
����������һ���û������
�����������ף�����ȥ����
����������������ʲô����ԥ�˰��Σ�����ü˵��
�����������Һ���ȥ�����ǣ��������Ͱ͵أ���������ɲ����Դ�Ӧ�Ҳ����ܣ���
�����������ܣ��Ҿ�㵵ؿ�������û�뵽��������ó������̵�������СС���ˡ�
�����������������������������������ӣ�������ֻ���ڲ���ƽ��ʱ��ų��ܡ���
������������ɲ����Դ�Ӧ�ң�����������ί����˵��������ƽҲ�����ܣ���
������������������������
������������С�㽫Կ�ײ��������ݾͻε��ε�����������¥��
�����������á��鷳��������¥��лл���ټ���
��������һ�������Ͻ���Ԣ���ٳ�������ɵ�ˡ��ⲻ���Զ����ݣ��ҵð�ť��¥��ֵ��
С��ô���С�������������Կ�ף��������ݣ����������ң�����ȥ��
�����������á��Բ�����Ҫ�鷳�����ǵģ���ȥ�����¡����ǣ��Ҳ��DZ����ˡ�лл��
���������ټ���
�����������������������£�һ��������ܲ����ˡ����Ǹ����Ắ�������ˡ�������
���罻�������Ҳ��һ�ֱ��£��Ͷ�����˵�Į�������˵����ʱ����Dz�˵
�����ҿ������ܣ���Ȼ���ϰ��Ҫ����̸̸����������è��������dzЦ�������Ҳ�
��ô�ں����ϰ�ߡ�
���������������Ǹ���ò���ˣ���������С���ܾ��ø���Ŀ���ӣ�����ͷ������л����
��֮���ҷ���ֻҪ�е��ݾ͵��е���С���ʱ���Ҽ�ֱ֧�Ų�ס�ˡ����У�
�ҵ���ò����һ�������ģ��������������������Ҫ�Ŷ���Ҫ�ܵ���в��
���������鷳����лл���ԣ������ˡ����ã������ܺá���¥���ԣ�лл������������
����
���������Բ�����Ҫ�鷳��������̫���ˣ����ȥ��лл���������ˡ����һ�����
�С�лл�ˡ��ټ���������������
���������ҿ�ʼ�е�����š������Ǹ��ڵ������һ�ѵ��ӣ�����Ƕ�ڱ��ϵ�һ����ť��
�Ե��ӺͰ�ť�ҿ��������ã����ӺͰ�ť����Ҳ����Ҫ��������ˣ������
�ϵ�Ϊ��������֮�͵��ˣ������������۾������ң�ʹ�Ҳ��ϵ�������һ�����ò
���������ƽ���ǣ����䲻�ǵ��Ӱ�ť��ȴ�͵��Ӱ�ťһ������ԶǶ�ڵ����
ֻҪ���õ��ݣ������������������ȡ��������ò������ʹ�������������֮
�䡣
���������ҿ�ʼ�ý�����¥�ݡ���������ȥ���������������Ѻ�������ò�����Ľ�
����͡�
������������֮���Ҳź�Ȼ�����������Ǽ������еĵ����ﶼ�и�����С�㣬����Ӻ�
��ťһ����װ�ڵ�������������۾�������������������ȥ����������ȥ����
����������
���������Ҽ�ֱ��ʧɫ��
����������̤�������խ�ĵ��ݡ���С�㡱�Ǹ�ͷ���ԲԵ��ϸ��ˡ�
�����������鷳������¥��������Ǭ��������
������������¥��ͣ���������ޱ���ء�
�����������ǡ������ҳ�����һ�£�������1989��������ж����ѵ����ϣ������˼���
ô�죿��
����������������·���������ݡ�С�㡱��̫�ͷ�����Ȼ�����ҵ������е��Ī�����
������������������������������������������������������������������������������������������������
���������ص��⽻��Ԣ������С�����ڴ��ſںͱ�¥��С�����졣������һ��������
����������һ��ͷ�ᣬʱ��ʱ�����Ÿո�ϴ������ʪ��ͷ����ϥ���ܰ���һ�ݶ���
�˵ġ���������������������̨���ϣ���������ҹĻ��£����գ�������������
�εεĴ���С�¡�
�������������ˮ��ͦ���ģ���̤�����š�
�����������á��鷳����
����������û��������˵�����Ű�ɣ������ǵĻ���һ���Ҳ�����ҵij��ִ�ϡ�����
�������˵���Ƶ�ͬʱ������������ƽ��Ų����ͷ�������Ҳ���Ÿ������ݡ�����
֪��С����������˭����
����������¥��лл�㡣
�����������һ���Ϊ������˹���ԭ��ѽ����û��ɣ��˼һذĴ�����ȥ�ˡ�
�����������������塢ͷ�ᡢ�������������������ĸ�һ������Ʈ�¡�
�����������ŵ��ݽ�����£���ţ���ͻȻ���������ǵ�����Ҳ��ǵ��ӺͰ�ť����
������Ƕ�ڵ������ʱ��ʱ��ĵƣ����Ƕ����dz��������õġ������ҵ����ˡ�
�������DzŻ����ȥ��
������������һ������
����������¥��
����������������������������������������������������������������������
���������Ӷ���һ�������������Ƿ�ŭ��������
�������������ϵ�С̯�ԣ��������̿��������ʹ��ȫ�������س��żܣ����Ӵ��˶��ˣ�
���ǵ��Ϻ졣����֮�仹վ�Ÿ��߰�����С�����������Ź�Ҫ��δ�ȵĿ��֣���
�����ӵ����Ż𱬵Ĵ��ˡ�
�����������˵�����Խ��Խ�������������������������Ů�ˡ���һ���������ϵ�С��
���ޣ�һ��������ֵĺ��ӵ��衪�����ƵIJ�������ų�������������ˣ�ֻ��
�ĸ���ͬʱ���ź������£�˭Ҳ������˭�ġ�
����������С��ͻȻ����ȥ�����İ��ʱ�������ֵ��˶�����һ����С���ڻ���������
�ָ߾ٰ�ʣ���������Ҫ�������ļ�ʽ��
��������û�а�ʵ����˳ԳԵ�˵����������ģ�������ġ�������˵���ˣ�һ��һ��
�ˣ��۾����Ű�ʣ�С��һ��һ���ƽ����ڹ��ڻ�������������ѽ����ʱ�����ѷ�
Ȼ��������£�û�ҵ�������ת�����ܣ�С�����Ű���������˾�Χ������̯��
��ôһ��һ������Ȧ������Ȧ����ߣ�����Ů���Ѿ����������˴����������
���ģ�������ģ���
�������������ֵ����ƺ��õ�һ������ľ�ϲ��û�뵽��С��˵�ɾ��ģ����ǵ�����
���ſ���ҹ�ֲ�ӰƬ�����Ǻ������ǻ�ϲ�ı��顣
����������Ц�ˡ�
�������������İְ�һ�Ե��ң����˼Ҵ�ܣ�����ú�Ц�������߿��ˡ�
��������һֱ�����������ֵİ����ɿ����֣�˵�������裬����Ц�������ְ�ȥ�ˡ�
������������������ҵ�Ц��������ô֪����������һĻ����Ϸ�罫�Һ�����������
���ص���ʮ��ǰ��̨�壬��һ��Ʈ�����ε��������ص����Ҽ���������ͯ�ꡣ
����������֪���ж�����û������ͷ�Ĵ���ˡ���ŷ�����ꣿû�����������İ��ꣿ
û������̨�壿
���������еģ�������ʮ��������һ��Ǹ����ű��������������СŮ����ʱ��ͷ
��ܺ������о������һ���֣�����ʱ��ʱ�������С����һ��������������飬
�����dz���ײ������������顣�������������Ľ��ϣ�ͻȻ���ú�ͷ�����ܲ�����
�Ż���ȹ���Ų�����Ů����������˵��
����������ǰ��ǰ�����˴�ܡ�
�������������������������˼������ʣ������ֱߵĻ��һ��նѼͷ�ĵ���һ
֧�������������ӡ�һ����ϴ�IJˡ����Ų������ظ���ǰȥ��
��������ǰ���������ʵʵΧ��һ���ˣ�С��ֻ�ܴ����ȵļ�϶���ȥ����ܵ������ˣ�
�٣��ǺڱǺ�һ������ʶ���ˣ�Ť��һ�ţ��������Ӱ������ȭ�����磬ֻ����ץ
��ͷ����ҧ��ƨ���ֲ���س�����ȥ�����Ǻڱǵı���������Ѫ��
��������Ȼ�����˺������������ˣ���
�������������ÿ�һ��·�������ҡ��ڵ��߽�������ܵ���Ҳ��һ������
��������������ȥ��������Ĺ��û�뵽ȴ������һ����ܡ���С��������ʱ�����֮
���Լ������Ǹ����ű����������������СŮ�������ڴ��˵��ȼ䣬����ؿ�����
��ô�����Լ�����С����̲�ס��Ц����һ����Ȼ���ľ�ϲ��Ҳ��һ��Ī������
����꣬��������ȥ��������ߵ��龳��
������������֮���ڳ��������ֿ������������������һ�ţ��Ҿ�Ц�������ˡ�
����������һ���¼����Σ�����ס������̨����˵��������ࡣǰ�����ҿ��������˴�
�����↑ʼ��һֱ����ȥ�����ͷ��Ѫ����
��������������˵������ʮ�����̨��Ҳ�������ġ������ֱ�������������۾�������
�ػص���
����������̨���˲Ų���������̨���˸���½�˸�����ȫ��һ�����е��������������ԡ�����
���������������浹���ҳ���һ��������Ϊ������������ʮ�꣬��̫��ʶ��ȥ��̨�壬
����������Ⱥ֮�����б����ϵIJ�ͬ����������90�����̨�壬����ŷ����һ����
���Ѽ�����ܵĽ־������ǣ��⾿������Ⱥ�Ը�IJ�ͬ������һ����ᷢչ�Ľ�
���⣿
������������ѧ����������������������һ���������й��Ļ��ñ�һ�������䣻����
�˴���������Ҫ�Ķ��������������̨���ˡ����������ˡ��¼���������Ҫ��
���������ڵ�����ʷ�����IJ�ͬ�����൱��һ�������Ǿ����ó���Ӧ������Ĺ���
��һ����������ɻ�����һ����
��������90����ı������������Ǹ��������������ϵ���ͽ����̨������̨��Ĺ���
�������൱��IJ�����ֲ����ɲ�ͬ�����ʺ��ԡ��ҶԱ�������ʶ��Ϊ��dz��
���ǣ���dz�и�dz���ŵ㣬��Ϊ���ܸ����еز���һӡ������ո�µ��۹⣬��
�����ظ���һ�����е��Ը�1993��8�µı����������İ����Ա����������̵�
�о����ǣ�����һ��ѹ�ּ���ij��С�
������������������Ҫȥ�˽��γ�������е�����ʲô��ᡢ�Ļ������α�������ֻҪ
�������������������ɫɫ�ij��У�Ȼ�����ͷ����������һԾ�����о�����X
�أ������˵ġ������ġ������ֳ��ġ�������ġ��ġ��ϰ���ļ��䣬��ͻ�о�
���Ƿ����������ѹѹ����ͷ�����ص��ƺ���Ҫ��������ȴ���ϲ����ꡣ����ÿ��
�˶��ڵȴ������صصȴ����ȴ���
�������������˴����һ�ִ�����ȴ��Ѱ�������蹤�ߵĿ��գ�����˵�������ش�
��������ʵ��֪��������ͷû����������Ҫ�Ĺ��ߣ����Դ��ۣ�����ѹ�֣����Խ�
�ǵصȴ���
��������90�����̨�����ԵñȽ����ɣ���Ϊ������������֮��Ĺ�ϵû��ô���š���
��������Ķ�����������ȫ���⣬������������ʱ�����ӻ����������������ʱ
�����������ϼ���Ҳ�ⲻ����������������������Ϲ��ã�����Ҳ������ȥ����Ϊ
�����Լ��Ĺ�����������ijһ���̶ȵ�����Ȩ��������Եû��
�����������˵�����Ⱥ����ԵIJ�ͬ���ҵ����ѻ����ǶԵģ������ұϾ���������ʮ
��ļ��䣬��ʱ�Ĵ�ܽ־�������Ŀ���������֪����̨���˲���һ���������
����ģ��Ӵ�ܵ�����ܣ�̨���������ʮ�ꣻ���������Ϊ���ش�ܣ������ش�
�ܣ���������Ҫ�����������
�������������ﵥ��������ײ����ײ���ˡ��������Dz���Ҫ�����أ�
����������һ����
���������������ֻ�dz�����ӵ�еIJƲ��м�С��һ���֣�Ʃ��˵������֮��������
��������������ԽҰ���г��ȵȣ���ô�����п���ֻ�ǻӻ��֣�����û��ϵ��
��������������������б��գ�Ҳ����˵�������ķ��ö��ɱ��չ�˾��������ô
����Ҳ����ֻ�ǽ���һ�±˴˵ĵ绰���룬�����������ֵ���
���������෴�ģ����ʧȥ�˵��������������Ӷ������ij������������������ѡ�����
�ܲ�����
����������ʮ��ǰ��̨�������˸����Ļ�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