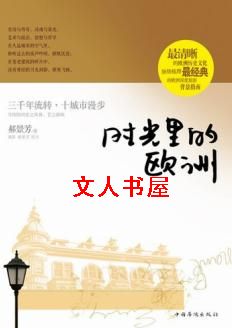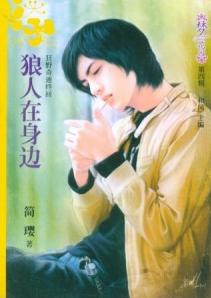人在欧洲-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裁员、遣散、失业
从前,店铺里空空荡荡,买不到东西;现在,店铺里应有尽有,只是买不起。
从前,以为争取到了民主就等于争取到西方的物质享受,现在发觉,自己成为仰赖
救济金的失业游民。
于是,一年半前拥向街头高喊“民主自由”的人,现在又拥向街头,高举的标
帜上写着:
“基民党,你出卖了我们!”
在柏林一个马克斯铜像基座上,有人用喷漆涂着:
“再来一次的话,我们一定会成。”
※ ※ ※ ※ ※
当然,没有几个德东人真愿意再回到独裁的时代去,只是由于原先对统一充满
了感情的激荡,对经济现实又一知半解,满怀幻想;许多人,面对转型期的残酷淘
汰,难免就转为失望而愤恨,
统一一年之后的今天,民族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没有人再去为统一写诗
或流泪了。西佬和东佬都在忙着面对现实;现实,常使两边兄弟怒目相对——东德
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在当了一年国会代表之后,终于又拂袖而去,永久脱离政坛。
西佬觉得“我已经牺牲很多”,东佬觉得“诺言根本没有实现”——这两种不满情
绪的震荡, 还有东西方心态的基本不同, 可以由一场政坛对话和“吵架”刻画。
(节译)
修柏乐是现任内政部长,一九八九年的统一条约由他主导。乌尔曼,在和平革
命起始时,组织了“立即民主”,参加了当时和西德政府对商的圆桌会议,而后在
东德过渡政府中任政务委员。两人,一西一东,都是当年直接参与促成统一的重要
人物。(原载《明镜周刊》,九月三十日)
问:去年统一日,给你们印象至深的是什么?
修:是十月三日那天夜晚。在国会大厦前,那种极为沉静的庆祝。没有大
声喧哗、没有大张旗鼓、没有嚣张的民族主义,而纯粹的只是一种喜悦。
乌:第二天,最末一届东德国会和西德国会第一次一起开会——我欢欣若
狂,可是没想到那场会沉闷极了。当然我也不想要什么嚣张的民族情绪,
可是,我当时在想,怎么这么就事论事呀,好像这个会根本不知道围墙刚
垮了,暴政灭亡了。我失望得很。
修:可是统一是三号;四号就是正常工作的日子呀。
乌:可是那历史的重量,我一点没感觉到。对我而言,统一是我一生中最
最重要的一件事。
修:对我也是。我们也许不再那么容易冲动,可是那不见得是坏事。我觉
得这件事咱们德国人实在干得不错。
问:你们认为德国人是一体了?
修:围墙倒塌就证明了:对,我们是一体的。
乌:我的护照里,在国籍一栏,向来都清楚地写着:“德国人”。可我觉
得,德国是在历史上统一了,但东西两边人民的权利并不平等。
修:我不懂您的意思。两边人民在经济、社会上确实还有很多不同,但权
利不平等是什么意思?
乌:您想想妇女、退休老人、或者艺术家的情况吧。
修:如果您说:东边一个退休老人的收入比西边的低,我同意。但我就得
说,他的收入可比两年前共产时代要多得多啦。
乌:这种比法完全不对,而你们老是这么比。
修:不对,乌先生,不只您,还有你们新邦的人应该这么说:你们不能老
跟西德的物质水准比,然后抱怨缺这个,少那个。你们要跟过去比。比起
东德时代,你们的生活好多了。那个“拖笨”车就快消失了
最近有个妇女很愉快地对我说,她现在总有奇异果在家里,那是她以
前想吃而吃不起的东西。这些小事情就是所谓生活水准。
乌:这场对谈越来越无聊了,修先生,我们东佬实在听你们谈奇异果听得
很厌烦了。
修:我说,东佬的生活比从前好多了。
乌:这您就大错特错了。生活并不只包含奇异果,还包含恐惧:失业了怎
么办?房租付不出了怎么办?我说权利不平等就是这个意思:西佬请得起
律师、税务顾问等等,东佬就不可能。
修: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嘿,你现在吃得起奇异果了,满足了吧!我同意
您的说法,人们现在最难的就是适应的问题,他们全身投入一个未知。但
是要变成像西德一样的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是东德人民自己的选择。
乌:太感情冲动了。
修:刚刚您说感情不够,现在又太多了。
乌:大家说起来好像当初我们有四种五种选择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
们一边是东德社会主义经济的烂摊子,另一边是时髦的西德——我们有什
么选择的余地?
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呢?
乌:我不反对您的说法,墙一开,东德就像糖化在水里一样消失了。但是
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慎思熟虑,怎么样稳住冲动的脚步。这一点没做到,
结果就是,输家太多了。
修:我们有庞大的计划,为新邦付出亿万的马克。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容
易在新市场中找到工作是真的,但这在西边也一样。我相信有许多人觉得
自己是输家,可是,我又不得不强调:统一的速度如此之快。我们也没有
选择。
在庆祝统一周年的今天,波昂的政治圈里最头痛迫切的问题,竟然不是经济问
题,而是在德东一连串的反外暴力事件。
在德东大城小镇,年轻人,光头、皮靴,成群结队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外国
人,用汽油弹和石块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甚至于纵火焚烧难民营。
到今年八月为止,对外国人的攻击事件高达四百件,但这种暴力不仅限于德东;
在四百件中,一百八十件在西边发生,只是德东通常较为暴烈,上个月有两名非洲
人被杀,一名越南人在街上被打得不成人形。
原因?
德东人说,求政治庇护的外国人夺走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使失业问题恶化。这
自然是非理智的找代罪羔羊的心理。外国人只占德东人口的百分之一。
对外国人的暴力,只是快速统一的后遗症之一。在东德的社会制度中,东德人
与外界隔绝(人民没有旅行自由),基本上,今天的德东人还是一个封闭的、没有
国际视野和经验的人民。统一,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以前习惯的安全
和依靠,更失去了自尊——统一使他们沦为大德国的二等公民。
气,就出在比他们更弱的外籍难民身上。
今年的统一庆典,德国想必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庆祝。去年的沉静,是因为德国
人顾忌别人对自己民族主义的猜疑。今年的沉静,是因为,统一的路途坎坷,德国
人实事求是的性格使他们无法放松自己。
辑三 大陆印象
吵 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
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
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
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
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
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
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
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
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
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
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
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
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
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
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
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
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
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 ※ ※ ※ ※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
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
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
声音——“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
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
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 ※ ※ ※ ※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
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
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