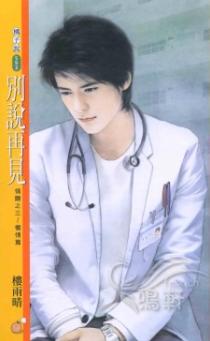别说我神经 作者:章无计-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章无计,你给我老实点,你卖的假酒喝死人了!
这句话像条蚯蚓在我身体里蠕动,我的脑袋立刻嗡嗡一片,我卖这么长的酒都没出事,怎么一下子就喝死人了?我小心翼翼地问,怕不是人家酒喝多了醉死的吧?女警察说,我们已经做了化验,是酒精中毒,你卖的酒含有超标的酒精度是罪魁祸首,你将被提起诉讼,现在惟一要做的就是配合我们调查清楚。
我连忙伸冤说,死了个人不能怨我,我是无辜的,你们抓错人了。
女警察冷笑道,不只死了一个,是死了一双,夫妻俩都是因为喝了你们的酒而双双毙命。
夫妻?我脑子里闪过一个问号,谨慎地问,他们喝完酒做啥事了没有?不能怨酒,夫妻一同死的案子很多都是快活死的。
章无计,你给我老实点,不主动交代这就是下场。女警察说着另只手拍向桌子,我阻止都来不及,眼看着她另一只手那柔嫩的掌心穿过像阴茎般的钉子,随之传来她欲哭无泪的“哎哟”声,我心想,那枚钉子这回算爽透了,爽了两回。
我交代什么呢,基本事实我都弄不清楚,张凹和猪头我暂且还不能提供出来,否则大家都没好日子过,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等他们来救我出去,我不担心这个,他们要是消极对我,终有一天我会咬出他们,想必这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部分 什么,有意外?什么,有意外?(3)
我后来被押到了看守所,曾经我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对这儿环境我很熟悉。只是物是人非,朋友们都换了几茬,他们对我的二进宫抱以同情,也没怎么为难我。除了心情不好时,这帮坏小子把我当沙包练拳击外,平时都比较克制,不像第一次进来,我充当一只足球的角色供他们娱乐。好歹,我现在也是革过命的人,他们畏惧这点。蒋小红像当初小花一样,隔三岔五来看我,她还为我请了律师,律师告诉我,张凹和猪头早跑了个没影,责任全推到我身上,我成了替罪羔羊。而我依旧保持清醒,他们会暗中帮助我,否则上庭之时就是他们送命之日,但遗憾的是,他们这一躲,公安局怕很难找到他们,都半年过去了,他们还说没找着人。
我放心不下的是李雪,她随蒋小红一道来看我,向我表达了她对我的切骨思念之情,还告诉我一个秘密,说张凹就是张平,她自己跑到厂子里调查的。我说你不是看不见么?李雪说,通过询问和对他的种种特征对比,加上与朱大春的关系可以确信他就是隐名埋姓的张平。我说,你肯定弄错了,我看过他,根本不像,这个不能乱说,万一人家告你个诽谤罪就收不了手了。
在我看来,张凹的确有张平的影子,不过在没有事实根据前我不会乱给人扣帽子,再说,只要他救我出去,我没必要逮住他纠缠不放,过去的事再翻回来,痛苦的还是我们自己。李雪说,无计,你要这样想你就是个冷血动物。我说,自从脑子受伤后,我的血基本上没有热过。
光在看守所我就待了大半年,这段时间没有与表哥杨会谈是件遗憾的事,他现在应该在农场里劳动改造,太忙,见不着他也是情有可原。一直到夏天里蚊子吃人的时候,张凹才终于来探望我。他说他活动了很长时间,马上就可以结案子把我搞出去。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兄弟,我就靠你了。他安慰我说,应该的,应该的。
这酒是他造的,出了事他一点儿也不害臊,愣充是救世主让我感激他,不过我始终认为把我搞出去我就得感谢他。只是,这一晃,时间就要过去一年了。
法庭终于开庭审判了,我因为贩卖假酒而被执行两年刑期,缓期三年。也就是说,坐了大半年牢现在我终于可以出狱了。无论如何,张凹还算言而有信。我只是在后来有那么一个疙瘩解不开,这造酒的怎么就没一点责任呢?
蒋小红与李雪这两个人我一个都舍不下,一个是未婚妻,出来后要跟她把事办了;一个已经失明对我却满怀阳光之情,我不能丢下她,照顾她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为曾经的那份炽热的感情,也为现如今她对我的付出。
蒋小红说,是李雪去找的张凹求他弄你出来,可是,那天我看到她跑过来找我,委屈地哭个不停我问,为什么?蒋小红说,张凹凌辱了她,这是救你出来的惟一条件。他如果不赔偿死者家属的经济要求,你这个案子无法结束。可是,李雪她
我难以置信地去找李雪,她的样子黯淡多了,我问为什么要这样。李雪吞吞吐吐说,一是希望他帮你一把救你出来,二是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张平,可是他却利用了我。
我咬牙切齿问,结果呢,你验证到了什么?
李雪说,结果不重要了,你出来就好。
可是你呢,失去了什么知道吗?我有些怒不可遏,可李雪的眼睛让我无法发起火,它充满了无助和苍凉。
我出来以后,李雪却从此再不见我,她逃避我的感情,拒绝与我直面,然而我已经下了决心要照顾她一生。我告诉蒋小红这个想法,她没说什么,只是收拾了行李要搬回医院宿舍。我帮她收拾着,心里在说对不起,你们都是好女孩,只有我,是个惹事的人,倒霉的人。
我找到猪头,他在家里修身养性,我说这次要感谢张凹,没他我很难出来。猪头说,大家都是同事、朋友,他应该做的。我说,好,我买点东西去感谢他,这回我买的是真中华,用蒋小红的工资。
张凹果然牛烘烘,他的厂子平安无事,继续生产。别墅住着,汽车开着,小姐玩着。他这么牛的人我得真心投靠他,将来还得靠他让我事业腾飞,没有事业,我始终是个瘪三。
我很快发现我妈有些不对劲,我回来她应该感到高兴并为此悉心照顾我的生活,为我的身体茁壮成长而搞些有营养的东西犒劳我,安慰我。她做起事来处处小心,且不怎么配音,话语的缺失令我惊恐,这样的人内心压抑,很容易出乱子。我妈吃了饭往往不见了人影,她的消失跟我爸的消失成正比,一只脚前一只脚后。大哥大嫂早已有了自己的房子,二哥二嫂在家里住着,他们说老娘现在成了间谍,老是神神秘秘地跟踪老头,有时回来会哭一场,有时回来自个儿乐个不停。
我们一直不太相信我爸这样一个军人会做出如此不忠的事情,它违背一名军人应有的操守。在安慰我妈的同时,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加上我一致认为,我妈是在捕风捉影。我们很久没叫“妈”了,这个名称已经被“神经病”所替换,特别是我根本无法忍受我妈的反复唠叨和疯狂臆测。她太相信和专注于自己的感官触觉,只要是我爸有风吹草动她都要推测出一大堆事情来。买斤糖回来,她会说糖是别的女人家的;买把伞回来,她说是别的女人送的;如果老爸出去吃饭,她更坚决相信是去了那个女人家。我受不了的时候会说我妈“神经病”,她大义凛然地承认,我就是神经病,我要一刀刀割他的肉。我说,那是犯法的。她说,他死了,我还会活着么?我爸现在在我妈嘴里成了“他”的特指,他们之间形同陌路,我们做子女的和父母又何尝不是。
第二部分 什么,有意外?什么,有意外?(4)
综上所述,我叫我妈“神经病”是情有可原,被逼无奈的。从这个理由来说,不仅我妈,很多人都将成为神经病。这一群体不会被人理解和谅解,他们怪诞的举止语言,只是他们外部的表现而己,脑子里他们自己很清楚,只不过外人无法窥清。
我妈近期念叨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三十多年了,从没红过脸,现在怎么造了这个孽。
我安慰她的只有一句,这世界每个人都在造孽,不是不造孽,只是时辰未到。
同样的,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报应,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我妈和我爸已经沦落到不用语言沟通,进步到用形体来交流,手足还不够,还借用鞋子、椅子来表达。那天我正好在家,我爸也难得在家,我妈理所当然在家,他们在努力沟通一件事情。我佯装睡着,房间的门虚掩,半合着眼睛能瞟到他们,声音不大但在手舞足蹈,我竖起耳朵听清楚:我妈在质问我爸去某某小区干什么,我爸说我妈又在散扯;我妈说我爸做贼心虚,我爸说我妈没事干就到处跑;我妈说我爸挣钱也是给别人花,我爸说我就这样怎么搞;我妈说你不知道丑,我爸说你给我滚;我妈说你献丑献到了家,我爸拿起鞋子要掌我妈的嘴;我妈举起椅子要抵抗我爸的歹意,我爸与我妈虎视眈眈,剑拔弩张。我实在忍无可忍,愤怒而气势汹汹地走到他们之间,然后我悄然拿起大烟缸,往自己头上猛砸下去,我想破碎的烟缸落在地上会让他们停止暴力行为,恢复和平氛围,可惜的是,水晶烟灰缸质地优良,烟缸毫发未损,我当然也毫发无损,只是大脑一时浑然,眼前一片漆黑,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趔趄扑倒在地上。
我姥爷的如意算盘被彻底打翻,《新婚姻法》不合适宜地摆在他的面前,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对生活中的法律还是比较关注并打算随时以身献法,这么一来,他只能在大姥姥与我姥姥之间选择其一。先前下定决心娶我姥姥的态度此刻令他忐忑不安,他没有过多的底气和勇气来赌这一把,原因是,他明白糟糠之妻的价值。男人在吃着碗里霸着锅里的贪婪方面具有先天意识,可一旦有了得失之分,他就会慎重考虑。我姥爷从没如此痛苦过,犹豫过,彷徨过,无奈过。他有足够理由把赌注押在我姥姥身上,也有足够理由承担对大姥姥的责任,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他对自己说,好吧,抛个铜钱,字朝上的就不离婚,字朝下的就坚决离。然后他又想到真要字朝下离了,孩子怎么办?被他们杀了也不会有人同情,可字朝上,我姥姥又如何办,被她下鼠药毒害更是无人同情。思来想去,徘徊再三,姥爷还是决定抛个铜钱。他在心里默念,观音菩萨,您给指条路吧。接着他扔了一枚铜钱,铜钱“铛”的一声掉在地上。
然后呢,我急切问我妈,她很久没给我续这个故事了,坐牢回来以后她已经不善于言词。现在要不是我用烟灰缸砸晕自己,想必她也不会记着自己还会说这个故事,我倒认为她说故事的技巧急剧提高,专拣高潮的部分留着,正到了姥爷大抉择的时候,我妈戛然而止,我缓过神来,逼着她问,然后呢?
前面劲松家爸得癌症死了,你爸怎么却那么大命呢?
这个故事跟我爸的命有关联吗?
我妈总喜欢把话题往我爸身上扯,又不说好听的,尽想把我爸给咒死,我干脆鼓励她说,您要真觉得痛苦就去离婚吧。我妈不为所动地说,那太便宜他了,不能把便宜给人家占去了。她这么一说,我倒不怎么佩服她了,在我面前如此虚伪,可她在王阿姨张阿姨面前说的是,都一大把年纪了,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啊!
我能证明她跟我说话的虚伪,每次谈到这个话题她的眼神总在游移,面部表情略微扭曲,嘴巴有点打抖,鼻子不停翕合。
我妈对我的合理要求不管不问,她看到我爸因为争吵摔门而出后,后脚便跟上出了门。剩下我一个人揉着被烟灰缸砸肿的脑袋,自己告诉自己,没关系,就肿了一个包,不会有生命危险。
张凹还住在那儿,我和猪头拎着大堆东西前往私访,他那个小情人还是朱颜未改,穿着一条睡裙告诉我们,张凹出去办事了,稍后回来。然后又说,你们等会,我去洗澡。我和猪头安心坐在沙发上等,我尚未参观过这个地方,就踱着步随便观赏这所富丽堂皇的住宅。猪头在客厅看电视,我不小心逛到了卧室,说逛可能不太贴切,但这所别墅实在宽敞得很,闲庭散步也不为过。在卧室的梳妆台上,我被一样东西吸引,那是一张普通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却让我大惊失色,姓名一栏上赫然写着:花灰发。
我继续半年前的婚事筹办,只是女主角换成了李雪。蒋小红回到了宿舍,我欠她很多,临走我主动塞给她一笔钱,我不敢言说这是我致歉的赔偿费用,但它代表着我微薄的心意。可是蒋小红不领情,她大概知道我的难处,左推右拒,我心一急,不高兴地问,是不是嫌少?她愣了一下说,怎么可能呢,只是这二十块钱也不好挣,你留着更合适一些。我不容她推脱,口吻强悍,这二十块钱死都要给我收下。蒋小红叹了一声气说,好吧,我收下,我留给你的只有这封信。说着,她从皮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捏在手里,估计是封洋溢着真情实感的绝情书,里面肯定沾染了她太多的眼泪。但我明白,这些只能成为记忆,蒋小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