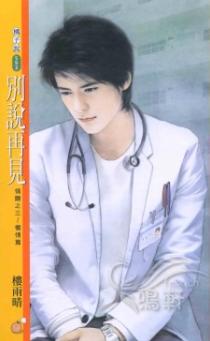别说我神经 作者:章无计-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
《别说我神经》作者:章无计
题记神经宣言
对!我就是“人渣”
没错!
说我“神经”也没关系
我就是我
漫画、天马行空、嘻哈
谈谈恋爱,玩玩时尚
High 并 Cool 着
记住,别企图复制我
千万别跟我拽
我是神经,我怕谁?
人渣的下一站,神经
这绝对是个有趣的故事,主人公在精神病医院里误伤了另一名精神病患者逃出了医院,母亲为唤醒他的意识和记忆在他犯病的时候跟他讲述祖辈的爱情故事。三条线索就此展开,外公那一代的爱情是旧时代的产物,母亲这一代的爱情是现实社会中的原生态体现,而主人公这一代的爱情充满戏剧夸张和无奈,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共同的结果——每一个都精神失常。
在作者眼里,世界本来就是荒诞不经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事非颠倒,黑白倒置,只有在最后关头,该神经的神经,该破碎的破碎,该死亡的死亡,一切的有趣都成为一种悲凉。
此文延续了作者上一部小说《我的人渣生活》的黑色幽默,反讽夸张的风格,用错位滑稽的另类手法来表现一个小人物悲喜无常的片段生活,放大他们在生活细微处的无奈和彷徨。此为作者现实题材“生活三部曲”的终结作品,也是作者创作风格渐趋成熟的代表作。
第一部分 透明的疯人院透明的疯人院(1)
我是一个忧郁的傻子。
说我是个傻子我不谦虚,但那些坏蛋老是说我缺点,戳我痛处,他们甚至还旁若无人地起哄,口无遮拦地喊:“啊,神经病!”我心里气急,胸膛像放了几吨非法制造的鞭炮,随时有可能爆炸,无情地闹出人命。但我也算是个有教养的人,义愤填膺也无法令我丧失“无计式”的典雅风度,我向来不跟他们计较。
听蒋小红说,我前些日子失过忆,脑袋被硬东西碰过,不但很难记起过去的小姑娘,遇到阴天或者其他不测风云就会显得脾气暴躁,比较集中的症状就是嘴巴里念念有词:我是人渣杀啊砍啊小花回来吧犯病的时候,我的意识是不清楚的,就像在一本书里看到的形容高潮时产生的幻觉一样,书名大概是《新婚必读》。我觉得那是条件反射,内心里不情愿或者有意为之都无法真实地反映出去,这大概是他们所说的精神病类型——神经不正常。
失忆我是承认的,面前这个叫蒋小红的护士跟我扯了大半天,说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听得迷迷糊糊,乍悲还喜,心潮澎湃,孤独无助,各种感觉都能浅尝一二,但却无法对号入座。我觉得自己除了傻一点,神经一点以外,绝没有故事中的章无计那么人渣。他那种人不说千刀万剐也得五马分尸,连蒋小红都唏嘘不已的小花在无计面前却成了一堆粪土,这种不珍惜感情的人简直就是人渣中的败类。我比人渣优秀点,不论智商的话。
通常意义上的傻子无非是喜欢在太阳底下长时间地发呆,眼神呆滞,嘴角流涎。我不反对他们叫我傻子,但我与他们口中所谓的傻子又是大大的不同,我是一个忧郁的傻子。比如,我就经常对着墙壁上我自己写的两行字怔怔发呆,那字写得遒劲有力,粗细匀和,特别是在日头的照耀下,更显得熠熠闪光,那两行字是:
为朋友两肋插刀,
为女人插朋友两刀。
我思考的时候很反感别人的打扰,在为女人插朋友两刀的字体之下,我一坐就是一整天,饭可不吃,水可不喝,我觉得精神食粮比大米白馍要崇高得多。身体死了,精神永存,所以我很注重对精神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我在思考是插朋友心脏令其一命呜呼,还是戳其坐骨神经使其痛不欲生。偏偏每到这时,同病房的病人朋友们就会嚷道:神经病要犯神经了!我瞪着眼看他们,想尽量用自己的英武之气镇住他们,哪晓得其中一个脑袋被牛踩过的精神病患者拿起喝水的勺子向我眼睛插来。我忙问,为啥要这样?他龇牙咧嘴地叫:你是牛,你是牛,我要挖你的眼珠
医院也跟一个大澡堂一样,脱光了谁都清楚谁,时间长了,什么人肚脐眼长毛,什么人有什么辉煌事迹大家心里都有一本明账。有些因为事迹突出而受大家的追捧,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那天不知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一个院级偶像跟我说话了,他是整个精神病医院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那天阳光贼好,整座医院竟没有一个发病的,看起来,在那么好的太阳底下,这些人也平静得跟刚出生的婴儿般。我的偶像是这里的长辈,在这个医院至少呆了十年时间,这是我从一个据说是因为胡言乱语被诊断为精神癫痫者口中得到的可靠情报。我在草坪上正全神贯注听蒋小红一日三遍地说一个关于人渣的故事,故事冗长无奇,我听得哈欠连连,但即便这样也还是不愿意别人来打扰,蒋小红圆圆的脸蛋和鼓囊囊的胸脯让我从中得到故事之外的快意。这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偶像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出现令我产生片刻的心理抽搐——我盯在一上一下的胸脯上的目光突然被挡住。偶像幽灵般的出现搞得我差点晕厥过去。
他终于过来和我打招呼了,我觉得这个机会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我谦卑地迎上去,他“嗯”了一声,伸出手,我瞧见他手中夹着烟卷,烟屁股脏兮兮的,不像是从烟盒里掏出来的。他一“嗯”我就明白了,立刻把火给偶像点上,怯懦地问:偶像,您贵姓呐?
我姓花,叫灰发,人称发哥。
我惊叫一声“原来是发哥”,连忙用另一只手遮住打火机,口中念叨“花—灰—发”。偶像开口道,别念太多,小心闪着舌头。我“哦哦”答应着,然后关打火机。这下连自己也纳闷,我看到我手中握着的不是打火机,而是半截冰棒棍儿。偶像却栩栩如生地吸了起来,还啧啧称赞:好烟,好烟。我嘴巴半天合不上来,我痛恨自己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就融入不到他们当中去呢?难道智商高也是错吗?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不想加入到上流社会中的高智商人群不是合格的精神病人。这座围墙困了我好几个月,我总是逃不出护士小姐的魔掌。蒋小红每次带我出去散步晒太阳时总会在出门前让我喝些不知名的药,大多时间她都趁我昏昏欲睡时,掰开我的嘴巴把药丢进去,偶尔是用自己的淫威强行让我喝下去。她力气特大,我不是她对手,我在前面跑,她在后面追,从病房跑到走廊,又从走廊折回病床上,她强行压住我,掰开我嘴巴,伸出手往里按,她气喘吁吁,我呻吟不断:“不要不要”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或许也能推开她,但她双胸压着我,我就没劲了,只好束手就擒。吃完药后带我出去散步,我只要试图甩开她逃离这地方,药性就起了作用,头晕,脚软,心律失常,蒋小红变成了两个,想逃?没门儿!
为了逃出这个地方,我越来越忧郁了,整天无所事事。被蒋小红逮到吃完药以后就胡思乱想起来,眼睛无光,神情呆滞,连看到偶像也变得暴躁不安,恨不得去撕烂他的衣服。要知道,对一个偶像产生冒犯的欲念,那足以说明此人精神有问题。暗地里,我早就开始琢磨这里的地形了,围墙之外是安徽大学,只要翻过前方的围墙我就可以混迹于安徽著名的高等学府,与天之骄子们走在一起,谁会看出我是神经病呢?那座围墙有一人多高,没有强壮的体魄和足够的力气是无法将它征服于胯下的。为此,我每天加大饭量,从一天两碗稀饭一个馍发展成两个馍数碗稀饭;别人在饭后散步打牌,我却珍惜时间发发神经,嘴巴大喊:“我是人渣我是坏蛋我是神经病”蒋小红冲我摇头,说,无计,你的病怎么就是好不了呢?我傻傻地朝她笑,身子往后退,退到围墙时,捡起地上的碎石块猛砸,还大声地骂:你是人渣,你是人渣,砸死你蒋小红扭过头不看我,她的神情悲伤极了,像看到我在寻短见似的。砸了一会儿,看蒋小红不注意,抬腿试了试,可以踩得住脚便收工回去,明天再来砸第二道口子。
第一部分 透明的疯人院透明的疯人院(2)
连续发了一个礼拜的神经,那座围墙凹陷出七个口子,我发点劲儿就可以攀登上去,然后纵身一跃就到了高等学府。一边是精神病医院,一边是天堂,眼看我就要改头换面,心里越想越激动,证明了那句话:有付出就有收获。我设计好一幕:饭后出去散步千万不能吃蒋小红的药,若把药灌在她嘴巴里,不但我能逃过一劫,对她自己也有益——抓一个逃犯是要冒着生命风险的,我不想逃离精神病医院时伤及到蒋小红无辜的性命。
没办法,还是照老规矩吧!我问蒋小红,怎样分辨章鱼的手和脚?蒋小红一愣,想了想说,走路的是脚,吃饭的是手。我说,废话,章鱼啥时走路来着?啥时看到它吃饭了?蒋小红又想了想说,从别人口袋里掏钱的是手,踩住钱的是脚。我纳闷:这个答案怎么想出来的?蒋小红拍手道:我聪明吧!章鱼就是乌贼,贼一般都是这样子的!
我说,我对你五体投地。此贼非彼贼,答案错了十万八千里,这是个脑筋急转弯,说出来会让你笑破肚皮的,再想。蒋小红挠头,说想不出来。我说,那你替我吃药,我告诉你答案,保准你乐呵呵地笑。蒋小红将药片拿起来端详,自言自语地说,我可没病。我说,你嘴角裂了!蒋小红张嘴伸出舌头去舔,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药片塞到蒋小红的张开着的窟窿里,在她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时,我已经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一溜烟跑到医院的围墙下。蒋小红撒腿追出来,我赶紧循着前几天砸出的砖口子往上攀登,蒋小红速度也不赖,夹着一股阴风转眼就已到了我的脚下,只要她伸手我就前功尽弃。我想这次还是失败了,药性还没发作,恐怕难以逃脱她的魔掌了,正在我闭眼准备束手就擒时,就看蒋小红像中了子弹似的,绵软的瘫了下去。我心下一亮,立刻跟猴子爬树似的攀到围墙顶,然后闭上眼纵身跃了下去,脑袋里思绪万千,心情更是难以言表。多少日子与一群病人为伍,多少日子被强迫吃药,多少日子被人喊“神经病”,终于有机会摆脱这种噩运,终于与梦想中的学子们为友,我、我、我我痛死了,全身像插满了针。努力睁开眼,定睛一看,这一看吓得我魂飞魄散——我摔在了一棵仙人掌上,它身上的剌很够义气地留在我身上。从几米高的围墙上跳下来,迎接我的怎么会是它呢?可是,看到墙上一行油漆字我又明白了,上面写着:
精神病患者不得入内!
我以为那边是天堂,所以我不要命地跳下去,谁知道那不过是一副假象,它不但让我重归精神病医院,还在我身上留下了“越院逃跑”的终身印迹。那边的天之骄子们也愧对大学几年的粮食供养,他们的精神食粮匮乏得要命,见义勇为或者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越来越难以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我跳下时有对帅男靓女当时偎在一起,屁股下是一方石墩,我跃下的刹那瞄见男的一双黑手正往女的下半身包抄过去。看到我飞过来,他们倒也知趣地终止了欲火中烧的场面,站起来,对我投来同情的眼光。我忍着痛说,对不起,你们继续。那女的翻了我一眼,甩给我几个字:神经病!便挽着男的胳膊扭秧歌似的甩头走了。但是扭得幅度过大,让人有理由怀疑她是先天性小儿麻痹。
怎么能这样子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医院的护士找过来对我不停的唠叨,说无计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逃跑解决不了你精神上的问题,你必须端正态度,正视你的思想,惟一的出路就是配合好蒋小红,早日治好病,那样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精神病医院。我说,我可以悄悄的吗?我可不想让大伙儿看到我章某人刚从精神病医院放出来,跌份儿的事在我身上屡见不鲜,等病好了,就满足我这小小的要求,让我翻墙跳到安大里,改头换面做一回知识分子。
这种状况是社会的一个特征,环境往往让一个人身不由己去承认实际上不存在的事情。思来想去,我总结出,只要院方不同意我“逃”出去,就算到天涯海角也洗脱不了我神经病的罪名。没有办法,我被他们抬回医院,看到蒋小红正在给病人擦洗,我说,过来看看我身上有几个洞?她没反应,依然故我。我猛地掀开上衣,仙人掌给我的伤痕像蚯蚓一样呈现在她的面前,她瞪着眼睛嗔怒道:你跑得了吗?惹得一身伤,这下死心了?来,我给你敷药!
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多么好的一个护士,不记着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