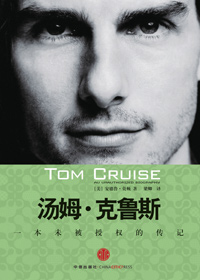约翰·克利斯朵夫-第7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双旧拖鞋;衬衣在裤腰上面扭做一团,钮扣也没完全扣好。克利斯朵夫嘟囔着向他通报
姓名,他却睁着没有光彩的倦眼瞧着他,机械的行了个礼,一声不出,对着一张椅子点
点头教克利斯朵夫坐下;接着他叹了口气,望半榻上倒下身子,把靠枕堆在自己周围。
克利斯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曾经很荣幸的你先生曾经对我一番好意我是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
哈斯莱埋在半榻里促膝而坐,右边的膝盖耸得跟下巴一样高,一双瘦削的手勾搭着
放在膝盖上。他回答说:
“想不起。”
克利斯朵夫喉咙抽搐着,想教他记其他们从前会面的经过。要克利斯朵夫提到这些
亲切的回忆原来就不容易,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尤迫使他受罪:他话既说不清,字又找不
到,胡言乱语,自己听了都脸红了。哈斯莱让他支吾其词,只用着那双心不在焉的淡漠
的眼睛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讲完了,哈斯莱把膝盖继续摇摆了一会,仿佛预备克利斯朵
夫再往下说似的。随后,他回答:
“对可是这些话并不能使我们年轻啊”
他欠伸了一会,打了个呵欠:“对不起没睡好昨天晚上,在戏院里吃了消
夜〃他说着又打了个呵欠。
克利斯朵夫希望哈斯莱提到他刚才讲过的事;但哈斯莱对那些往事一点不感兴趣,
连一个字也没提,也不问一句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情形。他打完了呵欠,问:
“你到柏林很久了吗?”
“今天早上才到。”
“啊!〃哈斯莱除了这样叫一声,也没有别的惊讶的表示。“什么旅馆?”
说完他又不想听人家的回答,只懒懒的抬起身子,伸手去按电铃:
“对不起,〃他说。
矮小的女仆进来了,始终是那副放肆的神气。
“凯蒂,〃他说,〃难道你今天要取消我一顿早饭吗?”
“您在会客,我怎么能端东西来呢?〃她回答。
“干吗不?〃他一边说一边俏皮的用眼睛瞟了瞟克利斯朵夫。〃他喂养我的思想;我
喂养我的身体。”
“让人家看着您吃东西,象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您不害羞吗?”
哈斯莱非但不生气,反而笑起来,改正她的句子:“应当说象日常生活中的动物
〃他又接着说:“拿来罢,我只要吃早饭,什么难为情不难为情,我才不管呢。”
她耸耸肩退出去了。
克利斯朵夫看到哈斯莱老不问其他的工作,便设法把谈话继续下去。他说到内地生
活的苦闷,一般人的庸俗,思想的狭窄,自己的孤独。他竭力想把自己精神上的痛苦来
打动他。可是哈斯莱倒在半榻上,脑袋倚着靠枕望后仰着,半阖着眼睛,让他自个儿说
着,仿佛并没有听;再不然他把眼皮撑起一忽儿,冷冷的说几句挖苦内地人的笑话,使
克利斯朵夫没法再谈更亲密的话。——凯蒂捧了一盘早餐进来了,无非是咖啡,牛油,
火腿等等。她沉着脸把盘子放在书桌上乱七八糟的纸堆里。克利斯朵夫等她出去了,才
继续他痛苦的陈诉,而那又是极不容易说出口的。
哈斯莱把盘子拉到身边,倒出咖啡,呷了几口;接着他用一种又亲热,又随便,又
有点儿轻视的神气,打断了克利斯朵夫的话:“也来一杯吧?”
克利斯朵夫谢绝了。他一心想继续没有说完的句子,但越来越丧气,连自己也不知
说些什么。看着哈斯莱吃东西,他的思路给扰乱了。对方托着碟子,象孩子一样拚命嚼
着牛油面包,手里还拿着火腿。可是他终究说出他作着曲子,说人家演奏过他为赫贝尔
的《尤迪特》所作的序曲。哈斯莱心不在焉的听着,忽然问:“什么?”
克利斯朵夫把题目重新说了一遍。
“啊!好!好!〃哈斯莱一边说,一边把面包跟手指一起浸在咖啡杯里。
他的话只此一句。
克利斯朵夫失望之下,预备站起身来走了;但一想到这个一无结果的长途旅行,他
又鼓其余勇,嘟囔着向哈斯莱提议弹几阕作品给他听。哈斯莱不等他说完就拒绝了。
“不用,不用,我对这个完全外行,〃他说话之间大有咕噜,挖苦,和侮辱人的意味。
〃并且我也没有时间。”
克利斯朵夫眼泪都冒上来了。可是他暗暗发誓,没有听到哈斯莱对他的作品表示意
见,决不出去。他又惶愧又愤怒的说道:
“对不起;从前你答应听我的作品;我为此特意从内地跑来的,你一定得听。”
没见惯这种态度的哈斯莱,看到这愣头傻脑的青年满脸通红,快要哭出来了,觉得
挺好玩,便无精打采的耸耸肩,指着钢琴,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说:
“那末来吧!”
说完他又倒在半榻上,仿佛想睡一觉的样子,用拳头把靠枕捶了几下,把它们放在
他伸长的胳膊下面,眼睛闭着一半,又睁开来,瞧瞧克利斯朵夫从袋里掏出来的乐谱有
多少篇幅,然后他轻轻叹了口气,准备忍着烦闷听克利斯朵夫的曲子。
克利斯朵夫看到这种态度又胆小又委屈,开始弹奏了。哈斯莱不久便睁开眼睛,竖
起耳朵,象一个艺术家听到一件美妙的东西的时候一样,不由自主的提起了精神。他先
是一声不出,一动不动;但眼睛不象先前那么没有神了,撅起的嘴唇也动起来了。不久
他竟完全清醒过来,叽叽咕咕的表示惊讶跟赞许,虽然只是些闷在喉咙里的惊叹辞,但
那种声音绝对藏不了他的思想,使克利斯朵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哈斯莱不再计算
已经弹了多少,没有弹的还有多少。克利斯朵夫弹完了一段,他就嚷:
“还有呢?还有呢?”
他的话慢慢的有了人味儿了:
“好,这个!好!妙!妙极了!该死!〃他嘟囔着,非常惊讶。〃这算
什么呢?”
他半起来,探着脑袋,把手托着耳朵,自言自语的,满意的笑着;听到某些奇怪的
和声,他微微伸出舌头,好象要舔嘴唇似的。一段出岂不意的变调使他突然叫了一声,
站了起来,跑到钢琴前面挨着克利斯朵夫坐下。他仿佛不觉得有克利斯朵夫在场,只注
意着音乐。曲子完了,他抓起乐谱,把刚才那页重新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以后的几页,
始终自言自语的表示赞美和惊讶,好象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怪了!亏他想出来的,这家伙!”
他把克利斯朵夫挤开了,自己坐下来弹了几段。在钢琴上,他的手指非常可爱,又
柔和,又轻灵。克利斯朵夫瞧着他保养得挺好的细长的手,带点儿病态的贵族气息,跟
他身体上别的部分不大调和。哈斯莱弹到某些和弦停住了,反复弹了几遍,眯着眼睛,
卷着舌头发出的的笃笃的声音,又轻轻学着乐谱的音响,一边照旧插几个惊叹辞,表示
又高兴又遗憾:他不由得暗中气恼,有种下意识的嫉妒,而同时也感到非常快乐。
虽然他老是自个儿在说话,好象根本没有克利斯朵夫这个人;克利斯朵夫却高兴得
脸红了,不免把哈斯莱的惊叹辞认为对自己发的。他解释他的旨趣。先是哈斯莱没留神
他的话,只顾高声的自言自语;后来克利斯朵夫有几句话引起了他注意,他就不作声了,
眼睛老钉着乐谱,一边翻着一边听着,神气又象并不在听。克利斯朵夫越来越兴奋,终
于把心里的话全说了出来:他天真的,激昂的,谈着他的计划和生活。
哈斯莱不声不响,又恢复了含讥带讽的心情。他让克利斯朵夫把乐谱从他手里拿了
回去:肘子撑在琴盖上,手捧着脑门,望着克利斯朵夫,听他起着少年人的热情与骚动
解释作品。于是他想着自己早年的生活,想着当年的希望,想着克利斯朵夫的希望和在
前途等着他的悲苦,不禁苦笑起来。
克利斯朵夫老在那里说着,低着眼睛,生怕找不到话接上去。哈斯莱的静默使他胆
子大了些。他觉得对方在打量他,一句不漏的听着他;仿佛他们中间冰冷的空气给他融
化了,他的心放出光来了。说完之后,他怯生生的,同时也很放心的,抬起头来望望哈
斯莱。不料他看到的又是一双没有神的,讥讽的,冷酷的眼睛在那里瞪着他,心中才开
始的那点儿喜悦,象生发太早的嫩芽一般突然给冻坏了。他马上把话打住了。
默然相对了一会,哈斯莱开始冷冷的说话了。这时他又拿出另外一种态度,对克利
斯朵夫非常严厉,毫不留情的讥讽他的计划,讥讽他的希望成功,好似自嘲自讽一样,
因为他在克利斯朵夫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他狠命的摧毁克利斯朵夫对人生的信
念,对艺术的信念,对自身的信念。他不胜悲苦的拿自己做例子,痛骂自己的近作:
“都是些狗岂不通的东西!为那般狗岂不通的人只配这种东西。你以为世界上爱音
乐的人能有十个吗?唉,有没有一个都是疑问!”
“有我啊!〃克利斯朵夫兴奋的嚷着。
哈斯莱瞧着他,耸耸肩,有气无力的回答说:
“你将来也会跟别人一样,只想往上爬,只想寻欢作乐,跟别人一样而这个办
法是不错的”
克利斯朵夫想和他辩;可是哈斯莱打断了他的话,拿起他的乐谱,把刚才赞扬的作
品加以尖刻的批评。他不但用难听的话指摘青年作家没留意到的真正的疏忽,写作的缺
点,趣味方面或表情方面的错误;并且还说出许多荒谬的言论,和使哈斯莱自己受尽痛
苦的,那班最狭窄最落伍的批评家说的一模一样。他问这些可有什么意思。他简直不是
批评,而是否定一切了:仿佛他恨恨的要把先前不由自主感受的印象统统抹掉。
克利斯朵夫失魂落魄,不想回答了。在一个你素来敬爱的人嘴里,听到那些令人害
臊的荒唐的话,你又怎么回答呢?何况哈斯莱什么话都不愿意听。他站在那儿,手里拿
着阖上的乐谱,睁着惘然失神的眼睛,抿着嘴巴。末了,他好似又忘了克利斯朵夫:
“啊!最苦的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你!”
克利斯朵夫激动到极点,突然转过身来把手放在哈斯莱的手上,抱着一腔热爱,又
说了一遍:“有我呢!”
可是哈斯莱的手一动也不动;即使这青年的呼声使他的心颤动了一刹那,但瞅着克
利斯朵夫的那双黯淡的眼睛并没露出一点儿光采。讥讽与自私的心绪又占了上风。他把
上半身微微欠动一下,滑稽的行了个礼,回答说:“不胜荣幸!”
他心里却想道:“哼!那我才不在乎呢!难道为了你,我就白活一辈子吗?”
他站起身来,把乐谱望琴上一丢,拖着两条摇晃不定的腿,又回到半榻上去了。克
利斯朵夫明白了他的思想,感到了其中的隐痛,高傲的回答说,一个人用不着大家了解,
有些心灵抵得上整个的民族;它们在那里代替民族思想;它们所想的东西,将来自会由
整个民族去体验。——可是哈斯莱已经不听他的话了。他回复了麻痹状态,那是内心生
活逐渐熄灭所致的现象。身心健全的克利斯朵夫是不会懂得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的,他
只模模糊糊的觉得这一下是完全失败了;但在差不多已经成功的局面之后,他一时还不
肯承认失败。他作着最后的努力,想把哈斯莱重新鼓动起来:他拿着乐谱,解释哈斯莱
所挑剔的某些不规则的地方。哈斯莱却埋在沙发里,始终沉着脸一声不出,他既不首肯,
也不反对:只等他说完。
克利斯朵夫明明看到留下去没有意思了,一句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他卷起乐谱,站
起身子。哈斯莱也跟着站起。胆怯而惶愧的克利斯朵夫嘟嘟囔囔的表示歉意。哈斯莱微
微弯了弯腰,用着高傲而不耐烦的态度伸出手来,冷冷的,有礼的,送他到大门口,没
有一句留他或约他再来的话。
克利斯朵夫回到街上,失魂落魄。他望前走着,糊里糊涂走过了两三条街,又到了
来时下车的站头。他搭上电车,根本不知自己做些什么。他倒在凳上软瘫了,手臂,大
腿,都好象折断了。不能思索,也不能集中念头:他简直一无所思。他怕看自己的内心。
因为内心只有一平空虚。在他四周,在这个城里,到处都是空虚,他连气也喘不过来:
雾气跟高大的屋子使他窒息。他只想逃,逃,越快越好,——仿佛一离开这儿就能丢下
他在这儿遇到的悲苦的幻灭。
回到旅馆,还不到十二点半。他来到这个城里只有两小时,——那时他心里是何等
光明!——现在一切都是黑暗了。
他不吃中饭,也不进房间,迳自向店里要了帐单,付了一夜的租金,说要动身了:
店主人听了大为奇怪,告诉他不用这么急,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