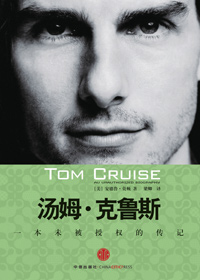约翰·克利斯朵夫-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停了,众人的笑骂可并不跟着停止:能有个机会说克利斯朵夫坏话真是太高兴了!连
续好几个星期,《伊芙琴尼亚》成为挖苦的资料。大家知道克利斯朵夫再没自卫的武器,
就尽量利用机会,唯一的顾忌是他在宫廷里的地位。虽然他跟那位屡次责备他而他置之
不理的大公爵很冷淡,他仍不时在爵府里走动,所以群众认为他还得到官方的支持,—
—有名无实的支持。——而他还要把这最后一个靠山亲自毁掉。
他受了批评。它不但针对他的作品,还牵涉他那个新的艺术形式,那是人家不愿意
了解的,可是要把它歪曲而使它显得可笑倒很容易。对于这种恶意的批评,最好是置之
不理,继续创作:但克利斯朵夫还没有这点儿聪明。几个月以来,他养成了坏习惯,对
一切不公平的攻击都要还手。他写了一篇把敌人们丑诋一顿的文章,送给两家正统派的
报馆,都被退回了,虽然退稿的话说得很婉转,仍带着讥讽的意味,克利斯朵夫固执起
来,非想法登出来不可。他忽然记起城里有一份社会党的报纸曾经想拉拢他。他认识其
中的一位编辑,有时和他讨论过问题的。克利斯朵夫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人,敢毫无忌讳
的谈到当局,军队,和一切压迫人的古老的偏见。可是谈话的题目也至此为止,因为那
社会主义者说来说去脱不了马克思,而克利斯朵夫对他就没有兴趣。他觉得那个思想自
由的人物,除了一套他不大喜欢的唯物主义以外,还有刻板的教条,思想方面的专制,
暗中崇拜武力,简直是另一极端的军国主义;总之他的论调和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每天听
到的并没多大分别。
虽然如此,他被所有的编辑封锁之后,他所想到的还是这位朋友和他的报纸。他很
知道他的举动会骇人听闻:那份报纸素来很激烈,专门骂人,大家都认为要不得的;但
克利斯朵夫从来不看它的内容,所以只想到那些大胆的思想(那是他不怕的),而没想
到它所用的卑鄙的口吻(那是他看了也要厌恶的)。并且别的报纸暗中联合起来打击他,
使他恨无可泄,所以即使他知道报纸的内容,也不见得会顾虑。他要教人知道要摆脱他
没这么容易。——于是他把那篇文章送到社会党报纸的编辑部,大受欢迎。第二天,文
章就给登出来了,编者还加上一段按语,大吹大擂的说他们已经约定天才青年,素来对
工人阶级的斗争极表同情的克拉夫脱同志长期执笔。
克利斯朵夫既没看到自己的文章,也没看到编者的按语,那天是星期日,天没亮他
就出发往乡下散步去了。他兴致很好,看着太阳出来,又笑又叫,手舞足蹈。什么杂志,
什么批评,一古脑儿丢开了!这是春天,大自然的音乐,一切音乐中最美的音乐,又奏
起来了。黑洞洞的,闷人的,气味难闻的音乐厅,可厌的同伴,无聊的演奏家,都给忘
得干干净净!只听见喁喁细语的森林唱出奇妙的歌声;令人陶醉的生气冲破了地壳,在
田野中激荡。
他给太阳晒得迷迷忽忽的回家,母亲递给他一封信,是他不在的时候爵府里派人送
来的;信上用的是公事式的口气,通知克拉夫脱先生当天上午就得到府里去一次。上午
早已过了,时间快到一点,克利斯朵夫可并不着急。
“今儿太晚了,〃他说,〃明儿去吧。”
可是母亲觉得不妥:“不行,亲王找你去,你得马上去,或许有什么要紧事儿。”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要紧事儿?那些人会跟你谈什么要紧事儿吗?还不是说
他那一套关于音乐的见解,教人受罪!只希望他别跟西格弗里德?曼伊哀比本领,
也写一①曲什么《颂歌》!那我可不客气喽。我要对他说:你干你的政治吧!你在政治
方面是主人,永远不会错的,可是艺术,替我免了吧!谈到艺术,你的头盔,你的羽饰,
你的制服,你的头衔,你的祖宗,统没有啦;我的天!试问你没有了这些,你还剩
什么?”
①西格弗里德?曼伊哀为当时德国写煽动文字的评论家替德皇起的诨名。——原注
把什么话都会当真的鲁意莎举着手臂喊起来:
“怎么能说这个话!你疯了!你疯了!”
他看母亲信以为真,更故意跟她玩儿,尽量吓唬她。鲁意莎直到他越来越荒唐了才
明白他在逗她,便转过背去说:
“你太胡闹了,孩子!”
他笑着拥抱她。他兴致好极了:散步的时候有个美丽的调子在胸中蹦呀跳的,好似
水里的鱼儿。他肚子饿得很,必要饱餐一顿才肯上爵府去。饭后,母亲监督着他换衣服;
因为他又跟她淘气,说穿着旧衣衫和沾满了灰土的鞋子,也没有什么不体面。但临了他
仍旧换了一套衣服,把鞋子上了油,嘴里嘁嘁喳喳的打着唿哨,学做各式各种的乐器。
穿扮完了,母亲给检查了一遍,郑重其事的替他把领带重新打过。他竟例外的很有耐性,
因为他对自己很满意,——而这也不是常有的事。他走了,说要去拐走阿台拉伊特公主。
那是大公爵的女儿,长得相当美,嫁给德国的一个小亲王,此刻正回到母家来住几个星
期。克利斯朵夫小时候,她对他很好;而他也特别喜欢她。鲁意莎说他爱着她,他为了
好玩也装做这个样子。
他并不急于赶到爵府,一路瞧瞧谱子,看到一条象他一样闲荡的狗横躺着在太阳底
下打呵欠,就停下来把它摩一会。他跳过爵府广场外面的铁栏,——里头是一大块四方
形的空地,四面围着屋子,空地上两座喷水池有气无力的在那儿喷水;两个对称的没有
树荫的花坛,中间横着一条铺着沙子的小路,象脑门上的一条皱痕,路旁摆着种在木盆
里的橘树;场子中央放着一座不知哪一个公爵的塑像,穿着路易?菲力普式的服装,座
子的四角供着象征德性的雕像。场中只有一个闲人坐在椅子上拿着报纸打盹。府邸的铁
栏前面,等于虚设的岗位上空无一人。徒有其名的壕沟后面,两尊懒洋洋的大炮似乎对
着懒洋洋的城市打呵欠。克利斯朵夫看着这些扯了个鬼脸。
他走进府第,态度并不严肃,至多是嘴里停止了哼唱,心却照旧快活得直跳。他把
帽子望衣帽间的桌上一扔,毫不拘礼的招呼他从小认识的老门房。——当年克利斯朵夫
跟着祖父晚上第一次到府里来看哈斯莱,他已经在这儿当差了:——老头儿对于他嘻嘻
哈哈的说笑一向不以为忤,这一回却是神色傲慢。克利斯朵夫没注意。更望里走,他在
穿堂里又碰到一个秘书处的职员,平索对他怪亲热,话挺多的,这回竟急急忙忙的走过
了,避免和他搭讪,克利斯朵夫看了很奇怪。可是他并不拿这些小节放在心上,只管往
前走去,要求通报。
他进去的时候,里头刚吃过中饭。亲王在一间客厅里,背靠着壁炉架,抽着烟和客
人谈天;克利斯朵夫瞥见那位公主也在客人中间抽着烟卷,懒洋洋的仰在一张靠椅中,
和四周的几个军官高声说着话。宾主都很兴奋;克利斯朵夫进门就听到大公爵一起粗豪
的笑声。可是亲王一看见克利斯朵夫,笑声马上停止。他咕噜了一声,直扑过来嚷道:
“嘿!你来啦!你终于赏光到这儿来啦!你还想把我耍弄下去吗?你是个坏东西,
先生!”
克利斯朵夫被这当头一棒打昏了,呆了好一会说不上话来。他只想着他的迟到,那
也不至于受这样的羞辱啊,他便结结巴巴的说:“亲王,请问是怎么回事?”
亲王不理他,只顾发脾气:“住嘴!我决不让一个坏蛋来侮辱我。”
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白,喉咙抽搐着发不出声音;他挣扎了一下,嚷道:
“亲王,您既没告诉我是什么事,也就没权利侮辱我。”
大公爵转身对着他的秘书,秘书马上从袋里掏出一份报纸。他生那么大的气,不光
是因为性子暴躁,过度的酒也有相当作用。他直跳到克利斯朵夫面前,象斗牛士拿着红
布一般,抖开那张打皱的报纸拚命挥舞,怒不可遏的叫着:
“瞧你的脏东西,先生!你就配人家把你的鼻子揿在里面!”
克利斯朵夫认出那是社会党的报纸:“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说。
“怎么!怎么!你那样的无耻!这份混账的报纸!那班流氓天天侮辱我,说着
最下流的话骂我!”
“爵爷,我没看过这个报。”
“你扯谎!”
“我不愿意您说我扯谎,〃克利斯朵夫说。〃我没看过这个报,我只关心音乐。并且,
我自有爱在哪儿发表文章就在哪儿发表的权利。”
“你什么权利也没有,唯一的权利是不开口。过去我待你太好了。我给了你跟你的
家属多少好处,照你们父子两个的行为,我早该跟你们断绝了。我不准你再在跟我捣乱
的报上发表文字。并且将来不经我的许可,也不准你再写什么文字。你为音乐掀起的笔
墨官司,我也看够了。凡是有见识有心肝的人,真正的德国人所看重的东西,我不准一
个受我保护的人去加以攻击。你还是作些高明一点的曲子罢,要是作不出,那末练习练
习你的音阶也好。我不要音乐界里来一个社会党,搞些诋毁民族的光荣,动摇人心的玩
艺儿。谢谢上帝!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所以,还是弹你的琴
去罢,先生,别跟我们捣乱!”
肥胖的公爵正对着克利斯朵夫,把恶狠狠的眼睛直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青,
想说话,扯了扯嘴唇,嘟囔着说:
“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气都塞住了,羞愤交迸,快要哭出来;两条腿在那里发抖。他动了动胳膊,把旁
边家具上的一件东西撞倒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可笑,也的确听见有人笑着;他模模糊糊
的看到公主在客厅那一头和几个客人交头接耳,带着可怜他和讥讽他的意味。从这时期,
他就失了知觉,不知道经过些什么情形。大公爵嚷着。克利斯朵夫嚷得更凶,可不知道
自己说些什么。秘书和另一个职员走过来要他住嘴,被他推开了;他一边说话一边无意
中抓着桌上的烟灰碟子乱舞。他听见秘书喊着:
“喂,放下来,放下来!”
他又听见自己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把烟灰碟子望桌边上乱捣。
“滚出去!〃公爵愤怒之极,大叫起来。〃滚!滚!替我滚!”
那些军官走过来想劝公爵。他好象脑充血似的突着眼睛,嚷着要人家把这个无赖赶
出去。克利斯朵夫心头火起,差点儿伸出拳头去打公爵的脸;可是一大堆矛盾的心理把
他压住了:羞愧,忿怒,没有完全消灭的胆怯,日耳曼民族效忠君王的性格,传统的敬
畏,在亲王面前素来卑恭的习惯,都在他心头乱糟糟的混在一起。他想说话而不能说话,
想动作而不能动作;他看不见了,听不见了,让人家把他推了出来。
他在仆役中间走过。他们声色不动的站在门外,把吵架的情形都听了去。走出穿堂
的二三十步路,他仿佛走了一辈子。回廊越走越长,似乎走不完的了!从玻璃门里
望见的外边的阳光,对他象救星一样他踉踉跄跄的走下楼梯,忘了自己光着脑袋,
直到老门房叫他才回去拿了帽子。他拿出全身的精力才能走出府第,穿过院子,回到家
里。路上他把牙齿咬得格格的响。一进家里的大门,他的神气跟哆嗦就把母亲吓坏了。
他推开了她,也不回答她的问话,走进卧房,关了门倒在床上。他抖得那么厉害,竟没
法脱衣服,气也透不过来,四肢也瘫痪了。啊!但愿不再看见,不再感觉,不必再
支撑这个可怜的躯壳,不必再跟可羞可鄙的人生挣扎,没有气没有思想的倒下去,不要
再活,脱离世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脱下衣服,乱七八糟的摔在地下,人躺在
床上,把眼睛蒙住了。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他的小铁床在地砖上格格的响。
鲁意莎贴在门上听着,敲着门,轻轻的叫他:没有回音。她等着,听着房里寂静无
声好不揪心,然后她走开了。白天她来了一二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过去
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声音。克利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哆嗦,哭了好
几回;半夜里他抬起身子对墙壁晃晃拳头。清早两点左右,发疯似的一阵冲动使他爬下
了床,半裸着湿透的身子,想去杀死大公爵。恨与羞把他折磨着,身心受着火一般的煎
熬。可是这场内心的暴风雨在外面一点都不表现出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他
咬紧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