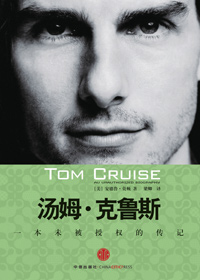约翰·克利斯朵夫-第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些作品的时候说的。大公爵冷冷的回答说:“听你他话,先生,有时人家竟会疑心你不
是德国人。”
①《哀丽阿》为门德尔松所作有名的清唱剧。
这句报复的话,从那么高贵的人嘴里吐出来,直流传到街头巷尾。凡是妒忌克利斯
朵夫的声名,或为了其他的私仇而和他过不去的人,立刻补充说,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
的德国人。大家记得他父系方面是佛兰德族。外方来的移民毁谤他所在国的荣誉当然不
足为奇。这一下可把事情解释明白了,而日耳曼民族除了看不起敌人以外,也更有理由
抬高自己的声价了。
至此为止,大家只是对克利斯朵夫作些精神上的报复,可是他还要提供更具体的材
料。一个人自己要被人批评的时候去批评别人,是最不智的事。换了一个聪明一点的艺
术家,一定会尊敬他的前辈。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别人的庸俗是应当瞧不起的,自己的力
量是应当得意的,没有理由把他的轻视别人和自己的得意藏在肚里。而他的表示得意又
是忘形的。最近一些时候,他非常的需要发泄。他一个人消受不了那么些欢乐,要不是
分一些给别人,他竟会快乐得爆裂的。既没有朋友,他就把乐队里的一个青年同事,叫
做西格蒙?奥赫的,当做心腹。他是魏登贝格人,在乐队里当副指挥:脾气很好,城府
极深,一向对克利斯朵夫很尊敬的。他对这位同事毫不提防;他怎么会想到把自己的快
乐告诉一个闲人或是敌人有什么不妥呢?他们不是应该反过来感谢他吗?他这是不分敌
友,使大家一起快乐啊。——殊不知天下的难事就莫过于教人家接受一桩新的幸福;他
们几乎更喜欢旧的苦难,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咀嚼了几百年的粮食。
一想到这个幸福是得之于别人的,他们尤其受不了。这简直是一种侮辱,直要无法
避免的时候才肯容忍,而且他们是要设法报复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的心腹话尽管有一千个理由不会受任何人欢迎,但有一千零一个
理由可以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不久就要告老,克利斯朵夫
虽然年纪很轻,可大有继承的希望。奥赫既是纯粹的德国人,当然承认克利斯朵夫有这
个资格,既然宫廷方面这样宠任他。可是奥赫自命不凡,以为倘若宫廷方面多了解他一
点,他自己更有资格当指挥。所以看到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而战意扮看正经面孔跑进戏
院的时候,他就堆起一副异样的笑容,来接受克利斯朵夫倾箱倒骯e的心腹话了。
“哦,〃他狡猾的说,〃又有什么新的杰作吗?”
克利斯朵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回答:“啊!朋友!这一件作品可是登峰造极了
要是你听到的话该死!那太美了!唉,将来能听到这个曲子的,简直是天赐之福!
大家听过以后连死也甘心的了。”
听到这种话的可不是个聋子。奥赫并不一笑置之,也不拿这种幼稚的狂热嘻嘻哈哈
的打趣一番。克利斯朵夫的脾气是倘使有人指出他的可笑,他自己就会先笑的。可是奥
赫假装听得出神,逗克利斯朵夫多说一些傻话;等到一转背,就赶快添枝接叶的把这些
话柄传播出去。大家先在音乐家的小圈子里把他挖苦一阵,然后好不心焦的等机会来批
判那些可怜的作品。——可怜的作品,不曾问世已经被判决了。
作品终于露面了。
克利斯朵夫在乱七八糟的稿子里,选了一阕以赫贝尔的《尤迪特》为题材的《序曲》,
那种粗犷有力的作风,和德国人的萎靡不振对照之下,使他特别觉得可取。(可是他已
经讨厌这作品,认为赫贝尔老是不顾一切的喜欢卖弄天才,多所做作。)其次是一阕交
响曲,借用瑞士画家鲍格林的浮夸的题目,叫做:人生的梦,又加上一句小题辞:人生
是一场短促的梦。还有是一组耿,和几阕古典作品,再加奥赫的一支欢乐进行曲:那是
克利斯朵夫明知平庸但为了表示亲热而放进去的。
几次的预奏会还平静无事。虽然乐队绝对不了解所奏的作品,各人心里对这种古怪
的新音乐非常骇异,但还来不及有什么意见;尤其在群众没有表示的时候,他们决不能
有何主张。看到克利斯朵夫那么自信,他们也就俯首帖耳的接受了。一般音乐师都很能
服从,很有纪律,象一切良好的德国乐队一样。唯一的困难倒是在女歌唱家方面。她就
是上次音乐厅中穿蓝衣服的太太,在德国很有声望,曾经在德累斯顿和拜罗伊特扮演瓦
格纳剧中的主角,肺量的宏大是没有话说的。她虽然学会了瓦格纳派最得意的咬音的艺
术,把辅音唱得高扬,元音唱得沉重象击锤一样,可是就因为这样,她没有懂得自然的
艺术。她对付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办法:所有的音都加强,所有的音节仿佛穿着铅底鞋子
在那里重甸甸的拖,每一句都带着悲剧的气息。克利斯朵夫要求她把戏剧化的成分减少
一些。她先还乐意听从,可是天生笨重的声音和卖弄嗓子的习惯使她无法控制。克利斯
朵夫变得心烦意躁,告诉这位可敬的太太,说他是要叫人类说话,而不是要巨龙法弗奈
吹小号。她听了这种不客气的话当然大不高兴。她回答说①谢谢上帝,她已经知道什么
叫做歌唱,她也很荣幸的唱过勃拉姆斯的歌,就在那位大人物前面,而他也听得津津有
味。“那可糟了!糟了!〃克利斯朵夫喊道。
①法弗奈为《西格弗里德》歌剧中守护尼伯龙根指环的巨龙,以女歌唱家善唱瓦格
纳作品,故以此讽之。
她傲然笑着,要求他把这句谜一样的惊叹语解释明白。他回答说勃拉姆斯一辈子也
没有懂得什么叫做自然,他的称赞简直是最难堪的责备,虽然他克利斯朵夫有时不大有
礼貌,——就象她刚才指摘的,——可也不至于说出对勃拉姆斯那种唐突的话。
两人继续用这种口吻争执下去;那位太太始终依着她慷慨激昂的方式唱,——结果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冷冷的说他看明白了,那是她的天赋如此,没法改的;但既然他的
歌唱不好,还是干脆不唱,从节目中删掉得了。——那时已经到了音乐会的前夜:大家
都知道音乐会中有他的歌,她自己也在外边提过;并且她不无相当的音乐天才,很能赏
识那些歌里面的某些优点;克利斯朵夫临时改变节目等于是侮辱她。而她想到明天的音
乐会也许会奠定青年音乐家的声名,也就不愿意跟这颗将升的明星伤了和气。所以她突
然让步了,在最后一次预奏会中,完全依照了克利斯朵夫的指示。可是她打定主意,在
下一天的音乐会中非用她自己的作风唱不可。
日子到了。克利斯朵夫一点不着急。他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音乐,没法加以批判。
他知道他的作品有些地方要给人笑。可是有什么相干?一个人怕闹笑话,就写不出伟大
的东西。要求深刻,必需有胆子把体统,礼貌,怕羞,和压迫心灵的社会的谎言,统统
丢开。倘若要谁都不吃惊,你只能一辈子替平庸的人搬弄一些他们消受得了的平庸的真
理,你永远踏不进人生。直要能把这些顾虑踩在脚下的时候,一个人才能伟大。克利斯
朵夫居然这样做了。大家很可能嘘他,他有把握不让他们安静的。想到熟人们对曲子里
某些大胆的部分会装出怎样的嘴脸,他暗略觉得好玩。他预备受一番尖刻的批评,先在
肚里好笑了。无论如何,除非是聋子,他作品中的力量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至于这
力能否讨人喜欢是另一问题。并且那有什么关系?时人喜欢!讨人喜欢!只要
有力量就行了。让它象莱茵河一样把什么都卷走吧。
他碰的第一个钉子是大公爵不到场。爵府的包厢里只有几个不相干的人,在府里当
随从的太太们。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想道:“这混蛋跟我怄气,他不知道对我的作品怎样
表示才好:他不来就是怕为难。〃他耸耸肩膀,假装不在乎这些无聊的事。但别人看了很
注意,这是对克利斯朵夫的第一个教训,同时对他的前途也是个威胁。
听众也不比主子殷勤: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酸的想其他童
年音乐会的盛况。要是他稍有经验,一定会懂得演奏上品音乐的时候,听众的数目自然
比不上演奏平凡音乐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感到兴趣的是音乐家而非音乐;而且一个跟
普通人没有分别的音乐家,显然不及一个穿着短裤的儿童音乐家那么好玩,那么动人,
能够教傻瓜们开心。
克利斯朵夫空等了一会儿听众,决意开场了。他硬要自己相信这样倒是更好,以为
〃朋友虽少,都是知己〃。——可怜他这种乐观的心绪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曲又一曲的音乐尽管奏下去,场子里寂静无声。有种寂静无声是因为大家感情冲
动到极点,快要涌出来的缘故。但眼前的寂静简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大家仿佛睡
着了。每一句音乐都掉在漠不关心的深渊里。克利斯朵夫背对着听众,全神对付着乐队,
可是依旧感觉到场子里的情形。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触觉,能够感知他
演奏的东西是否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他照常打着拍子,非常兴奋,可是从池子和包厢
里来的那股沉闷的空气,使他心都凉了。
终于《序曲》奏完了,大家有礼的,冷冰冰的拍了一阵手,就静下来了。克利斯朵
夫宁可受人嘘斥一顿便是怪叫一声也好!至少得有点儿生命的表示,对他的作品表
示一点反响!——可是完全没有。——他瞧瞧群众,群众也彼此瞧瞧。他们互相在
目光中探求一些意见而探求不到,只能又扮起那副漠不关心的脸。
音乐重新开始,轮到那支交响曲了。——克利斯朵夫几乎不能终曲,屡次想丢下指
挥棒,掉过头来就走。他也传染到了大众的麻木,结果竟不懂自己指挥的东西了;他明
明觉得掉入了烦闷的深渊。连他预料在某些段落上群众会交头接耳说的俏皮话也没有,
大家都在一心一意的翻阅节目单。克利斯朵夫听见众人同时哗啦啦的翻纸张的声音;然
后又是一平静默,直到曲子完了,然后又是一阵有礼的掌声表示懂得一曲已经奏完。—
—大家静下来以后还有两三下零星的掌声,因为没有回响,也就不好意思的停住了,空
虚显得更空虚,而这件小小的事故更显得听众是多么厌烦。
克利斯朵夫坐在乐队中间,不敢向左右张望一下。他真想哭出来,同时也气得浑身
哆嗦。他恨不得站起身子向大家喊:“你们多讨厌!多讨厌!一起替我滚罢!”
听众稍为清醒了些,等着女歌唱家出场,那是他们听惯而捧惯的。刚才那些新作品
等于一片大海,他们没有指南针,只能在那里彷徨;她可是稳固的陆地,决没有令人迷
失的危险。克利斯朵夫看出大家的思想,轻蔑的笑了一笑。女歌唱家也知道群众在等她;
克利斯朵夫去通知她上台的时候,她的神气就象王后。他们俩用着敌对的态度彼此望了
一眼。照例克利斯朵夫应当搀着她手臂,但他竟双手插在袋里,让她自个儿出台。她气
冲冲的走过去;他很不高兴的跟在后面。她一漏脸,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大家松了口气,
脸上发出光来,有了精神;所有的手眼镜都一起瞄准。她对自己的魔力很有把握,开始
唱起歌来,不消说是照她自己的方式,全不遵从克利斯朵夫上一天的嘱咐。替她伴奏的
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这种捣乱他是预先料到的。一发觉她走腔,他立刻敲着钢琴,愤
怒的说了声:
“不是这样的!”
可是她不理。他就在背后用着又重浊又生气的声音提醒她:
“不!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这些气愤愤的咕噜,虽然台下听不见,对乐队里的人可是句句分明;她一急,拚命
把节奏拉慢,不该休止的地方也休止。他没有留意,自顾自的弹下去,终于歌和伴奏相
差了一节。听众一点没觉得:他们久已认定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既不会悦耳,拍子也不会
准的;但克利斯朵夫并不这样想,他象疯子似的,脸都扭做一团,终于爆发了。他突然
半中间停下来,直着嗓子嚷道:“得了罢!”
她一口气收不住,继续唱了半节,然后也停住了。“得了罢!〃他粗暴的又说了一遍。
全场为之愣了一愣。过了一忽儿,他又冷冷的说:“咱们再来!”
她愕然望着他,双手哆嗦着,真想把乐器望他头上扔过去;事后她竟不懂当时怎么
没有那样做。但她慑于克利斯朵夫的威严,只得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