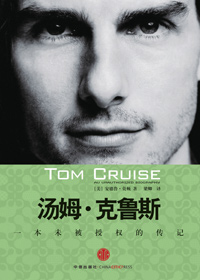约翰·克利斯朵夫-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向大公爵吐吐舌头,或是望什么太太的屁股上踢一脚。有一回他挣扎了一个晚上,因为
他一边指挥乐队,一边竟想当众脱衣服;而他越是压制这念头,越是被这个念头纠缠不
清,直要使尽全身之力才能撑过去。在这种荒唐的斗争之后,他一身大汗,觉得脑子里
空空如也。他真是疯了。只要他想到不该做某一件事,某一件事就象偏执狂一样顽强的
把他死抓不放。
于是他的生活不是被那些疯狂的力播弄,就是堕入虚无的境界。一切象是沙漠上的
狂风。哪儿来的这阵风呢?这种疯狂又是怎么回事呢?扭他的四肢,扭他的头脑的欲望,
从哪个窟窿里冒出来的呢?他仿佛是一张弓,被一只暴烈的手快拉断了,——不知为了
什么目的,——过后又被扔在一边,象无用的枯枝似的。他不敢深究自己做了谁的俘虏,
只觉得被打败了,非常屈辱,又不敢正视自己的失败。他困倦不堪,一点儿志气都没有
了。那些不愿意看到难堪的真相的人,从前他是瞧不起的,现在他了解了。在这些虚无
的时间,一想到浪费的光阴,丢掉的工作,白白断送了的前途,他吓得浑身冰冷。但他
并不振作品来,只无可奈何的承认虚无的力量,而宽恕自己的懦弱无能。他觉得委身于
虚无倒有种悲苦的快感,好比一条在水面上快要沉下去的船。挣扎有什么用?一切都是
空的:美,善,上帝,生命,无论什么生物,都是空的。在街上走的时候,忽然他双脚
离地了,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空气,也没有光明,也没有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他头重
脚轻,脑门向前探着;他能够撑着不跌下去也是间不容发的事了。他想他要突然倒下去
了,被雷劈了。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克利斯朵夫正在脱胎换骨,正在换一颗灵魂。他只看见童年时代那颗衰败憔悴的灵
魂掉下来,可想不到正在蜕化出一颗新的,更年轻而更强壮的灵魂。一个人在人生中更
换躯壳的时候,同时也换了一颗心;而这种蜕变并非老是一天一天的,慢慢儿来的:往
往在几小时的剧变中,一切都一下子更新了,老的躯壳脱下来了。在那些苦闷的时间,
一个人自以为一切都完了,殊不知一切还都要开始呢。一个生命死了。另外一个已经诞
生了。
一天晚上,他独自在卧室里,背对着窗,在烛光底下,把胳膊靠在桌上。他并不工
作。几星期以来,他不能工作了。一切在他头里打转。宗教,道德,艺术,整个的人生,
一古脑儿都同时成了问题。思想既然是总崩溃了,就谈不到什么条理跟方法;他只在祖
父留下的或是伏奇尔的杂书中胡乱抓几本看看:神学书,科学书,哲学书,大都是些零
本;他完全看不懂,因为每样都得从头学起;而且他从来不能看完一本,翻翻这个,看
看那个,把自己搅糊涂了,结果是疲倦不堪,颓丧到了极点。
那天晚上,他正沉浸在困人的麻痹状态中发呆。全屋子的人都睡了。窗子开着,院
子里一丝风也没吹过来。天上堆满了密云。克利斯朵夫象傻子似的,望着蜡烛慢慢的烧
到烛台底里。他不能睡觉,什么也不想,只觉得那空虚越来越深,在那儿吸引他。他拚
命不要看那个窟窿,却偏偏不由自主的要凑上去。在窟窿里骚然蠢动的是混乱,是黑暗。
一阵苦闷直透入内心,背脊里打了个寒噤,他毛骨悚然,抓住桌子怕跌下去。他颤危危
的等着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等着一桩奇迹,等着一个上帝
忽然之间,在他背后,院子里好似开了水闸一样,一场倾盆大雨浩浩荡荡直倒下来。
静止不动的空气打着哆嗦。雨点打在干燥坚硬的泥土上,好比钟声一般锋铮作响。象野
兽那样暖烘烘的土地上,在狂乱与快乐的抽搐中冒起一大股泥土味,一股花香,果子香,
动了爱情的肉香。克利斯朵夫神魂颠倒,全身紧张,连五脏六腑都颤抖了幕揭开了。
简直是目眩神迷。在闪烁的电光中,在黑暗的最深处,他看到了——看到了上帝,看到
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就在他心中:它透过卧室的屋顶,透过四面的墙壁,把生命的界限
推倒了;它充塞于天地之间,宇宙之间,虚无之间。世界象飞扑似的冲入它的怀抱。对
着这个天翻地覆的景象,克利斯朵夫吓呆了,出神了;旋风把自然界的规则扫荡完了,
克利斯朵夫也被吹倒了,带走了。他失掉了呼吸,倒在了上帝身上,他醉了深不可
测的上帝!那是生命的火把,生命的飓风,求生的疯狂,——没有目的,没有节制,没
有理由,只为了轰轰烈烈的生活!
精神上的剧变过去以后,他沉沉睡着了,那是久已没有的酣睡。第二天醒来,他头
脑昏沉,四肢无力,象喝过了酒。昨夜使他惊骇万状的,那道阴森而强烈的光,在他心
中还剩下一些余辉。他想要那道光再亮起来,可是办不到。而且他愈追求愈找不着。从
此,他集中精力要求那个一刹那间的幻象再现一回,结果是劳而无功。出神的境界决不
让意志作主的。
然而这种神秘的狂乱状态,并非只此一遭,以后又发生了好几次,但从来不象第一
回那么剧烈。来的时候总是克利斯朵夫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短短的几秒钟,完全是出岂
不意的,甚至抬一抬眼睛,举一举手的时间,幻象已经过去了,他连想也来不及想到这
是幻象,事后还疑心是作梦。第一晚是一块烈焰飞腾的陨石在黑暗中燃烧,以后的只是
一簇毫光,几小点稍纵即逝的微光,肉眼只能瞥见一下就完了。但它们出现的次数愈来
愈多,终于把克利斯朵夫包围在一个连续而模糊的梦境中,使他的精神都溶解在里头。
凡是足以驱散这种朦胧的意境的,他都恼恨。他没法工作,甚至也想不到工作。有人在
旁边他就恨,尤其是亲近的人,连母亲在内,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权控制他的精神。
他跑出去,常常在外边消磨日子,到夜晚才回家。他寻求田野里的清静,为的能称
心如意的,象狂人一般,把自己整个儿交给那些执着的念头。——但在荡涤尘怀的空旷
中,和大地接触之下,那种纠缠变得松懈了,那些念头也没有幽灵一般的性质了。他的
热狂并没减少一点,倒反加强,但已经不是危险的精神错乱,而是整个生命的健全的醉
意:肉体和灵魂都为了自己的力而得意。
他重新发见了世界,仿佛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童年以后的另外一个童年。似乎一
切都被一句奇妙的咒语点化了。自然界放出轻快的火花。太阳在沸腾。天色一清如水,
象河一般流着。大地咕噜作响,吐出沉醉的气息。生命的大火在空中旋转飞腾:草木,
昆虫,无数的生物,都是闪闪发光的火舌。一切都在欢呼呐喊。
而这欢乐便是他的欢乐,这股力便是他的力。他和万物分不开了。至此为止,便是
在童年时代快乐的日子,怀着热烈而欣喜的好奇心看着大自然的时候,他也觉得所有的
生物都只是些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或是可怕的,或是滑稽的,跟他毫无关系,他也无从
了解。连它们是否有感觉有生命,他也不大清楚,只认为是古怪的机器而已。凭着儿童
无意识的残忍心理,克利斯朵夫曾经把一些可怜的昆虫扯得四分五裂,看着它们古古怪
怪的扭动觉得好玩,根本没想到它们的受苦。平时那么镇静的高脱弗烈特舅舅看到他折
磨一只苍蝇,禁不住愤愤的把它从手里抢下来。孩子先还想笑,后来也给舅舅的神气感
动得哭了。那时他才明白他的俘虏也有生命,和他一样,而他是犯了凶杀的罪。从此以
后,他虽然不再伤害动物,可也并不对它们有什么同情;在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从来没
想到去体会一下,那些小小的躯壳里头有些什么在骚动;他倒是把它当做恶梦一般的怕
想到。——可是现在一切都显得明白了。那些暧昧的生物也放出光明来了。
克利斯朵夫躺在万物滋长的草上,在昆虫嗡嗡作响的树荫底下,看着忙忙碌碌的蚂
蚁,走路象跳舞般的长脚蜘蛛,望斜刺里蹦跳的蚁蜢,笨重而匆忙的甲虫,还有光滑的,
粉红色的,印着白斑,身体柔软的虫。或者他把手枕着头,闭着眼睛,听那个看不见的
乐队合奏:一道阳光底下,一群飞虫绕着清香的柏树发狂似的打转,嗡嗡的苍蝇奏着军
乐,黄蜂的声音象大风琴,大队的野蜜蜂好比在树林上面飘过的钟声,摇曳的树在那里
窃窃私语,迎风招展的枝条在低声哀叹,水浪般的青草互相轻拂,有如微风在明净的湖
上吹起一层绉纹,又象爱人悉悉索索的脚声走过了,去远了。
这些声音,这些呼喊,他都在自己心里听到。这些生物,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内部
都流着同一条生命的巨川:克利斯朵夫也受着它的浸润。他和千千万万的生灵原是同一
血统,它们的欢乐在他心中也有友好的回声;它们的力和他的力交融在一起,象一条河
被无数的小溪扩大了。他就浸在它们里面。强烈的空气冲进他窒息的心房,胸部几乎要
爆裂了。而这个变化是突如其来的:正当他只注意自己的生命,觉得它象雨水般完全溶
解而到处只见到虚无之后,一旦他想在宇宙中忘掉自己,就到处体会到无穷无极的生命
了。他仿佛从坟墓中走了出来。生命的巨潮汜滥洋溢的流着,他不胜喜悦的在其中游泳,
让巨流把他带走,以为自己完全自由了。殊不知他更不自由了。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是
自由的,连控制宇宙的法则也不是自由的,——也许唯有死才能解放一切。
可是刚在旧的躯壳中蜕化出来的蛹,只知道在新的躯壳中痛痛快快的欠伸舒展;它
还来不及认识新的牢笼的界限。
日月循环,从此又开始了新的一周。光明灿烂的日子,如醉如狂的日子,那么神秘,
那么奇妙,象童年时代初次把一件件的东西发现出来一样。从黎明到黄昏,他老是过的
空中楼阁的生活。正事都抛弃了。认真的孩子,多少年来便是害病也没缺过一课,在乐
队的预奏会中也没缺席一次,此刻竟会找出种种借口来躲避工作。他不怕扯谎,也不觉
得惭愧。过去他喜欢用来压制自己的刻苦精神:道德,责任,如今都显得空洞了。它们
那种专制的淫威,一碰到人类的天性就给砸得粉碎,唯有健全的,强壮的,自由的天性,
才是独一无二的德性,其余的都是废话!那些繁缛琐碎,谨慎小心的规则,一般人称之
为道德而以为能拘囚生命的:真是太可怜了!这样的东西也配称为牢笼吗?在生命的威
力之下,什么都给推倒了
精力过于充沛的克利斯朵夫,发疯似的想用盲目的暴烈的行为,把那股使他窒息的
力毁掉,烧掉,让它发泄。这种兴奋的结果往往是突然之间的松弛;他哭着,趴在地下,
亲着泥土,恨不得把牙齿和手陷进去,把泥土吞下肚子;烦闷与情欲使他浑身发抖。
一天傍晚,他在一个树林旁边散步。眼睛被日光照得有些醉意,头里昏昏沉沉的在
打转,他精神非常兴奋,看出来的东西都是另外一副面目。柔和的暮色使万物更添了一
种神幻的情调。紫红与金黄的阳光在栗树底下浮动。草原上好象放出一些磷火似的微光。
天色象人的眼睛一样温和可爱。近边的草场上有个少女在割草。穿着衬衣和短裙,露着
脖子跟手臂,她扒起干草,堆在一处。她长着个短鼻子,大脸盘,天庭饱满,头上裹着
一块手帕;焦黑的皮肤给太阳晒得通红,仿佛在尽量吸收傍晚的日光。
克利斯朵夫对她动了心。他靠在一株榉树上看着她向林边走来。她并没留神,只是
无意之间抬了抬头:他看见她黑不溜秋的脸上配着一对蓝眼睛。她走得那么近,甚至弯
下身子捡草的时候,他从她半开的衬衣里看见了脖子跟背上那些淡黄的毛。郁积在他胸
中的暧昧的欲望突然爆发了。他从后面起上去,搂住了她的脖子和腰,把她的头望后扳
着,拿嘴用力压在她半开的嘴里,吻着她那又干又裂的嘴唇,碰到了她把他怒咬的牙齿。
他的手在她粗糙的胳膊和汗湿的衬衣上乱摸。她挣扎着,他可把她抱得更紧,差不多想
掐死她。终于她挣脱了,大叫大嚷,吐着口水,用手抹着嘴唇,没头没脑的骂他。他一
松手就往田里逃了。她在背后扔着石子,不住的用许多脏字称呼他。他脸红耳赤,倒不
是因为被她当做或说做是怎么样的人,而是为了他对自己的感想。这个突如其来的无意
识的行动,使他惊骇万状。他刚才做的什么事呢?准备做些什么呢?他所能想象到的只
能引起心中的厌恶。而他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