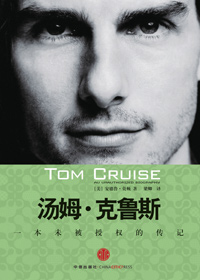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若无起事的走了出来。可是一关上门,她的傲气完全没有了,不由得躲在走廊的拐角儿
上偷听,——(她的确是屈辱到了极点之才会出此下策),——只听见很短促的笑了一
声,接着又是一阵唧唧哝哝,轻得简直听不见。但她当时吓昏了,自以为听到了她怕听
的话,似乎他们谈的是下次狂欢节中的化装会和喧扰。没有问题,他们想把铺灰的故事
穿插进去可能是她听错了;但她神经过敏到病态的程度,半个月来又老想着被公众
羞辱的念头,所以她非但把不确定的事当做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了。
从此她就打定了主意。
当天晚上,——(就是狂欢节以前的星期三),——勃罗姆被请到离城二十里左右
的地方去出诊,要第二天早上才能回来。阿娜关在屋里,不下来吃饭。她预备就在这晚
上实行她的计划。但她决意自个儿实行,不告诉克利斯朵夫。她瞧不其他,心里想:
“他虽然答应也不相干。男人总是自私的,只会扯谎。他有他的艺术,很快会把我
忘了的。”
并且这个好象毫无恻隐之心而生性暴戾的女人,或许对她的同伴还有点儿怜悯。但
她太强悍了,自己还不愿意承认有这点同情。
巴比告诉克利斯朵夫,说太太要她代为道歉,因为不大舒服,想早些休息。克利斯
朵夫只能在巴比监视之下独自吃晚饭;她絮絮叨叨的在旁嚼舌,逗他开口,并且一而再,
再而三的替阿娜说客气话,终于连那么轻信的克利斯朵夫也起了疑心。他正想利用这一
晚跟阿娜彻底谈一谈。他也拖不下去了。当天黎明时分约定的话,他并没忘掉。如果阿
娜要求,他是准备履行诺言的。同时他也明白两个人这样的自杀未免太荒唐,什么事都
解决不了,只有把痛苦和丑事压在勃罗姆身上,最好还是彼此分手,自己一走了事,—
—只消他有勇气离开她;但这一点便大有问题,他最近不是走了又回来的吗?可是他又
想,等到离开她以后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再一个人自杀也不为迟。
他希望吃过晚饭能溜进阿娜的卧房。但巴比老跟在他背后。往常她的工作很早就完
的;这一晚她扑在厨房里洗刷不完;赶到克利斯朵夫以为终于得到释放的时候,她又想
出主意在通到阿娜卧房的甬道中整理一口壁橱。克利斯朵夫看到她一本正经的坐在一只
高凳上,才知道她整个晚上不会走开了。他气愤之极,恨不得把她跟那些一堆又一堆的
盘子碟子一起摔下楼去;但他捺着性子,教她去问问女主人怎么样,他能不能去看她一
下。巴比去了,回来用一种狡狯的,高兴的神气瞧着他,说太太好了一些,想睡一会,
希望别打搅她。克利斯朵夫又恼又烦躁,想看书又看不下去,便回到自己屋里去了。巴
比直等他熄了灯才上楼,还预备在暗中监视,特意把房门半开着,以便听到屋子里的声
音。不幸她没法熬夜,一上床就睡熟了,而且一觉睡到天亮,哪怕天上打雷,哪怕存着
极大的好奇心,也不会醒的。这一点对谁都瞒不了,她的打鼾声隔了一层楼也听得见。
克利斯朵夫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便到阿娜房里去了。他心里非常不安,需要和她
谈话,他走到门口,旋着门钮,不料门拴上了,便轻轻敲了一会:没有回音。他拿嘴巴
贴在锁孔上,先是低声的,继而是迫切的哀求毫无动静,毫无声息。他以为阿娜睡
着了,但觉得自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因为竭力要听屋子里的声音,他把脸紧贴在门上:
一股好似从门内透出来的气味使他吃了一惊,便低下身子,仔细辨了辨,原来是煤气。
他登时浑身冰冷,拚命的推房门,也顾不得会不会惊醒巴比了;可是房门动都不动
他想出来了:跟阿娜的卧室相连的盥洗室内有一个小煤气灶,一定是被她把龙头旋开了。
非砸开房门不可。克利斯朵夫虽然慌乱,头脑还清楚,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让巴比听见。
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在门上,悄悄的使劲一顶。那扇坚固而关得很严的门只格格的响了一
下,还是不动。阿娜的卧室和勃罗姆的书房中间另外有扇门相通。他便绕进书房,不料
那扇门也关上了。这儿的锁是在外边的,他想把它拉下来,可是不容易。他先得撬去木
头里的四只大螺丝钉,但身边只有一把小刀,黑洞里什么都看不见,又不敢点火,怕把
煤气引着了,连屋子都炸掉。他摸索了半日,终于把刀尖旋进一只螺丝,接着又旋进了
另外一只,刀尖断了,手也弄破了;那些螺丝钉又是异样的长,怎么也旋不出来。浑身
淌着冷汗,又焦急又狂乱,他脑子里忽然浮起一幅童年往事:似乎看到自己十岁的时候
被关在黑房里,撬去了锁逃出屋子的情形终于最后一只螺丝退下了,锁也拿下来了,
掉下许多木屑。克利斯朵夫冲进房间,打开窗子,立刻吹进一阵冷风。克利斯朵夫撞着
家具,在黑暗中找到了床,摸索着,碰到了阿娜的身子,颤危危的手隔着被单摸到一动
不动的腿,直摸到她的腰:原来阿娜坐在床上发抖。煤气还没有发生作用:屋子的天顶
很高,窗户都不大紧密,到处有空气流通。克利斯朵夫把她搂在怀里。她却气愤愤的挣
扎着,嚷道:“去你的罢!你来干什?”
她把他乱打一阵,可是感情太激动了,终于倒在枕上,大哭着说:“哎哟!哎哟!
得重新再来的了!”
克利斯朵夫抓着她的手,拥抱她,埋怨她,和她说些温柔而又严厉的话:“你死!
你自个儿死!不跟我一块儿死!”
“哼!你!”她这话是表示一肚子的怨恨,意思之间是说:“你,你是要活的。”
他责备她,想用威吓的方法改变她的主意:“疯子!你不要把屋子炸掉吗?”
“我就是要这样,”她气哼哼的嚷着。
他挑动她宗教方面的恐惧,这一下果然中了她的要害。他才提了两句,她就嚷着要
他住嘴。他却不顾一切的说下去,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唤醒她求生的意志。她不出声了,
只抽抽搭搭的打呃。他说完了,她恨恨的回答:“现在你快活了罢?你做得好事!把我
收拾完了,教我怎么办?”
“活下去啊,”他说。
“活下去!你不知道不可能吗?你一点儿都不知道,一点儿都不知道!”
“什么事呢?”他问。
她耸了耸肩膀:“你听着。”
于是她用简短的断续的句子,把她一向瞒着的事统统说了出来:巴比的刺探,铺灰
的经过,萨米的事,狂欢节,无可避免的羞辱等等。她说的时候也分不出哪些恐惧是有
根据的,哪些是没有根据的。他听着,狼狈不堪,比她更分不出真正的危险与假想的危
险。他万万想不到人家暗地里钉着他们。他想了解这个情形,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对付
这一类的敌人是没办法的,他只是没头没脑的气疯了,唯一的念头是想打人。
“干吗你不把巴比打发走呢?”他问。
她不屑回答。把巴比赶出去当然比让巴比待在这儿更危险;克利斯朵夫也懂得自己
问得无聊。许多思想在他脑子里冲突;他想打定一个主意,立刻有所行动。他握着抽搐
的拳头说:“我要去杀他们。”
“杀谁?”她觉得这些废话不值一笑。
他勇气没有了。周围埋伏着奸细,可是一个也抓不到,每个人都是奸党。
“卑鄙的东西!”他垂头丧气的说了一句。
他倒在地下,跪在床前,把脸紧贴着阿娜的身子。——两人一声不出。她对于这个
既不能保卫她又不能保卫自己的男人,觉得又可鄙又可怜。他的脸感觉到阿娜的大腿在
那里冷得发抖。窗子开着,外面气温很低;明净如镜的天空,星都打着哆嗦。
她看见他跟自己一样的失魂落魄,心里痛快了些;然后声音很凶但又很困倦的吩咐:
“去点一支蜡烛来!”
他点了火。阿娜牙齿格格的响着,拳着身子,抱着手臂放在胸口,下巴放在膝盖上。
他关了窗,坐在床上,抓着阿娜冰冷的脚,用手跟嘴巴焐着。她看了不由得感动了。
“克利斯朵夫!”她叫了一声,眼神气惨到极点。
“阿娜!”
“咱们怎么办呢?”
他瞅着她回答:“死罢。”
她快活得叫起来:“噢!真的吗?你也愿意死吗?那末我不孤独了!”说完,
她把他拥抱了。
“你以为我会丢掉你吗?”
“是的,”她低声回答。
他听了这句话,才体会到她痛苦到什么地步。
过了一忽,他用眼睛向她打着问号,她明白了,回答说:“在书桌的抽屉里。靠右
手,最下面的一个。”
他便去找了。抽屉的尽里头果然有把手枪,那是勃罗姆在大学念书的时代买的,从
来没用过。克利斯朵夫又在一只破匣子内找到几颗子弹,一古脑儿拿到床前。阿娜望了
一眼,立刻掉过头去。克利斯朵夫等了一会,问道:“你不愿意了吗?”
阿娜猛的回过身来:“怎么不愿意!快点儿!”
她心里想:“现在我得永远掉在窟窿里了。早一些也罢,晚一些也罢,反正是这么
回事!”
克利斯朵夫笨手笨脚的装好了子弹。
“阿娜,”他声音发抖了,“咱们之中必有一个要看到另外一个先死。”
她一手把枪夺了过去,自私的说:“让我先来。”
他们俩还在互相瞧着可怜!便是快要一块儿死的时候,他们觉得彼此还是离得
很远!各人都骇然想着:“我这是干的什么呢?什么呢?”
而各人都在对方眼中看出这个念头。这件行为的荒唐,在克利斯朵夫尤其感觉得清
楚。他整个的一生都白费了;过去的奋斗,白费了;所有的痛苦,白费了;所有的希望,
白费了;一切都随风而去,糟掉了;一举手之间,什么都给抹得干干净净要是在正
常状态中,他一定会从阿娜手中夺下手枪,望窗外一扔,喊道:“不!我不愿意。”
可是八个月的痛苦,怀疑,令人心碎的丧事,再加这场狂乱的情欲,把他的力量消
耗了,把他的意志斵丧了,他觉得一无办法,身不由主唉!归根结蒂,有什么关系?
阿娜相信这样的死就是灵魂永远不会得救的死,便拚命的想抓住这最后一刹那:看
着摇曳不定的灯光照着克利斯朵夫痛苦的脸,看着墙上的影子,听着街上的脚声,感到
手里有一样钢铁的东西她抓住这些感觉,仿佛一个快淹死的人抱着跟他一起沉下去
的破船。以后的一切都是恐怖。为什么不多等一下呢?可是她反复说着:“非如此不
可”
她和克利斯朵夫告别了,没有什么温情的表示,匆匆忙忙的,象一个怕错失火车的
旅客;她解开衬衣,摸着心,拿枪口抵在上面。跪在床前的克利斯朵夫把头钻在被单里。
正要开放的时候,她左手放在克利斯朵夫的手上,好比一个怕在黑夜中走路的孩子
那几秒钟功夫真是可怕极了阿娜没有开枪。克利斯朵夫想抬起头来抓住阿娜的
手臂,但又怕这个动作反而使阿娜决意开放。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失去了知觉直听
到一声哼唧,他方始仰起头来,看见阿娜脸色变了,把手枪扔在床上,在他面前,她哀
号着说:“克利斯朵夫!子弹放不出呀!”
他拿起手枪看了看,原来生了锈,机关还是好的;也许是子弹不中用了。——阿娜
又伸出手来拿枪。
“算了罢!”他哀求她。
“把子弹给我!”她带着命令的口吻。
他递给了她。她仔细瞧了瞧,挑了一颗,浑身哆嗦的上了膛,重新把火器抵住胸部,
扳着机钮。——还是放不出。
阿娜一撒手把手枪扔了,嚷着:“啊!我受不了!受不了!他竟不许我死!”
她在被单中打滚,象疯子一般。他想走近去,她又叫又嚷的把他推开了,终于大发
神经。克利斯朵夫直陪她到天亮。最后她安静下来,差不多没有气了,闭着眼睛,惨白
的皮肤底下只看见脑门的骨头和颧骨:她象死了一样。
克利斯朵夫把乱七八糟的床重新铺好,捡起手枪,拆下的锁也装还原处,把屋子都
整理妥当,走了;时间已经七点,巴比快来了。
勃罗姆早上回家的时候,阿娜还是在虚脱状态。他明明看到发生了一些非常的事,
但既不能从巴比那儿,也不能从克利斯朵夫那儿知道。阿娜整天的不动,眼睛闭着,脉
搏微弱到极点,有时竟完全停止;勃罗姆好不悲痛的以为她的心已经不会跳了。慌乱之
下,他对自己的医道起了怀疑,便找了一个同道来。两人会诊的结果,决不定这是发高
热的开始呢,还是一种忧郁性的神经病:还得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