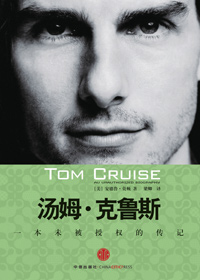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9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让医生听诊,——(她宁死也不愿意在一个男人面前脱掉衣服);——只是说了实话。
医生把她大大的埋怨了一顿,她才答应不再来了。而祖母为了保险,也从此检查她的衣
著。阿娜并没在这些苦行中得到什么神秘的快感;她没有想象力,凡是圣?法朗梭阿或
圣女丹兰士所有的诗意,对她都谈不到。她的苦修是悲观的,唯物的,折磨自己并非为
了求他世界的幸福,而是由于苦闷的煎熬,求一种自虐狂的快感。出人意外的是,这颗
象祖母一样冷酷的心居然能领会音乐,至于领会到什么程度,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对
别的艺术都木然无动于衷,也许从来没对一幅画瞧过一眼,简直没有造型美的感觉,因
为她骄傲,冷淡,所以一点不感兴趣。一个美丽的肉体,在她心中只能引起裸体的观念,
就是说象托尔斯泰所讲的乡下人那样,只能有种厌恶的情绪;而这种厌恶在阿娜心中尤
其强烈,因为她跟一般她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暗中只有欲念的冲动,而很少心平气
和的审美的批判。她从来不想到自己长得好看,正如从来不想到被压制的本能有多少力
量;其实是她不愿意知道,而且因为对自己扯谎成了习惯,结果也认识不清了。
勃罗姆和她是在人家的婚筵上遇到的。那次她去吃喜酒是例外;大家一向认为她出
身下贱而不敢请她。她那时二十二岁。勃罗姆对她留了心;可并非因为她有什么惹人注
意的举动。她在席上坐在他旁边,姿态强直,衣服穿得很难看,简直不开口。但勃罗姆
一刻不停的和她谈着,——就是说他自个儿说着话,——回去不禁大为动情。他凭着肤
浅的观察,觉得那邻座的姑娘幽雅贞静,通情达理;同时他也赏识那个健康的身体和一
望而知善操家政的长处。他去拜访了祖母,第二次又去,就提了婚,祖母同意了。陪嫁
是一个钱都没有的:桑弗老太太把家产捐给公家发展商业去了。
这年轻的女人对丈夫从来不曾有过爱情,认为那是良家妇女应当看作罪恶一样回避
的。但她知道勃罗姆的好心是了不起的,也感激他不顾她的出身暧昧而跟她结婚。她对
于妇道看得很重,结婚七年,夫妇之间不曾有过风波。他们守在一块儿,既不了解,也
不因此而有什么不安。在大众眼里,他们正是一对模范夫妻。两人难得出门。勃罗姆的
病家相当多,但没法使妻子踏进那个社会。她不讨人喜欢,出身的污点还不能完全抹掉。
阿娜自己也不想法去亲近人家。对于从小受到的轻蔑,使她的童年悒郁不欢的原因,她
至今心里很气愤。并且她在人前觉得很局促,也愿意人家把她忘掉。为了丈夫的事业,
她不得不拜访和接待一些无可避免的客人。那般女客都是些好奇的,喜欢说坏话的小布
尔乔亚。她们飞短流长的议论,阿娜完全不感兴趣,也不隐藏这种心理。而这一点就是
不可原谅的。因此宾客的访问渐渐的稀少了,阿娜孤独了。而她正是求之不得,只希望
什么都不来打扰她心里翻来覆去的梦境,和她身上那种暧昧的骚动。
几星期来,阿娜似乎闹着病,脸瘦下去了。她躲着不跟克利斯朵夫与勃罗姆见面,
成天关在卧房里胡思乱想;人家和她说话,她也不回答。勃罗姆照例不会因女人这种任
性的行为着慌的,他还对克利斯朵夫解释呢。好似一切生来看不透女人的男子一样,他
自命为了解她们。他的确相当了解,可是毫无用处。他知道她们往往很固执的做着梦,
心里存着敌意,一味的不开口;那时最好听其自然,别去追究,尤其别追究她们在那个
危险的潜意识领域里做些什么。虽然如此,他也开始为阿娜的健康操心了,以为她的形
容憔悴是由于她的生活方式,由于老关在家里,从来不出城,也难得出大门的缘故。他
要她去散散步。他自己不大能陪她:星期日她忙着敬神礼拜的功课;平日他忙着看诊。
至于克利斯朵夫,又特意避免跟她一同出去。有过一二次,他们一块到城门口作短距离
的散步:那简直烦闷得要死。话是没有的。对于阿娜,自然界仿佛是不存在的,她一无
所见;田野在她眼里不过是草木和石头,那种冥顽不灵的态度使人心都凉了。克利斯朵
夫曾经教她欣赏一角美丽的风景。她望了望,冷冷的笑了一下,勉强敷衍他说:
“噢!是的,那很神秘”
她也会用着同样的态度说:“嗯,太阳好得很。”
克利斯朵夫气得把手指掐着自己的手掌,从此再也不问她什么;她出去的时候,他
总借端留在家里。
其实阿娜对于自然界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不喜欢人家所谓美丽的风景,不觉得那
和其余的景色有什么分别。但她喜欢田野,——不管是哪一种,——喜欢土地跟空气。
不过她对于这种爱好,象对于别的强烈的感情一样,自己并不感觉到;而和她共同生活
的人自然更不容易觉察。
勃罗姆一再劝说的结果,阿娜终于答应到近郊去玩一天。这是她为了免得人家纠缠
不清而让步的。散步定在一个星期日。到最后一刹那,为这件事喜欢得象小孩子一样的
医生,竟为了一个急症不能分身,只能由克利斯朵夫陪着阿娜出发。
虽是冬天,气候却非常好,也没有下雪:空气清冽寒冷,天色开朗,太阳明晃晃的,
吹着一阵砭骨的北风。他们搭着区间小火车,望远山如带的地方驶去。车厢里挤满了人;
他们俩分开坐着,一句话也不说。阿娜脸色很不高兴;上一天她出乎勃罗姆意料之外的
说这个星期日不去做礼拜了。这是她生气第一次缺席。是不是反抗的表示呢?她内
心的斗争,谁说得出呢?——当时她脸色惨白,直瞪着面前的凳子
他们下了火车,开始散步的时候,彼此都很冷淡。两人并肩走着;她步子很坚决,
对什么都不注意,两条胳膊甩来甩去,鞋跟在冰冻的地上橐橐的响着。——慢慢的,她
脸色活泼起来,走路的速度使苍白的腮帮有了血色。她把嘴巴张开了一点呼吸空气。在
一条弯弯曲曲向上的小路的拐角儿上,她从斜刺里沿着一个石坑,爬上山岗,象一头羊,
遇到要颠簸的时候便用手抓着身旁的灌木。克利斯朵夫跟着她。她越爬越快,滑跌了,
又抓着草爬起来。克利斯朵夫嚷着要她停下。她不回答,尽管弯着身子,手脚并用的往
上跑。浓雾象银色的绞绡般起浮在山谷上空,遇有树木的地方才露出一道裂缝。两人穿
过雾,到了高处的阳光里。到了顶上,她回过身来,神色开朗,张着嘴喘气,带着嘲弄
的表情瞧着克利斯朵夫在后面爬上来,脱下大衣扔在他脸上,然后不等他喘过气来又向
前奔了。克利斯朵夫在后面追着。他们都动了游戏的兴致;清新的空气使他们迷迷忽忽
的好象醉了。她拣一个陡峭的山坡奔下去,石子在脚下乱滚,可并不跌交,溜来滑去,
连蹿带跳,象一支箭一般飞去。她不时回顾一下,估量她跑在克利斯朵夫前面有多远。
他越追越近,她便溜入树林。枯叶在脚下簌簌的响着;撩开去的树枝又回过来拂着她的
脸。最后她蹴在一个树根上,被克利斯朵夫抓住了。她挣扎着,拳打足踢的抗拒,狠狠
的打了他几下,想要把他摔下地,又是叫又是笑。她紧贴在他身上,胸部起伏不已;两
人的腮帮差不多碰着了,他沾到了阿娜额上的汗珠,呼吸到她头发上潮湿的气味。突然
她使劲一推,挣脱了身子,用着挑战的眼睛瞅着他,没有一点骚动的表情。他发觉她有
一股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使出来的力量,不由得大为惊奇。
他们向邻近的村庄出发,很轻快的在富有弹性的干草堆里穿过去。前面有群觅食的
乌鸦在田野中飞。太阳很旺,寒风砭骨。克利斯朵夫搀着阿娜的胳膊。她穿的衣服不十
分厚,他能感觉到她身体上蒸发出来的暖气与汗湿。他要她把大衣穿上,她不肯,并且
为了表示勇敢,把领扣也松了。他们到一家乡村客店去吃饭:招牌上画着个“野人”的
商标,门前种着一株小柏树,饭厅壁上装饰着德文的四节诗和两幅五彩印版画:一幅带
着感伤意味的,叫做《春》;一幅带着爱国意味的,叫做《圣?雅各之战》;另外还有
一个十字架,下端刻着一个骷髅。阿娜狼吞虎咽的胃口,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见过。他们
兴致很好,喝了一点儿白酒。饭后,他们象两个好伙计似的,又到田里玩儿去了,心里
很安静,只想着走路的乐趣,想着在他们胸中激动的热血和刺激他们的空气。阿娜舌头
松动了,不再存心提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她讲着童年的事:祖母带她到一个靠近大教堂的老太太家里;两个老人谈天的时候,
打发她到大花园里去玩。教堂的阴影罩着园子,她坐在一角,一动不动,听着树叶的哀
吟,探着虫蚁的动静:又快活又害怕。——她可没说出在她想象中盘旋不去的念头,—
—对魔鬼的恐惧。人家说那些魔鬼老在教堂门前徘徊,不敢进去;她以为蜘蛛,蜥蜴,
蚂蚁,所有在树叶下,地面上,或是在墙壁的隙缝里蠢动的丑恶的小东西,全是妖魔的
化身。——随后她谈到当年的屋子,没有阳光的卧室,津津有味的回想着;她在那儿整
夜的不睡觉,编着故事
“什么故事呢?”
“想入非非的故事。”
“讲给我听罢。”
她摇摇头,表示不愿意。
“为什么?”
她红着脸,笑着补充:“还有白天,在我工作的时候。”
她想了一下,又笑起来,下了个结论:“都是些疯疯癫癫的事,不好的事。”
他取笑她说:“难道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
“罚入地狱喽。”
她的脸登时冷了下来,说道:“噢!你不应该提到这个。”
他把话扯开去了,表示佩服她刚才挣扎的时候的气力。于是她又恢复了信赖的表情,
说到她小姑娘时代的大胆。——(她嘴里还不说“小姑娘”而说“男孩子”,因为她幼
时很想参加男孩子们的游戏和打架。)有一回她和一个比她高出一个头的小朋友在一起,
突然把他捶了一拳,希望他还手。不料他一边嚷着一边逃了。另外一次,旁边走过一条
黑母牛,她跳上它的背,母牛吃了一惊,把她摔下来,撞在树上,险些儿送了命。她也
曾经从二层楼的窗口往下跳,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她不信自己敢这样做;结果除了跌得青
肿之外竟没有什么。她独自在家的时候,还发明种种古怪而危险的运动,要她的身体受
各种各式奇特的考验。
“谁想得到你是这样的呢,”他说,“平常你那么严肃”
“噢,你还没看见我有些日子自个儿在房里的模样呢!”
“怎么,你现在还玩这一套吗?”
她笑了,随后又忽然扯到另外一个题目,问他打猎不打。他回答说不。她说她有一
回对一只黑乌放了一枪,居然打中了。他听了很愤慨。
“喝!”她说,“那有什么关系?”
“你难道没心肝吗?”
“我不知道。”
“你不以为禽兽跟我们一样是生物吗?”
“我是这样想的。对啦,我要问你:你可相信禽兽也有一颗灵魂吗?”
“我相信是有的。”
“牧师说没有的。我,我认为它们有的。”她又非常严肃的补上一句:“并且我相
信我前生就是禽兽。”
他听着笑了。
“有什么可笑的?”她这么说着也跟着笑了。“我小时候就给自己编造这样的故事。
我想象我是一头猫,一条狗,一只鸟,一匹小马,一条公牛。我感到有它们的欲望,很
想跟它们一样长着毛或是翅膀,试试是什么味儿;仿佛我真的试过了。唉,你不懂吗?”
“不错,你是个动物,是个古怪的动物。可是你既然觉得和禽兽同类,又怎么能虐
待它们呢?”
“一个人总要伤害别人的。有些人伤害我,我又去伤害别的人。这是必然的事。我
从来不抱怨。对人不能太柔和!我教自己很受了些痛苦,纯粹是为了玩儿!”
“怎么,你伤害自己吗?”
“是的。你瞧,有一天我用锤子把一只钉敲在这只手里。”
“为什么?”
“一点儿不为什么。”(她还没说出她曾经想把自己钉上十字架。)
“把你的手给我,”她说。
“干吗?”
“给我就是了。”
他把手伸给她。她抓着拚命的掐,他不由得叫起来。他们象两个乡下人那样比赛,
看谁能够教谁更痛,玩得很高兴,心里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世界上其余的一切,他们生
命的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