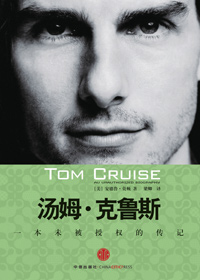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床上,谈着话,房门打开着,可以在一面镜子里瞧见彼此的快乐而累得有些虚肿的脸;
他们笑着,送着飞吻,一忽儿又朦胧入睡,瞧着对方睡着的模样;大家都懒洋洋的瘫倒
了,除了吐几个温柔的单字以外简直没气力说话。
安多纳德从来没停止一个小钱一个小钱的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她一向瞒着兄弟,
不说出她预备给他一个意外的欣喜。录取的第二天,她宣布他们要到瑞士去住一个月,
作为辛苦了几年的酬报。现在奥里维进了高师,有三年的公费,出了学校又有职业的保
障,他们可以放肆一下,动用那笔积蓄了。奥里维一听这消息马上快活得叫起来。安多
纳德可是更快活,——因兄弟的快活而快活,——因为可以看到她相思多年的田野而快
活。
旅行的准备成为一桩大事,同时也成为无穷的乐事。他们动身的时候已是八月中了。
他们不惯于旅行:头天晚上,奥里维就睡不着觉;火车上的那一夜,他也不能阖眼。他
整天担心,怕错失火车。他们俩都急急忙忙,在站上给人家挤来挤去,踏进了一间二等
车厢,连枕着手臂睡觉的地位都没有:——睡眠是号称民主的法国路局不给平民旅客享
受的特权之一,为的让有钱的旅客能够独享这个权利而格外得意。——奥里维一刻都没
闭上眼睛:他还不敢肯定有没有误搭火车,一路留神所有的站名。安多纳德半睡半醒,
时时刻刻惊醒过来;车厢的震动使她的头摇晃不定。奥里维借着从车顶上照下来的黯淡
的灯光瞅着她,看她脸色大变,不由得吃了一惊。眼眶陷了下去,嘴巴很疲倦的张着;
起色黄黄的,腮帮上东一处西一处的显着皱纹,深深的刻着居丧与失望的日子的痕迹:
她神气又老又病。——她的确是太累了!她心里很想把行起延缓几天,可又不愿意使兄
弟扫兴,竭力教自己相信没有什么病,只是疲劳过度,一到乡下就会复原的。啊!她多
么怕在路上病到!她觉得他瞧着她,便勉强振作精神,睁开眼来,——睁开这双多
年轻,多清澈,多明净的眼睛,但常常不由自主的要被苦闷的浊流障蔽一会,好似一堆
云在湖上飘过。他又温柔又不安的低声问她身体怎么样,她握着他的手,回答说很好。
她只要听到一个表示爱的字就振作了。
在多尔与蓬塔利哀之间,红光满天的曙色一照到苍白的田里,原野就仿佛醒过来了。
高高兴兴的太阳——象他们一样从巴黎的街道、尘埃堆积的房屋、油腻的烟雾中间逃出
来的太阳——照着大地,草原打着寒噤,被薄雾吐出来的一层乳白色的气雾包裹着。路
上有的是小景致:村子里的小钟楼,眼梢里瞧见的一泓清水,在远处飘浮的蓝色的岗峦。
火车停在静寂的乡间,阵阵的远风送来清脆动人的早祷的钟声;铁路高头,一群神气俨
然的母牛站在土堆上出神。这种种都显得那么新鲜,引平安多纳德姊弟的注意。他们好
似两株桔萎的树,饮着天上的甘露愉快极了。
然后是清晨,到了应当换车的瑞士关卡。平坦的田里只有一个小小的车站。大家因
为一夜没睡,觉得有点儿恶心,清晨潮湿的空气又使人微微颤抖。四下里静悄悄的,天
色清明,周围那些草原的气息冲进你的嘴巴,沾着你的舌头,沿着你的喉咙,象一条小
溪似的流到你胸中。露天摆着一张桌子,大家站在那儿喝一杯提神的热咖啡,羼着带酪
的牛乳,还有一股野花野草的香味。
他们搭上瑞士的火车,看了车上不同的设备高兴得象儿童一样。可是安多纳德累极
了!她对于这种时时刻刻的不舒服觉得莫名片妙。为什么看到了这些多美多有趣的东西
而并不怎么高兴呢?和兄弟作一次美妙的旅行,不用再为将来的生活操心,只顾欣赏她
心爱的自然界:不是她多少年来梦想的吗?现在她是怎么回事呢?她埋怨自己,勉强教
自己欣赏一切,看着兄弟天真的快乐强作欢容
他们在土恩停下,预备第二天换车到山里去。可是在旅馆里,安多纳德晚上忽然发
了高度的寒热,又是呕吐,又是头疼。奥里维慌了,心神不定的挨了一夜,天明就去请
医生:——又是一笔意想不到的支出,对他们微薄的资源大有影响。——医生认为暂时
并不怎么严重,不过是极度的劳顿,身体太亏了一点。继续上路是不可能了。医生要安
多纳德整天躺在床上,并且说他们也许要在土恩多待一些日子。他们虽然难过,幸而事
情没有意料中的严重,也就很安慰了。可是老远的跑来,关在简陋的旅馆里,卧房给太
阳晒得象暖室一般,毕竟是够痛苦的。安多纳德劝兄弟出去散散步。他在旅馆外边走了
一程,看见阿尔河的绿波,远远的天边又有白色的山峰在云端浮动,快活极了;但这快
乐,他一个人没法消受,便匆匆回到姊姊房中,非常感动的把见到的风景告诉她;她奇
怪他回来这么早,劝他再出去,他却象以前从夏德莱音乐会回来的时候一样的说:
“不,不,那太美了;我一个人看了心里会难受的”
这种心绪是一向有的:他们知道,不跟对方在一起自己就不是个完全的人。但听到
对方把这意思说出来总是怪舒服的。这句温柔的话给安多纳德的影响比什么药都灵验。
她微微笑着,又喜悦,又困倦。——很舒畅的睡了一夜,她决意清早就走,不去通知医
生,免得他劝阻。清新的空气和一同玩赏美景的快乐,居然使他们不致为了这个卤莽的
行动再付代价。两人平安无事的到了目的地;那是山中的一个小村,在什齐兹附近,临
着土恩湖。
他们在一家小旅馆里待了三四星期。安多纳德没有再发烧;可是身体始终不硬朗。
她只觉得脑袋重甸甸的支持不住,时时刻刻的不舒服,奥里维常常问到她的健康,只希
望她的脸色不要那么苍白。可是他对着美丽的景色陶醉了,自然而然的把不愉快的思想
撂在一边,所以听到她说身体很好,就很愿意信以为真,——虽然明知道事实并不如此。
另一方面,她对于兄弟的快乐,清新的空气,尤其是对于休息,深深的感到快慰。经过
了多少艰苦的年头而终于能休息一下,不是最愉快的事吗?
奥里维想把她拉着一同去散步,她心里也很高兴和他一块儿去;可是好几次,她勇
敢的走了二十分钟,不得不停下,气透不过来了,心要停止跳动了。于是他只能自个儿
向前,——虽然是并不辛苦的攀援,她已经忐忑不安,直要他回来了才放心。或者两人
出去随便遛遛:她抓着他的胳膊,迈着细步,谈着话;他尤其多嘴,一边笑,一边讲他
将来的计划,说着傻话。走在半山腰,临前山谷,他们遥望白云倒映在静止不动的湖里,
三三两两的小艇在那里飘浮,仿佛氽在池塘上的小虫;他们呼吸着温和的空气,听着远
风送来一阵又一阵的牛羊颈上的铃声,带着干草与树脂的香味。两人一同梦想着过去,
将来,和他们觉得所有的梦里头最渺茫而最迷人的现在。有时,安多纳德不由自主的感
染了兄弟那种小孩子般的兴致:跟他追着玩儿,扑在草里打滚。有一天他居然看到她象
从前一样的笑了,他们小时候那种女孩子的憨笑,无愁无虑的,象泉水般透明的,他多
年没听见过的笑声。
但更多的时候,奥里维忍不住要去作长途的远足。过后他心里难受,埋怨自己不曾
充分利用时间和姊姊作亲密的谈话。便是在旅馆里,他也往往把她一个人丢下。同寓有
一群青年男女,奥里维先是不去交际,可是慢慢的受着他们吸引,终于加入了他们的团
体。他素来缺少朋友,除掉姊姊之外,只认得一般中学里鄙俗的同学和他们的情妇,使
他厌恶。一旦处在年纪相仿,又有教养,又可爱,又快活的青年男女中间,他觉得非常
痛快。虽然性情孤僻,他也有天真的好奇心,有一颗多情的,贞洁而又肉感的心,看着
女性眼里那朵小小的火焰着迷。而他本人尽管那么羞怯,也很能讨人喜欢。因为需要爱
人家,被人家爱,他无意中就有了一种青春的妩媚,自然而然有些亲切的说话,举动,
和体贴的表现,唯其笨拙才显得格外动人。他天生的富于同情心。虽是孤独生活养成了
他讥讽的精神,容易看到人们的鄙俗与缺陷而觉得厌恶,——但跟那些人当面碰到了,
他只看见他们的眼睛,从眼睛里看出一个有一天会死的生灵,象他一样只有一次生命,
而也象他一样不久就要丧失生命的。于是他不由自主的对它感到一种温情,无论如何也
不愿意去难为它。不管心里怎么样,他总觉得非跟对方和和气岂不可。他是懦弱的,所
以天生是讨一般人喜欢的;他们对于所有的缺陷,甚至所有的美德,都能原谅,——只
除了一件:就是为一切德性之本的力。
安多纳德可不加入这个青年人的集团。她的体力,她的疲乏,表面上没有原因的精
神的颓丧,使她瘫下去了。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操心与劳苦,她被折磨得身心交瘁;姊弟
的角色颠倒了:如今她觉得跟社会,跟一切,都离得很远了!她不能再回到社会里
去:所有那些谈话,那些喧闹,那些欢笑,大家所关切的那些小事,都使她厌烦,疲倦,
甚至于气恼。她恨自己这种心情,很想学着别的姑娘们的样,对她们所关切的也关切,
对她们所笑的也笑可是办不到了!她的心给揪紧了,仿佛已经死了。晚上她守在屋
里,往往连灯也不点,在暗中坐着;奥里维却在楼下客厅里,搞他那些已经习惯的谈情
说爱的玩艺儿。安多纳德直要听见他上楼,听见他和女友们笑着,絮聒着,在她们的房
门口恋恋不舍的,一遍又一遍的说着再会的时候,她才会从迷惘的境界中醒来;那时,
她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微微笑着,起来捻开了电灯。兄弟的笑声使她精神振作了。
秋深了。太阳黯淡了。自然界萎谢了:在十月的云雾之下,颜色慢慢的褪了;高峰
上已经盖了初雪,平原上已经罩了浓雾。游客动身了,先是,一个一个的,随后是成群
结队的。而看见朋友们走,——即使是不相干的,——又是多么凄凉;尤其是眼看恬静
而甘美的夏天,那些在人生中好比水草般的时光消失的时候,令人格外伤悲。姊弟俩在
一个阴沉的秋日,沿着山,往树林里作最后一次的散步。他们不出一声,黯然神往的幻
想着,瑟索的偎倚着,裹着衣领翻起的大氅,互相紧握着手指。潮湿的树林缄默无声,
仿佛在悄悄的哭。林木深处,一头孤单的鸟温和的怯生生的叫着,它也觉得冬天快来了。
轻绡似的雾里,远远传来羊群的铃声,呜呜咽咽的,好象从他们的心灵深处发出来的
他们回到巴黎,都很伤感。安多纳德的身体始终没复原。
那时得置备奥里维带到学校去的被服了。安多纳德为此花掉了最后一笔积蓄,甚至
还偷偷的卖去几件首饰。那有什么关系呢?将来他不是会还她的吗?——何况他现在进
了学校,她自己用不着花什么钱了!她不让自己想到他走了以后的情形:一边缝着
被服,一边把她对兄弟的热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工作里头;同时她也预感到,这或许是她
替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分别以前的几天,他们形影不离,唯恐虚度了一分一秒。最后一天晚上,他们睡得
很迟,对着炉火,安多纳德坐在家中独一无二的安乐椅里,奥里维坐在她膝旁一张矮凳
上,拿出他素来被宠惯的大孩子模样,惹人怜爱。对于将要开始的新生活,他觉得有些
担心,也有些好奇。安多纳德想到他们的亲密从此完了,骇然自问将来怎么办。他似乎
有心加强她的苦闷似的,这最后一晚的一举一动都比平时更温柔:他天真的撒娇,象一
个快要出门的人把自己的优点与可爱的地方统统拿了出来。他坐在钢琴前面,久久不已
的弹着她在莫扎特与格路克的作品中最喜爱的篇章,——那种缠绵悱恻,惆怅而高远的
意境,正是他们过去的生涯的缩影。
分别的时间到了,安多纳德把奥里维送到校门口。她回到家中,又孤独了。但这一
回和以前上德国去的情形不同,那次的离别与相会是可以由她作主的,只要她觉得支持
不住就可以回来。这一回是她在家而他走了,那是长久的离别,终生的离别。可是她那
么富于母性,初期只念念不忘的想着弟弟而没想到自己,想着他刚开始过着那么不同的
新生活,受着老同学的欺侮,还有那些琐碎的烦恼,虽是无足重轻,但一个独居其处而
惯于为所爱的人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