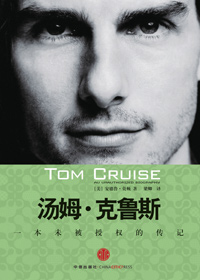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人笑了笑,过了一会又说:“你瞧,做个音乐家多了不起!造出这些奇妙的场面,
不是最大的光荣吗?那简直跟上帝下凡一样。”
孩子听了大吃一惊,怎么!这是人造出来的?他真没想到。他几乎以为那是自然而
然产生的,是天造地设的原来一个人,一个音乐家,就象他将来也会成功的那种人,
竟能造出这样的作品!哎唷!希望自己能有那么一天,便是一天也好!过后过后,
随便怎么都可以!就是死也甘心了!他问:“祖父,这是谁作的呢?”
祖父说作者叫做法朗梭阿?玛丽?哈斯莱,是个德国的青年音乐家,住在柏林,他
从前认识的。克利斯朵夫竖起耳朵听着,突然问道:
“那末您呢,祖父?”
老人打了个寒噤。
“什么?〃他问。
“您,您有没有也做过这些东西?”
“当然,〃老人的声音有点儿不高兴。
说完他不做声了;走了几步,又深深的叹了口气。这是他终身隐痛之一。他一向想
写戏剧音乐,可是灵感不帮忙。他纸夹里头的确藏着他创作的一二幕乐曲;但他对它们
的价值毫无把握,从来不敢拿给人家去评一评。
直到家里,他们俩再也不说一句话。两人都睡不着觉。老人心里很难过,念着《圣
经》安慰自己。克利斯朵夫在床上回想着当晚的情形,连小地方都记得,赤足的女郎又
在他面前出现了。快睡着的时候,一句音乐忽然清清楚楚在耳边响着,好象乐队就在近
边;他不由得惊跳起来,昏昏沉沉的靠着枕头想道:“将来有一天,我也要写这种东西,
噢!我是不是能写呢?”
从那时期,他唯一的欲望就是看戏。因为人家把看戏作为他工作的酬报,他对功课
更上劲了。他老想着戏:上半星期想着过去的戏,下半星期想着下次的戏。他甚至怕上
演的那天害病,这种恐惧使他觉得有三四种病的征象,到了那天,他吃不下饭,好象担
着重大的心事,骚乱不堪,跑去对时钟看了几十次,以为天不会黑的了。临了他忍不住
了,在售票房开门以前一个钟点就出发,怕没有位置;又因为他第一个到,对着空荡荡
的场子不免暗暗发急。祖父和他说过,有两三次因为看客不多,演员宁可退还评价而停
演。他注意来的人,数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噢!不够啊人数老是不
够啊!〃看到花楼或正厅里来了几个重要的人物,他心又轻松了些,对自己说:“这一个,
他们总不敢请他回去吧?为了他,总得开演吧!〃——可是他还没有把握,直要乐师们进
了场才放心。但他到最后一刻还在发急,不知道会不会开幕,会不会象某一晚那样临时
宣布更改戏码。他山猫似的小眼睛瞅着低音提琴手的乐器架,瞧瞧谱上的题目是不是当
晚演的戏。等到看清楚了,过了两分钟又看一下,只怕刚才看错了乐队指挥还没有
进场,一定是害病了幕后有人忙忙碌碌的乱做一堆,又是谈话声,又是急促的脚步
声。可是闯了祸,出了事吗?还好,声音没有了。指挥已经在他的位置上。明明一切都
准备好了还不开场!是怎么回事呢?他急坏了。——终于开演的记号响了。他
的心跳了。乐队奏着序曲;然后,克利斯朵夫有几个钟点在极乐世界中载沉载浮,美中
不足的就是担心这境界早晚要完的。
过了些时候,一件音乐界的大事把克利斯朵夫刺激得更兴奋了。第一次使他激动的
那出歌剧的作者,法朗梭阿?玛丽?哈斯莱要来了。他要亲自指挥乐队演奏他的作品。
全城都为了这件事轰动起来。年轻的大音乐家正在德国引起剧烈的争辩;十五天内,大
家只谈论他。可是他到了城里,情形又不同了。曼希沃和老约翰?米希尔的朋友们老讲
着他的新闻,把音乐家的起居生活说得那么离奇,孩子非常热心的听在耳里。想到大人
物就在这儿,住在他的城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走着同样的街道,他暗中激动到极点,
只希望能见到他。
大公爵①把哈斯莱招待在他的府第里。除了上戏院去主持预奏会,音乐家难得出门,
而逢到预奏的场合,克利斯朵夫是不能进去的;他又因为生性很懒,进出都坐着亲王的
车。因此克利斯朵夫很少有瞻仰到他的机会;他只有一次看见他在路上过,而且只看见
车厢底里的皮大氅,虽然他在路旁等了几小时,用肘子左一下右一下的在人堆中钻到第
一排,还得想法不给人家挤掉。他又花了好多时间站在爵府外面,听人家说哪儿是音乐
家的卧室,他就远远的对那边的窗子东张西望,聊以自慰。他往往只看到百叶窗:因为
哈斯莱起得很晚,差不多整个上午窗子总是关着的。所以消息灵通的人说哈斯莱怕见日
光,永远过着夜生活。
①克利斯朵夫本乡的城市是一个诸侯的首府,诸侯的爵位当是大公爵。书中屡次提
及亲王,是欧洲人对一般诸侯的尊称,与实际的爵位无关。
末了,克利斯朵夫终于能靠近他的大人物了。那是举行音乐会的一天。全城的人都
到场。大公爵和他的家族占据了御用的包厢,高头悬着冠冕,由两个肥胖的小天使高高
的举在空中。戏院的布置象举行什么大典一样。台上扎着橡树的枝条和带花的月桂。凡
是有些本领的音乐家,都以能参加乐队为荣。曼希沃坐在他的老位置上,约翰?米希尔
担任合唱队的指挥。
哈斯莱一出现,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妇女们还站起来想看个仔细。克利斯朵夫恨不
得用眼睛把他吞下去。哈斯莱的相貌很年轻很清秀,可是有些虚肿,疲倦;鬓脚已经不
剩什么,在蜷曲的黄头发中间,头顶有点儿秃了。眼睛是蓝的,目光没有神。淡黄的短
髭下面,那张带有嘲弄意味的嘴巴老是在那里微微扯动。他身躯高大,好似站不稳的样
子,可并非为了局促,而是由于疲倦或是厌烦。他的指挥的艺术灵活而带点任性,整个
高大而脱骱似的身子在那里波动,手势忽而柔媚忽而激烈,象他的音乐一样。可见他非
常的神经质;而他的音乐也反映出这种性格。一向无精打采的乐队这时也感染了那种震
荡颠动的气息。克利斯朵夫呼吸频促,虽然怕引起人家的注意,还是没法安安静静的坐
在那里;他烦躁之极,站起身子,音乐给了他那么剧烈那么突兀的刺激,逼得他摇头摆
脑,手舞足蹈,使邻座的人大受威胁,只能尽量躲闪他的拳脚。而且全场的人都兴奋若
狂,音乐会的盛况比音乐本身更有魔力。末了,掌声跟欢呼声象雷雨似的倒下来,再加
乐队依照德国习惯把小号吹得震天价响,表示对作者致敬。克利斯朵夫得意之下,不由
得浑身哆嗦,仿佛那些荣誉是他受到的。他很高兴看见哈斯莱眉飞色舞,象儿童一样的
心满意足;妇女们丢着鲜花,男人们挥着帽子;大批的听众象潮水一般望舞台拥过去。
每人都想握一握大音乐家的手。克利斯朵夫看见一个热烈的女人把他的手拿到唇边,另
外一个抢着哈斯莱放在指挥台上的手帕。他莫名片妙的也想挤到台边,可是他要真的到
了哈斯莱身边,马上会不胜惊惶的逃走的。他象头羊似的低前脑袋在裙角与大腿之间乱
钻,想走近哈斯莱,——但他太小了,挤不过去。
祖父在大门口把他找到了,带他去参加献给哈斯莱的夜乐会。那时已经天黑了,点
着火把。乐队里全体人员都在场,①所谈的无非是刚才听到的神妙的作品。到了爵府前
面,大家静悄悄的集中在音乐家的窗下。虽然哈斯莱跟众人一样早已知道,可是大家还
装得非常神秘,在静寂的夜里开始演奏哈斯莱作品中最著名的几段。哈斯莱和亲王在窗
口出现了,众人对他们欢呼,而他们俩也对大家行礼。亲王派了一个仆人来请乐师们到
府里去。他们穿过大厅,壁上满是油画,绘着戴盔的裸体人物:深红的皮色,做着挑战
的姿势;天上盖着大块的云象海绵一般。另外也有男男女女的大理石像,穿着铁皮做的
短裙。地毯那么柔软,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音。后来进入一间大厅,光亮如同白昼,桌
上摆满着饮料和精美的食物。
①Sérénade为曲体名称(即所谓小夜曲),亦为演奏此种乐曲之音乐会名称,原
为男女相悦求爱之用,后演变为对名流伟人之歌颂,但仍照昔时习惯,于夜间露天举行。
大公爵就在那间屋里,可是克利斯朵夫看不见他:他心目中只有哈斯莱一个人。哈
斯莱迎着乐师走过来,向他们道谢,他一边说一边找字,赶到句子说到一半想不出下文,
便插一句滑稽的俏皮话,引得众人都笑了。然后大家开始吃东西。哈斯莱特别把四五个
艺术家请在一边,把克利斯朵夫的祖父也找了来,恭维了一番。他记得最先演奏他作品
的那些人里头就有约翰?米希尔;又提到他常常听见一个朋友,祖父从前的学生,说他
如何如何了不起。祖父不胜惶恐的道谢,回答了几句过火的奉承话,连极崇拜哈斯莱的
克利斯朵夫听了也非常难为情。但哈斯莱似乎觉得挺舒服挺自然。等到祖父不知所云的
说了一大堆,没法接下去的时候,便把克利斯朵夫拉过去见哈斯莱。哈斯莱对克利斯朵
夫笑了笑,随手摸着他的头;一知道孩子喜欢他的音乐,为了想见到他已经好几晚睡不
着觉,他便抱起孩子,很亲热的向他问长问短。克利斯朵夫快活得面红耳赤,紧张得话
也不会说了,望也不敢望了。哈斯莱抓着他的下巴颏儿,硬要他抬起头来。克利斯朵夫
先偷偷的张了一下:哈斯莱眼睛笑眯眯的,非常和善;于是他也笑了。然后,他觉得在
他心爱的大人物的臂抱中那么快乐,那么幸福,以至眼泪簌落落的直掉下来。哈斯莱被
这天真的爱感动了,对他更亲热,把他拥抱着,象母亲一样温柔的和他说话。同时他尽
挑些滑稽的话,呵孩子的痒,逗他发笑;克利斯朵夫也禁不住破涕为笑了,一忽儿他已
经跟他很熟,毫无拘束的回答哈斯莱的话,又自动咬着哈斯莱的耳朵说出他所有的小计
划,仿佛他们俩是老朋友;他说他怎样想做一个象哈斯莱那样的音乐家,写出象哈斯莱
那样美妙的作品,做一个大人物等等。一向怕羞的他居然放心大胆的说着,可不知道说
些什么,他出神了。哈斯莱听着他的唠叨笑开了,说:
“等你大了,成功了一个音乐家的时候,你得上柏林来看我,我可以帮你的忙。”
克利斯朵夫快活得答不上话。哈斯莱便跟他开玩笑说:
“你不愿意吗?”
克利斯朵夫拚命摇头,摇了五六次,表示决不是不愿意。
“那末一言为定喽?”
克利斯朵夫点点头。
“那末你亲我一下啊!”
克利斯朵夫把胳膊勾着哈斯莱的脖子,使劲的抱着他。
“哎啊,小家伙,你把我弄潮了!放手!你擤擤鼻子好不好!”
哈斯莱一边笑一边亲自替又羞又喜的孩子擤鼻子。他把他放在地下,拉他到桌子旁
边,把糕饼塞满了他的口袋,说道:
“再会了!别忘了你答应的话。”
克利斯朵夫快乐得有点飘飘然。世界上一切都不存在了。他怀着一腔热爱,目不转
睛的看着哈斯莱所有的表情,所有的动作。可是忽然有句话使他听了很奇怪。哈斯莱举
起杯子,脸色顿时紧张起来,说道:
“我们在这种快乐的日子也不该忘了我们的敌人。那是永远不应该忘掉的。我们没
有被打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留情。我们也用不着为了他们的生存而留情。所以我的干杯祝
贺对有些人是除外的!”
大家对于这古怪的祝辞笑着鼓掌;哈斯莱也跟着大家一起笑,又象刚才一样的高兴
了。但克利斯朵夫心里很不痛快。虽然他崇拜哈斯莱,不敢议论他的行为,可是他觉得
今天晚上应当和颜悦色,只有些快乐的念头才对,哈斯莱想到那些丑恶的事未免太扫兴
了。可是这个印象是模糊的,而且很快就被过度的欢乐和在祖父杯子里喝的一点儿香槟
酒赶跑了。
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语的说个不停,哈斯莱对他的恭维使他高兴极了;他大声
的说哈斯莱是个天才,一百年只会出一个的那种天才。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把他象爱
情那样的醉意都藏在心里:啊!他亲过他,抱过他!他多好!多伟大!
他在小床上热烈的抱着枕头想道:
“噢!我为他死也甘心的,甘心的!”
光明的流星在小城的天空照耀了一晚之后,克利斯朵夫精神上便受到确切不移的影
响。在他整个的童年时代,哈斯莱变成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