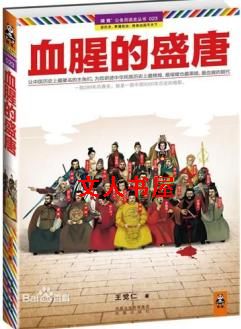盛唐风月-第47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入了私囊而已。身在官场;没人追究的时候也就罢了;一旦有人穷究;一个贪字就是最大的隐患
“派人送个信去云州;对宇文夫人他们禀报一声吧;唉。”
刘墨答应一声;却并没有退去;而是有些忧虑地问道:“陛下大怒之下令继续追查;朝中会不会有人想要追回赃款;继而在宇文夫人他们身上动脑筋?
“你不要担心;我既然肯接受他们徙往云州;就已经做好了这最坏的打算。宇文夫人他们已经丢弃了在长安的所有产业;随身只带了少许细软;如果真的有人到云州追查;王子羽会挡一挡的。要知道;当初张丞相受难的时候;他的奔走居功至伟;蒋岑既然和张丞相相交甚密;应该不会一味穷追猛打。倒是给事中冯绍烈是裴相国引以为给事中的人;应是其心腹无疑。”
“是;长安报说;张丞相如今正在病重;却还抱病为冯绍烈的父亲冯昭泰写神道碑;其碑文一千四百余字。要知道;张丞相据说已经病得七荤八素了;抱病拟写这样的神道碑;张丞相和冯绍烈的关系也断然非同小可。”
“想是如此了;但他们应该也知道;宇文融的两个儿子还未成气候;不至于担心遭其报复。若是一定要惹我;我可没有宇文融那等把柄给人抓;触及到了我的头上;想来鱼死网破四个字的真义;我会让人好好领会领会
杜士仪既如此说;刘墨自无二话;答应一声便要下去。然而;他刚到门口;杜士仪突然想起一桩同样重要的事;连忙开口将其叫住;好一会儿方才似笑非笑地问道:“刘墨;我和夫人把白姜许配给你;如何?”
“啊”刘墨一时措手不及;然而;见杜士仪虽然满脸都是笑意;却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一下子醒悟了过来;慌忙翻身下拜道;“多谢郎主和夫人;多谢郎主和夫人我一定一定不会辜负二位美意”
“好好好;你下去;我回头就让人给你们预备预备;也算是近来难得的大喜事”
杜士仪笑着屏退了刘墨;瞥见一旁的吴天启正在偷笑;待发现自己看他方才立时一本正经地坐直了身子;他登时哑然失笑:“你这小子也下去吧;明日我去州学讲论语;你也不妨一块去听听。对了;以后但凡我这里没有要事吩咐你;你整理完了书房;随时随地可以到代州州学去蹭个课;别人知道你是我的从者;必然会以为是我差你去巡查的;定然不会赶你走。”
这下子换成吴天启高兴得一蹦三尺高了。他连声道谢之后;起身一溜烟就跑出了屋子。不一会儿;外头就传来了他忘情的欢呼。
两件对自己来说都只是举手之劳的事;却让刘墨和吴天启高兴坏了;杜士仪自己也禁不住心情稍好。然而;想到赤毕跟着宇文融前往昭州平乐;这一走就是一年多了。现如今又要面对宇文融的再次被处流刑;他不禁暗自叹了一口
只希望;宇文融和赤毕那两个身份境遇截然不同的人;能够平安无事
昭州尽管远在岭南;但距离桂州都督府所在的桂州;只有上百里路——即便这上百里路并非官道;得转道荔浦方才能达;终究比桂州所领其他偏远到车马难及的州县要强得多了。而岩州乃是调露二年析郁林、横、贵、牢、白五州地置;州治安乐县;瘴气密布;历来州官都很少有人愿意出任;安乐县更只有一个光杆县令。当宇文融得到流刑诏书的时候;早有预料别人会穷追猛打的他已经有些麻木了。
说是县尉;但平乐县乃是昭州县治;县廨之内也总算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然而;上下都知道宇文融是因罪被贬;他上任这一年多来;别人都躲得远远的;自始至终没什么人和他往来;他随身的两个老仆操持起居;此外便是一个沉默到几乎很少开口的大汉随侍身侧。此时此刻;宇文融默默地看着老仆整理行李;自己拖着沉重的步子出了屋子;见那身形健壮的身影正在低头劈柴;他突然低低问了一声。
“我即将配流岩州;山高路远瘴疠横行;你还要跟着我同行?”
赤毕回头看了宇文融一眼;这才言简意赅地说道:“郎主早有吩咐;宇文少府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自会相从宇文少府前往岩州。”
宇文融从家里带了五个仆人来到昭州平乐;可现如今只剩下区区两个老仆;其他三个壮年的都已经逃亡得无影无踪;尽管他沦落到这个地步;也不会再有什么人用暴力手段觊觎他的性命;可他还记得自己刚刚上任的时候;那次山民闹事;不敢冲击刺史署;却来冲击县廨;他因为不受待见而被迫出面前去平息;可他他根本听不懂那些山民的土语。倘若不是赤毕突然现身;并露出一手超绝的武艺震慑了山民;恐怕他早就没有命在了。
事后;他才知道;赤毕是受了杜士仪之命到昭州平乐保护他。既然道破了身份;赤毕就一直呆在了他的身边。可他没想到;这样一个武艺高强的人竟然能够在昭州守着他整整一年多
“杜君礼高义;我自然铭感五内;我并不是有意拖延”
不等宇文融把话说完;赤毕就打断道:“我之所以一来便如实告知宇文少府我之来意;就绝不会得了东西便立时遁去无踪。宇文少府既有疑虑;那就无需解释。这一路上;我自会善尽职责。”
赤毕如此说;宇文融越发觉得心中愧疚。然而;蝼蚁尚且贪生;更何况是他?他还有妻子和儿女在远方守候;倘若就这么死了;岂不是让仇敌更加得意?而且;他仍然还留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天子在发现国家财计没有他绝不可为的情况下;宽宥他的那些疏失;让他能够起复重新回朝。也正因为如此;赤毕所求的东西;他不由得犹豫着不想给出去。当然;潜意识中;他更怕没有这样一个可靠的护卫随侍;自己根本无法在岭南生存。
然而;等到从昭州动身前往岩州;他方才知道;这一路上究竟有多艰难。尽管说是只数百里路;可一路基本上没有官道;只有那些山间林间小道;车辆根本无法通行。而那些押送他前往岩州的军卒凶神恶煞;硬是逼着他每日必须赶路五十里以上。一个跟着他多年忠心耿耿的老仆在出发十天之后就因为发病赶路;最终一夜高热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撒手人寰。默默葬了老仆之后;宇文融自是心情越发沉重;又走了两日之后;自己也因为忧虑过重;瘴气又深;一下子病倒了。
面对这样的景况;为首的小军官大为恼怒;本还要再逼;赤毕终于看不下去了。若非他带着避瘴气的药丸;又提早给自己和宇文融几人服下;恐怕不习惯南方气候的他们早就支撑不住了。他纵使铁打的筋骨;总不能把宇文融背到岩州这种荒僻的地方去。因此;他嘱咐另一个老仆先行看护宇文融;随即就把为首的小军官叫到了一边;以宇文融感染瘴疠为由;要求回昭州或是邻近州县暂时休养。
“时间那么紧;根本不能宽限;更何况休养”
“按照永徽律疏;流人如若在路上患病;就该给假调治;不在每日五十里程限之内”赤毕直接**地顶了回去;见对方面露凶光;手甚至按在了刀柄上;他便哂然一笑道;“我并非宇文少府的从者;而是其京城好友派来随侍左右的。你若是不答应;我便到桂州都督岭南采访使张使君那里去告状;倘若张使君也不理会;我就到长安去告御状”
说到这里;赤毕伸手在一旁一棵粗大的竹子上一按;旋即猛然出拳击去;那硕大的竹子竟一瞬间折断倒地。见那小军官为之瑟缩;他方才安之若素地回到了宇文融那儿;趁着几个军卒商量之际;把自己为宇文融请假调治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多谢;多谢你了”宇文融一时流露出了难以抑制的感谢之色;但眼神中却流露出了深深的灰败。
“宇文少府不用谢我。”尽管宇文融如今连县尉都不是了;但赤毕在岭南陪着人呆了一年多;早已习惯了这个称呼;一时半会还改不过去;“我本来是可以花钱买通他们。但这些人久在岭南;若是真的起了坏心;我一人难以抗衡;毕竟他们更识得路途。与其如此;只能暂时狐假虎威胁迫他们听命。”
宇文融半辈子风雨;什么都经历过了;当然明白赤毕担心的是什么。他轻轻点了点头;但随即低声说道:“不过;不要送我到这桂州所领之地休养;桂州都督张九龄乃是因我弹劾张说之故;这才由中书舍人任上被贬出为外官;必然恨我入骨;想要我死也不为过。去广州”
竭尽全力吐出这几句话;宇文融一时气喘吁吁;好半晌方才低声说道:“广州不比这里气候湿热瘴气横行;而且有好大夫。”
张九龄何许人也;赤毕却还知道一个大概。尽管其人颇有刚正之名;但他眼下最重要的是保护宇文融的安全;宇文融既铁了心要前往广州;他几乎想都不想便答应道:“好此事交给我”
折返平乐然后回广州的这一条路;却是通衢官道。经贺州的临贺、封阳;再往东行;便是广州地界。尽管负责押送的军卒们最初还不愿意;但在赤毕经过昭州平乐时;在一处柜坊兑了二十贯钱作为报酬之后;他们的脸色就好看多了。而等到进入广州城时;同样也是第一次到这里来的他们亦是好奇得东张西望;当赤毕张罗了一家旅舍把众人安顿了下来之后;几个人竟是连押送的本职都顾不上;齐齐出门见识这岭南第一大城的繁华富庶去了。
横竖宇文融根本就不敢跑
自己总共两个老仆;如今只剩下了一个人;因此赤毕说要到外头再买两个仆从随侍的时候;宇文融并没有拒绝。这一路上的辛苦他固然已经领教过了;可更知道赤毕这个外人为了自己同样殚精竭虑;至于些许银钱;相形之下反而是小事了。
然而;眼看其要出门;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当即叫住了赤毕;犹豫片刻便开口说道:“我毕竟是流人;如今因病暂时在广州休养;若事后才因为别人举发报到了广州都督耿仁忠的耳中;怕是讨不了好。烦请你让人去广州都督府报个信。”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更何况广州都督还兼领岭南五府经略使;管辖着整个岭南道;而宇文融如今已经被一撸到底;很难说再有起复的希望;因此;赤毕自然答应了一声。等到他嘱咐仅存的一个老仆好生照顾宇文融;先往广州都督府投书送给了广州都督耿仁忠;到集市上挑选了两个看上去还老实的壮健仆从回到了旅舍之后;却发现那些去逛街的军卒倒还不见回来;却已经有几个差役骂骂咧咧地从旅舍中出来;从自己面前离去。
心中一突的他连忙带着人快步进了旅舍;到了自己赁下的院子时;就只见院子里刚刚晾晒出来的那些受潮衣服竟是被人丢得满地都是。情知刚刚那些差役来者不善;他也顾不得那两个新买的仆从了;快步进屋一看;就发现宇文融正双目无神地靠坐在那儿;一旁跪坐的老仆则是垂泪不止。
“出了什么事?”
“赤郎回来了”那老仆见到赤毕就仿佛是见到了主心骨一般;慌忙一骨碌起身迎上前来;带着哭腔说道;“刚刚那些是广州都督府来的人;说是阿郎因贪墨之罪名确凿;为陛下一怒决以流刑;若是还念君恩;就应该尽快启程前往岩州;而不是在这广州装病拖延时间。那几个差役说话极其难听;阿郎一时忍不住斥了几句;他们他们出去后;就把外头那些衣架全都砸翻了。还撂下话说;耿都督有命;限期三日之内;阿郎必须立时上路”
听到这话;赤毕登时眉头倒竖。尽管他从前对宇文融谈不上有什么尊敬抑或是其他;但宇文融被贬昭州平乐尉期间;除却那些县廨的杂务之外;默默整理的还有关于河道、盐铁、度支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手稿;他对此人涉猎财计之广;还是颇为震撼的。即便他一直觉得宇文融这次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可已经黜落被贬;现如今还受了流刑;确实真正病倒难行;有些人就连这最起码的怜悯之心也没有么?
想到这里;他登时恼火地说道:“我去求见耿都督”
“不要去”宇文融几乎是从喉咙口迸出了三个字;见赤毕回过头来;他竭力用枯瘦的手抓住榻沿边上;疲惫地叫道;“你打算以什么身份去求见耿都督?”
此话一出;赤毕登时为之语塞。是啊;他用什么身份去?倘若他以代州长史杜士仪的心腹从者的身份去见耿仁忠;对方不但会质疑;而且还可能会借题发挥。而如果他以宇文融的从者前去求见;被拒之门外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可是;流人路上若病倒;可以给假调治;这是朝廷律法上明文规定的;结果到了某些人手上;便成了打击政敌的工具;简直是无耻之尤
见赤毕果然脸色发青地缓步回转;宇文融露出了一丝惨然的笑容;随即低声说道:“事到如今;我有话想对赤郎说。刘甲;你出去门外守一守;莫要让不相于的人进来。”
榻边那老仆点点头;蹒跚出了门。这时候;宇文融方才费力地拉过自己枕边一个沉重的包袱;见赤毕已经在榻边坐了下来;他便将其推到了对方面前:“你跟着我在岭南一年;这是你看着我整理出来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