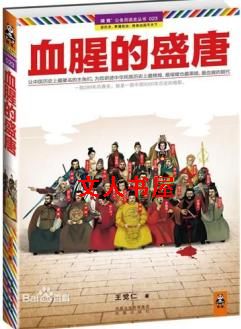盛唐风月-第2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错;我老是别人说一句就高兴就生气;耳根子太经不住话了我自做我自己的;别人怎么说和我何于?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心就够了;从今往后;该听的我就听;不该听的我只当耳边风
尽管崔俭玄曲解了部分意思;但杜士仪眼下只要人不钻牛角尖就行了;莞尔一笑就回席坐下;却是轻轻一拍手。
只听外间突然筚篥一响;继而就是琵琶铙钹锣鼓;随着这铿锵有力极有力度的曲乐;一个人影从堂外一跃而入;一时顺着曲声急旋不停。烛火照耀下;她身上的蹀躞带随着转速快慢四下飞舞;裙袂纷飞流光溢彩;恰是让人目光流连不愿移开。尤其毫无准备的崔俭玄;一下子就被这突如其来的登场和胡旋舞姬给吸引住了。然而;当耳边传来了一声琵琶弦响时;他的注意力立刻移到了另一个方向;看清是杜士仪怡然自得地奏响了琵琶;他立刻愣住了。
杜十三娘只听杜士仪说今夜会安排些惊喜;可门上都没和她知会一声;这胡旋舞姬和外头那乐班便飘然而至;她心中一时又是惊讶又是懊恼。可那舞姬明眸皓齿笑意盈盈;舞姿又轻盈而俏丽;她不禁一边看;一边琢磨自己除了琴和琵琶;是不是也该去学些适合自己的舞。就在她那思绪飘飞到了极远处时;便只听外头传来了一个爽朗的笑声;直到这时候她方才恍然醒悟到;这曲乐和胡旋舞都已经停了。
“崔十一郎;要不是杜十九郎特意来求我帮个忙;这南市胡姬酒肆最有名的龟兹舞娘;可没那么容易请来”
姜度昂首登堂;身后随侍的两个婢女一个为他张罗坐具;一个在他面前安放了另一具食案;这才垂手退出。这时候;杜士仪方才举杯相敬道:“一时半会想不到别人;只能劳烦姜四郎了。谁让崔十一说闹别扭就闹别扭;我可不想好好的庆功宴突然变得没了气氛。”
“崔十一;你好福气。”见杜士仪先于为敬;姜度二话不说也斟满酒喝了个于净;这才看着崔俭玄道;“只不过你这县试既然考完了;马球赛这边你可缺席好几天了。窦十郎是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再这么下去这事情都快成我一个人的独角戏了”
“于就于;横竖八月才是府试;我又不用临时抱佛脚”
崔俭玄想起崔泰之对自己那不务正业的评价;心里就生气;当即重重一巴掌拍在食案上:“这两项赛事;预选都只剩下没两场了;即将进入了最jing彩纷呈的时候;但接下来天气太热;容易让人没有观赏的心情;再加上之前的预选场地太过逼仄;我之前让人在空地最多的南城宁人坊找到一块开阔的马球场;四周又有荫凉;正适合大量人流观战。明ri我们三个碰一下头;商议一下到时候拈阄等等
杜士仪见崔俭玄对姜度侃侃而谈;半点没有此前受挫的影子;他不禁暗自点头。一旁的杜十三娘自也是心中高兴;等见着崔俭玄一面喝酒;一面滔滔不绝说着心里那些打算;最后劲头和酒意全都上来了;突然兴致勃勃要下场舞剑;她更是连忙叫了婢女进来挪开食案腾出地方。当他仗剑摆开架势;突然翻动手腕舞将起来之际;她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一团渐渐凝练的银光。
而姜度却已经是从自己原本的位子上离开;悄悄紧挨着杜士仪坐了。见那边一双男女一个舞得淋漓尽致;一个看得眼露异彩;他不禁嘿然一笑;低声说道:“杜十九;那天端午节的风波你可还记得?人人都赞陛下宽仁;赐宫人于信臣;成就良缘;却不知道宫中因此而杖死了数人。据我从阿娘那里听到的;诗笺的字迹仿若皇后亲笔。”
尽管姜度没有明着说;但这已经相当于点破了。杜士仪怎都没想到事情竟然会这般奇峰迭起;暗叹幸好自己撇清得快。看了一眼一时剑势矫若游龙的崔俭玄;他便无奈苦笑道:“真没想到竟会如此复杂。那些诡谲多变的事情;能躲多远躲多远;姜四郎以为然否?”
“我就想躲;否则我怎会跟着崔十一郎捣鼓这马球赛?好歹比掺和宫中事情来得惬意。”姜度轻轻一耸肩;随即苦笑道;“可惜我家阿爷阿娘又不听我的。我就是提醒你一声;我只管及时行乐;ri子能过得轻松愉快就行了;可懒得掺和这些不说了;不能让崔十一郎这家伙专美于前;且看我和他同舞”
眼见姜度出去不知道打哪儿找来又一把剑器;与其说同舞;还不如说是下场和崔俭玄乒乒乓乓乱打一气;杜士仪不禁为之莞尔。
宦海无涯;处处风暴;可难得的却是他交了几个好友
第三百二十一章 纵横睥睨无敌手
唐人好名;官亦然;民亦然。
尽管天气已经ri渐炎热;但几乎都是平民百姓参加的大唐马球jing英赛仍然如火如荼。在如今这太阳底下满场飞奔打一场马球赛;一场终了汗湿重衣几乎是轻的;磕着碰着甚至于头破血流摔下马背全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可即便如此;一场比赛终了;胜者欢呼雀跃绕场一周接受观众的欢呼呐喊时;依旧全都神采飞扬;即便是那些败军之将;离场时会遗憾会沮丧;可谁也不会后悔大热天来这般挥汗如雨剧战一场。
预选赛全都是免费观战;一场比赛的观众从最初的几十人上百人到如今的一来便是成百上千;这也使得崔家窦家姜家三家派来维持秩序的家丁数量节节攀升;如今每一场都要动用七八十人维持秩序。因为是自家少主人的胡闹;家里又给了赏钱;尽管大热天还要应这种差事;可大多数家仆都还不觉得苦。至于冲着那足可让一家人十年八载衣食无忧的高额赏金;参赛者就更不会觉得辛苦了;而观战者们;能够看不要钱的热闹;谁也不会因为天热退缩。
由于洛阳地处东西两侧的中心;闻讯而来报名参赛的人形形sèsè;既有闲汉游侠儿;也有往昔的军中将卒;既有寒素之家爱好马术的子弟;也有常走西域商旅之家的佣工总而言之;形形sèsè的人汇集于此;往昔洛阳城中jing擅马球的那些游侠儿们;这一次也终于见识到了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此时此刻正是午后;恰逢最后一场预选;便是一场长安人对河北人的较量。
整备好了马匹;见其他人都扎好了护腿预备停当;关中所属的那一拨长安人中;一个面貌俊秀的年轻人就看向了身旁一个身长七尺的昂藏虬髯大汉。即便是在北地;此人的身量也显得极其扎眼;那双眼睛更是如同鹰隼一般。和别人的或紧张或兴奋不同;他的面上只有平平淡淡的表情;此刻也只是笑着说道:“照平ri那般上场就行了;不用多想。”
“楚大叔;这几个河北人下手极狠;其中一个号称黑金刚;上场的时候据说稍有不顺遂就下黑手;几场比赛已经重伤了三个人。因他们素来凶悍;又是柿子拣软的捏;裁判也多半向着他们;要是不预先提防”
“你只记得;鞠球多多传给我就行了。”虬髯大汉淡然一笑;面上满是自信之sè;“能冲撞我和旋风儿的人;还没生出来他们既是喜欢横冲直撞;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铁板”
听得他如此说;那年轻人顿时喜形于sè;但很快便露出了微妙的惭愧表情:“楚大叔;权大叔当初只不过举手之劳帮了你一把;如今你却为了我们这般尽心竭力;我实在心中惭愧”
“报令叔昔ri之恩是其一;二则是我正好囊中羞涩;来都来了;自当竭尽全力。”
虬髯大汉不以为意地阻止了年轻人继续提旧事;目光往对面一扫;见那些对手们已经雄赳赳气昂昂整装待发;他便扫了一眼那年轻人身后三个跃跃yu试的长安后生;露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笑容;“胜了这一场;接下来便是正赛;上吧”
这一ri既是午后比赛;此前还从未亲自临场观战的杜士仪便换了一身便服;只带了赤毕一个悄悄来到了这里。有钱能使鬼推磨;赤毕轻轻松松给他找到了一个有荫凉的好位置;再加上目力颇佳;他一眼就注意到了来自河北道那支队伍中的虬髯大汉。一来那魁梧雄壮的个头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二来则是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当此人上马之际;他注意到那匹坐骑亦是比寻常马匹高出了小半截;顿时惊叹不已。
“此人此马;在这场上恐怕没人挡得住”赤毕在马球场上也是一把好手;眼力自然比杜士仪更毒;这会儿少不得低声解释道;“这马通体漆黑;只看其驻马之时马蹄仍然时时刨地;就可见应该是从野马驯肝卩来的。在军阵中;这种坐骑兴许不适合;但若是单枪匹马两相厮杀;这等深具野xing的坐骑;便足可胜过那些圈养的马匹;人有气势;马有马势至于这虬髯大汉;但使有五分不逊sè于其坐骑的本事;这场比赛恐怕就是一边倒。”
“那我就看你的说法准与不准了。”
杜士仪欣然一笑;但只听场边铜钹乍响;两边人已经入了场。十人十马彼此相对行礼毕;随着场边裁判的喝令渐次勒马徐徐后退了四步远;就只听一声高喝;随着鞠球被高高抛起;两边各有两骑人如同闪电一般冲上前;竟是全都直奔那鞠球地的落点而去。
眼看其中最快的两人堪堪就要撞到一起的时候;那一马当先的虬髯大汉却是神乎其神地引马侧移了小小半步;就是这半步之差;他横着马头连人带马侧撞向了对手;随即看也不看那一匹把控不住去势;几乎一头歪倒在地的骏马;更没有分神去注意马上狼狈滚落下来的骑手;轻舒猿臂伸出鞠杖将那从高处下落的鞠球一挑。一瞬间;那涂成朱红的鞠球就在空中划出了另一个漂亮的弧线;径直冲着场中的同伴落了过去。
“好”
此起彼伏的喝彩声刚刚响起;杜士仪就只听得身边赤毕突然低低惊呼了一声。
他定睛看去;越过那追逐鞠球的两拨队伍;当即发现了那个坐骑倒地的骑手从地上爬起来之后;竟是猛然间弹地而起;抄起鞠杖往那虬髯大汉的坐骑马腹下直击而去。尽管这显然是违反规则的;可马球场上人仰马翻是普遍现象;只要裁判选择xing无视;旁人就是看见了也不能说什么;这下子连他的心都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虬髯大汉仿佛没瞧见;可他那坐骑却仿佛长了眼睛;就在那骑手连人带鞠杖从极其隐蔽的角度一击而至时;那匹高大见状的黑马突然前蹄猛然蹬地;竟是倏然腾空前跃;偏偏还在跃至最高点时猛然之间一尥后蹄;那坚实的马蹄就这么蹬在了那偷袭骑手的身上;把人重重蹬了出去。眼看着那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家伙如同破布袋似的重重掉在地上;杜士仪忍不住暗自惊心;竟有些感同身受的牙疼。
这一下偷鸡不成蚀把米还真的是不死都要去半条命
这边厢此人重伤落地;那边厢虬髯大汉一方的鞠球入门得分;先拔头筹;这大起大落几乎是不分先后。因而虬髯大汉那一方的四个年轻人欢呼雀跃庆贺的时候;他们的对手却是人人黑着一张脸。尽管他们有替补的人手;可当硬着头皮上场的那个人瞥了一眼半死不活被抬下去的同伴时;气势何止低落了三分。重新开球的时候;杜士仪就只见人人都小心翼翼躲着那虬髯大汉;结果便造成此人在场上左冲右突纵横睥睨;须臾又是连取两筹。
“到底你是行家;慧眼如炬。”杜士仪笑着对赤毕竖起了大拇指;这才又若有所思地说道;“都说燕赵多猛士;可今ri这虬髯大汉竟是一力降十会;把这些燕赵之士打得丢盔弃甲。就不知道此人究竟是为何下场竞技;倘若不是为了名利;那就有些令人好奇了。”
“郎君既然感兴趣;我就去打听打听。”
“你有把握?此人看样子;不是那么好相与的。”
赤毕却只是嘿然笑道:“问他恐怕问不出什么;可我看他那些同伴都不过寻常水准;看年纪更像是涉世未深。回头我就去打探打探。”
杜士仪虽这还是第一次来临场观战;但刘墨也好;赤毕也好;两人总是轮流前来“看热闹”;注意留心的人全都一一打听记录;然后设法招揽。其他看热闹的人都只追捧胜者;他们却对败者更感兴趣。之前一个多月下来;矮子里拔高子;查根底辨心xing;收纳进来的人已经有十几个;而这些人都送去了樊川杜宅;ri后另有安置之处。只不过今天这虬髯大汉如此鹤立鸡群;赤毕心中明白此人绝非等闲;要想招揽恐怕难如登天;因而这一趟答应去打探;纯粹是为了满足杜士仪的好奇心罢了。
这一场比赛的结果自然不言而喻;尽管是最后一场预选赛;但崔俭玄和窦锷姜度正在紧赶着商议新球场;谁都没来;因而看热闹的人虽则对那虬髯大汉津津乐道;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然而;当晚上打探消息回来的赤毕匆匆来到书斋的时候;面sè却远不如去打探消息时那么轻松。
“这虬髯大汉并不是长安人士;在参赛报名的时候;此人留下的名字是楚沉;公验过所上写的是河北人士;可我向洛阳南市的熟人打探过;谁也没听说过此人。而且;与他对阵的那伙人显然不知道他厉害;否则也不至于那么直接地碰撞败下阵来。除却这一点奇怪;更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