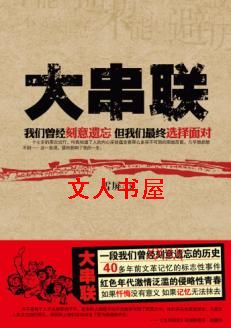死于青春 -海岩 著-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摆了一下手,“我不喝酒。”
“嘿,男子汉大丈夫,不喝酒?来来来,不喝不够意思,今儿嘿,我奉陪到底,咱们同醉!”
他皱着眉,他听不惯葛建元这种油里巴卿的腔调,可还是强迫自己用一种平淡的声音回答:
“我真不喝。”
“算了,表哥,喝个酒,干吗还求爷爷告奶奶的,他不喝你喝。”杜丽明看也不看他,在自己和葛建元面前各摆了一只杯子。“给我来点啤酒,一点啊。”
都落了座,葛建元高声劝菜,“来,吃吃吃。”并且率先大嚼大咽起来。
徐五四动作机械地夹起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却不辞其味。他把筷子放下,眼睛被迎面墙上挂着的一幅油画猛地刺了一下,那是个半躺在床上的全裸体的外国女人。这画和那些家具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极不高明的自制品。葛建元注意到他的视线,也扭过头来看了一眼,解释说:
“维纳斯。”
杜丽明说:“表哥,你一个大小伙子的卧室,单独挂上这么一张画,实在不好,快拿下来吧,我看着都难受。”
“世界名画,外面都有卖的”
“挂世界名画也得讲究场合环境,对不对?就冲你这猪窝似的地方,挂这画就不顺眼,听见没有,拿下来!”
徐五四却带着毫不信任的冷笑,问:“你怎么知道这是维纳斯,是你画的?”
“我哪儿有这个本事呀,是一个朋友画了送给我的。也他妈不白送,搓了我两顿饭呢,一顿新侨、一顿华都,操!也不便宜。
徐五四扭过脸对杜丽明说:“怪不得,这两年维纳斯见多了,可还没见过这么色相的维纳斯,原来出自这类手笔。”
杜丽明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犯牛脖子呢,所以没搭他的茬。葛建元很尴尬地哼哼两声,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肚量,“好好好,你们不乐意看,我拿下来。”他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起身把画摘了下来,反扣着靠在柜橱边上,然后解嘲地笑道:“咱那哥们儿是业余的,画得水平不高,水平不高。”拿菜刀来,该把鸭皮片下来了。”
“我这儿有刀,”葛建元从裤兜里掏出一只个儿不算小的弹簧刀,啪地打开,就用它来片鸭皮,油腻腻的鸭皮迎刃而落,看得出,那刀子是相当锋利的。徐五四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来,吃!”葛建元张张罗罗,片完鸭皮又把荷叶饼、葱、酱一劲往徐五四这边挪,“我专门挑了只大个儿的,一只就十五块六毛八,你们就甩开腮帮子吃吧!”
徐五四用荷叶饼包了一块鸭皮,很不是味的吃了。他只盼着
能早早地结束这顿令人尴尬的晚饭。看看葛建元,这家伙吃相很
粗,自斟自饮,兴致极高,把新开盖儿的一瓶竹叶青干下去一大
半,没一会儿功夫便酒酣耳热的有几分醉相了。
“嘿,”他摇晃着手里的酒杯,把一张通红的桔皮脸凑近五
四,“咱们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今儿我得好好谢谢你。”说完,
咕略,把酒吞下去,然后把光光的杯底儿亮给五四看,油嘴里还
打了一个异常响亮的酒嗝。
五四冷冷地说:“我不用你谢。”
徐五四身上象烧了火,象受了侮辱似的那么难受,难怪队里
的人们都知道他和葛建元的这层关系了,一定是居委会听了这小
子的胡吹,通过派出所反映到分局去的。这种无赖是什么话都吹
得出来的。他胸口上一下子凝聚起一团恶狠狠的反感和怨气,忍
不住把筷子往下一搭。
‘噶建元,我和丽明不是你那帮哥们儿,今天一块儿吃饭,
都正正经经说人话行不行?交朋友,可以,可就冲你这么一副腔
调,一来我交不起,二来,这话就难听了,你也不配!”
他正色直言,把葛建元弄得很狼狈,一脸僵笑,“五四儿,
干嘛呀,今儿可是我请你,别撕我脸呀。”不知是醉了还是火儿了,他的话直直抖。_
徐五四尽量让自己放得平静,说:“这顿饭,啊门也讲清楚,丽明事先没告诉我,我也没给你办事,没资格受请,该多少钱,我还你。”这么说了,他肚子里的怨气还是泄不出去,便又加了一句:“我是看在丽明的面上,才坐在这儿的。”
“你甭坐在这儿,你走呀,滚!”葛建元本来就不会有那种涵养,这一醉,再也顾不上装相了,脖子上红筋暴露,油乎乎的嘴巴咧着,“给你脸你不要脸,你当我待见你呀,你不就是分局的吗?老子行得正走得直的,不怵!你滚,滚蛋!”
徐五四激动起来厂‘告诉你,嘴巴可干净点。就冲你这样的,要是知道马有利那摩托车是偷来的,也会帮他藏起来,你会的!你这种人,有条件就会犯罪。”徐五四指指桌上的弹簧刀,又说:“公安局收缴凶器的通告看了没有,为什么不交?”
“我,我,”葛建元猛地站起来,把桌掀得沈咪响,一把抓过那把刀子,骂了一声:“我我找他妈宰了你!”
“你们要干什么?”杜丽明尖声大叫,从他们一吵起来,她的脸就是铁青的,不知是恨五四还是恨葛建元,端得话都快说不出来了。“你们还要动刀子,你们还要动刀子!”
徐五四压着火儿站起来,说了一句:“丽明,我在下面等你!”拉开门走出去了。
如果继续呆在那间屋子里,他不知道会怎么样,打起来?出人命?谁知道两个小伙子急了眼会干出什么事来!
站在楼门口,微微有凉风吹来,他张开嘴大吸了几口气,想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可胸口却激动得止不住略步地跳。周围很暗,很安静,也许是刚刚从一场暴风雨中走出来,过分的安静反而使人有点难耐。他拼命尖起耳朵,想捕捉从远处的马路上隐隐飘来的喧嚣声。现在几点了?
杜丽明很快从楼上下来了,看也不看他便去推自己的自行车。他也没急着说话,等他们默默地骑车转出了楼区,来到明亮的大马路上,他才讪讪地凑了上去。
“你这表哥,也太叫人看不惯了,和他在一起,我一分钟也忍木下去。”
壮丽明不说话。
“你生我气了吧?我这人就是脾气不好。”
杜丽明仍旧不说话,也不看他。他这时才感觉出事情有点严重,今天显然是过分伤了杜丽明了。可他匆忙间又不知道该找个什么词儿来弥补一下,挨着她默默地骑了一会儿车,快到十字路口了,才慢瞒着问:“咱们上哪儿?送你回家?”
这回壮丽明说话了,眼睛仍旧不看他。
“你走吧,以后别再来找我了,我受不了你这样的。”
胸口又跳起来,他辨不出她是赌气还是认真的。“你别生气了行不行,怪我不好行不行”过了十字路口,他仍然随着她,往她家的方向骑。
“你不用送我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也不是说你今天骂了我表哥,他现在这个样子,是该骂,我是说你这脾气,咱们俩不合适,真的不合适。”
她是认真的,冷静的,命令式的,毫无余地盼
徐五四的车子沉重地慢下来,呆呆地看着壮丽明一个人朝前骑去,越骑越远了。
他脑子里胡乱地闪过一个念头:
第八个是铜像
回家的路上起了大风,他推着自行车进院儿,地上呼地卷起一片土来,麻麻地扑了他一脸,啤!
小屋的窗户上, 渗着暗黄的灯光。 他的家,连灯光都是寒酸的。妈正在那片iCh巨昏欲睡的灯影下眯部又纫作, 天都这么确_了,妈真是一辈子吃苦受累的命。他没去帮她,进屋便径自走到自己的床边,很重地坐下来。
从他一进屋,妈就放下针线,目光随着他,看他坐下来一语不发,才忍不住问:“哪儿去啦?”
他一仰身躺下去了。
“嘿——,你这是怎么啦?连话都问不出来啦?大老晚的你上哪儿去啦?吃了没有?”“吃了。”他低声咕唱一句。
徐五四不想说话,他没一点心思说话,他需要安静,需要一个人静静地躺在这片暗影里,只有墙壁和他,把身心超脱到没有生命的冥冥世界中去,可是妈偏不让他安静,“你这是犯哪门牛脖子啊?”她索性走过来,一只热乎乎的手掌突然贴在了他冰凉的额头上,“病啦?还是跟丽明吵架啦?”
他还是一动不动,直到妈的手掌挪开了,才用低低的,仿佛是怕妈听见的声音说:“我们吹了。”
“啊?”妈嗓子眼儿里直哆噱,“你和丽明吹了?”她的声音忽然变得胆怯、小心,甚至还带着点拼命做出来的笑意。在这瞬间妈也许还指望他是穷极无聊逗闷子呢,可她马上就能从他鲜明的脸色上看出真情来。他一动不动,等着她的声调陡陡地拔起来,尖尖地吊上去,就象是眼盯着一个冒了烟儿的手榴弹,憋着气等着它炸开。
“你起来,你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真话?成心不叫我舒坦是怎么着,唆!”
妈妈的火儿一爆出来,他反倒松下气来,很快,所有的委屈、闷气,一下子顶到了舌尖.顶上了脑门,身子仿佛也不是自己的了,不知道怎么就虎虎地坐起来,破着嗓子喊了一声:
“你嚷嚷什么!”’
妈弄得一怔,立刻用嘶哑的声音拼命压过他:“养活你这么大,养活你这么大,你凭凭良心!”
他搞不清妈要说什么,可是看着那张哆哆噎喷的老脸,心忽地就软下来了,嘴里咕喀了一句:“有话说话,干嘛那么大脾气,又不是我乐意吹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说好,看我今儿跟你有好脸没有?”
“她,她,”五四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说得清,“她领我上葛建元那儿去了。”
“葛建元,她表哥!”
“表哥怕什么,又不是别的,嗅,含着跟你交了朋友,连表哥都不能见啦。”
“咳,跟您就扯不清楚嘛,葛建元是流氓。”
“你少摆臭谱,跟谁扯不清楚?丽明那孩子是学校老师,能跟流氓措葛吗?”
“他一身子流氓味儿,我是干什么的,还能看不出来?”
“就算是流氓,碍你们俩什么事啦?”
“我是干公安的,看不惯他那流氓劲儿,我教训他几句,嘿!壮丽明就要和我吹,吹就吹,跟葛建元搭亲戚,我心里还腻歪呢。”
“我是干公安的,眼里不愿意钻灰星儿,怎么啦?我就是没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习惯。”
“少跟妈摆臭谱, 你干公安的怎么啦,干公安的怎么啦,公 安局又不是和尚庙,想娶媳妇还不得将就点。”
索性,他一拉被子,仰天躺下去了。“我生不求人,死不求鬼,谁爱去谁去。”他说不清是委屈还是气愤。
她猛地掀开他的被子,抄起扫炕管帚,在他的肩头啪地一记,火辣辣的,“我叫你不去,我叫你不去,你当你是公安局的妈就不敢打你啦,没那门儿,看我今儿晚上能叫你舒坦了!”
又一记管帚疙瘩飞下来,五四一翻身下了床,抄手抓了一件衣服,往肩膀上一枪,话也不说,一摔门就跑出去了。他听见妈在他身后哆嚷发哑的声音:
“黑灯瞎火的,你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走!逼急了,我不回来!他心里直发狠。
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在街上走。顶着风。风,透过薄薄的衣服,一直把胸口吹得透凉。今年的五月真冷。唉,他这是干嘛呀!为了一个葛建元,得罪了凌队长,得罪了杜丽明,又得罪了妈。搞成了这么个里外不是人的德行,可知不知道自己倒底有什么错!
黑灯瞎火的,风又大,上哪儿去?火车站?
他一下子想起小时候到火车站“刷夜”的事儿了,嘴上想笑,鼻子却酸溜溜的。
那年,他刚刚上初一,十三岁,十三岁的人在家挨了打,已经懂得并且敢于跑出去“刷夜”了。
十三岁啊,青春少年!
可他的少年,哪儿有一点青春浪漫的味道啊,甚至连一点值得怀念和留恋的记忆也没给他留下。那时候,每天除了在学校里“复课闹革命”,应付两节“语录课”之外,大多数时间就是和那辆拣废纸的小车子做伴了。
现在思想。那意是主人简单的东尼,底下图木板拼.成三角,形,装上三个在杂货店里买来的大轴承当钻输,上面再架上只筐。这种小车子在当年北京城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成群结队时,小伙伴们一齐野腔无调地嘴哨着,能把车子蹬得哗哗地响彻一条街,倒也威风则个!直到七十年代以后,这栋废纸的大军才慢慢在城圈子里绝了迹,大街上再也听不见那震耳欲聋的轮箍声了。人们也许都忘了,当年拣废纸还真能算个生财之道呢,满街贴的大字报足有两寸厚,用小刀边戳边扯,一会就能扯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