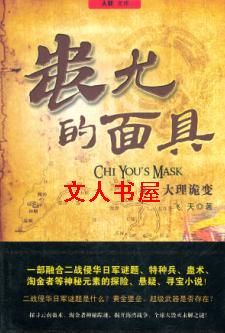蚩尤的面具-第1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师父,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一旦决定了某件事,就会一路走到底,绝对不会中途罢手。我愿意为他而死,就算牺牲自身的元神蛊救他,也心甘情愿。与此相比,做不做‘蛊圣女’都没什么意思,还比不上他的轻轻一笑。”又是一吻印下来,叶天想避开,但头颈、背脊、腰椎全都灌了铅一般沉重,扭曲不得,挪移不动。
“你——”女人的声音猛地提高,“我要你去大理,只是为了监视蝴蝶山庄与段承德,可你先招惹了司空摘星,又失足爱上叶天,浑然不管这些事有多麻烦、多头疼。莫邪,如果早知是这种结局,我真不该让你出山参与‘血咒’之事。唉,难道这就是我迫害蝴蝶山庄的报应吗?难道我要段承德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翻脸无情付出代价也做错了吗?”
莫邪握住了叶天的双手,不再出声,似乎那女人的话纯粹是自言自语,跟她毫不相干。
叶天无力地躺着,又过了几分钟,他忽然发现莫邪左掌心里发出一种灼热的力量,由自己的右掌、右腕、右臂、右肩输入,火辣辣的,一路烧向心房。同时,她的右掌心里则清清凉凉,并且产生了一种隐隐的吸力,仿佛要从自己身上吸走什么似的。
“莫邪,炼蛊师是不能动真情的,因为我们的灵魂已经献给了无所不在的蛊神,毕生忠实于蛊神,生死性命,都与蛊神联系在一起。一旦动情,就是自动毁诺,必将死得凄惨无比。现在收手,还来得及,结束了泸沽湖的事,我们就潜伏到苗疆最深处,再不回来——”女人的话没有说完,突然被一个小女孩的啼哭声打断。而小女孩只哭了半声,女人便发出一声尖锐的断喝,“神藏行止,三门禁闭,闻我号令,万事皆休!”
小女孩的哭声又被喝声截断,重新归于静默。
只凭半声号哭,叶天就辨别出了小女孩正是小彩。他瞬间就想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小彩被送回了蝴蝶山庄,但遭受重创的段承德自顾不暇,哪里有余力保护小彩?于是,最终被莫邪和那女人乘机出手,掳到泸沽湖来。那女人不会是别人,肯定就是与段承德在男女之情上纠缠不清的苗疆大炼蛊师孔雀。
“我……”叶天聚集全身气力,猛地睁开眼,并拧腰发力,半坐起来,然后开口大叫,“小彩,你在哪里?不要怕……”
嗖地一声,有人飞掠过来,将一柄明晃晃的银钩送入叶天嘴里,一沉一提,伴着一声低叫:“好,攻入肺部的蛊虫解决了!”
叶天等银钩撤出,喉结一动,便察觉满嘴都是涩涩的血腥气。
“莫邪,盘踞在他心脏上的那条虫,普通方式已经无法驱逐,只能用血脉代换法引它出来。我担心的是,叶天的身体异变后,血液也会产生质变,流入你的体内,总是不妥。”提着银钩的女人站在叶天的另一侧,那只尾端分为三叉倒须钩的半寸长银钩上,挂着一条仅有一厘米长的豆沙色小虫,兀自摇头摆尾,挣扎不休。小虫身上悬着一滴紫黑色的血珠,不知是属于叶天还是它的。
那女人披着一件雪白色的斗篷,夜风吹拂,斗篷半卷,瘦削身材半藏半露。她的五官线条尤其柔美而纤细,特别是那双秋水般盈盈润润的眼睛,似会传情说话一般,比双十年华的小女孩更容易勾起男人的相思。
“师父,为了他,我愿意冒这个险。不要说是有什么‘不妥’了,我早说过,就算用自己的命去换他的命,我也心甘情愿。”半跪在叶天身侧的莫邪喘息着说。
她那张美丽而年轻的脸与叶天的脸靠得极近,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叶天,既不避讳,也不怕羞。她说这些感情炽热的话的时候,嘴里呵出的热气直扑在叶天额上,苗女之热情,一至于斯。
第08章 以命换命
叶天与莫邪之间本是敌人,因为他是段承德的朋友,而段承德则饱受孔雀发出的“血咒”之苦。如果不是为了对付血咒,叶天甚至不会到大理去,更不会辗转赶来泸沽湖畔。阴差阳错,莫邪却爱上了他,而且一往情深,九死无悔。
“莫邪,你不要只凭一时冲动行事,所有的汉人……汉人都是靠不住的,前车之鉴,你还没看明白吗?”那女人凝视着银钩尖上挣扎的小虫,心事重重、无限感慨地低语,“多年以前,我曾是最有前途的苗疆大炼蛊师孔雀,但现在的我已经被段承德伤透了心,一生都已经被这件事彻底改变。所以,我多么想让你明白,汉人是不值得相信的,他们与苗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叶天也黯然苦笑:“莫邪小姐,千万别为我做傻事,那么重的人情,我是还不起的。”他从来都是秉承“人予我一尺、我还人一丈”的处世格言,一旦别人为他做过什么,他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假若莫邪以命抵命救他,他就算粉身碎骨也难回报对方。
“是吗?但我真的已经决定了。”莫邪微笑着,左掌持续发力,令叶天全身的血脉都在震颤着。
风中传来淡淡的草香,没有人再关注时间的流逝,而是共同面对着这道难解的连环谜题。
叶天感到自己的左胸正在隐隐作痛,可惜此地没有日本人的扫描仪器,无法观察他身体内部的状况。
啪地一声,孔雀揿亮了一支笔形的强光手电筒,用左手指尖翻开叶天的眼皮,仔细地向眼底照着。白光刺眼,叶天的眼角立刻涌出咸涩的泪水,胸口疼痛也骤然加剧。
孔雀轻声叹息:“莫邪,我觉得你最好能停止救援工作,因为他心脏旁边潜伏的那条蛊虫是——”
莫邪笑起来,笑声中饱含着成年人一样的沧桑愁郁:“我知道,那是牛头马面降,苗疆最丑陋、最阴毒的降头术。要破解它,就必须找到替代的寄生体,而且所选的寄生体必须是具有相当功力的炼蛊师。苗疆之大,想找出一名舍己救人的炼蛊师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炼蛊师一入师门,学习的第一课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师父,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选择有多傻,但我还是选了,毫无怨言。”
孔雀忽然怔住,电筒光柱落在叶天左胸上,指尖弹出一柄银背小刀,哧哧两声,在光柱落点的衣服上划出一道十字缺口。那两刀的力度用得异常巧妙,只破衣,不伤身。然后,她用刀尖挑开衣服,令叶天的胸膛赤裸着。
灯光下,叶天的左乳右下方一寸处,有一枚红点正在突突跳动,如同热锅上的一粒红豆。
“师父,帮我。”莫邪说。
孔雀倒吸了一口凉气,冷冷地反问:“帮你?莫邪,你一定知道牛头马面降一旦发作,将是什么结局?帮你即是害你,我是你师父,怎么能做那种事?”
光柱阴影中,莫邪的脸色变得无限苍白,如一张被水濡湿的纯净白纸。
“我知道。”叶天苦笑着接过话题。
孔雀摇摇头,感慨万千地低语:“不,你不知道,只有真正被这种下三滥的降头术伤害过的人,才会明白,牛头马面降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生不如死。你们还年轻,体会不到男女之间最复杂的情感。莫邪,这次你真的错了,如果还能自控,就听我的话,赶紧罢手吧!”
她是一个很美的女人,这一刻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极度悲哀,令她的五官微微扭曲,就像一朵被流逝的时光摧折了的凌霄花,带着让人惋惜、唏嘘、感伤的残缺之美。
叶天瞥见她那张脸的时候,忍不住想:“段承德不该因她犯错,但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面对她时,最应该做的,也许就是宁可犯错,不可错过。”
“我美吗?”孔雀问。
叶天下意识地点头,因为这个问题无需考虑,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她呢?”孔雀又问。电筒一转,光柱落在莫邪的印堂正中。
莫邪当然很美,眉目之间,带着一种野性、冷傲、不羁的气势,像一株由苗疆广袤的黑山白水培育出来的野百合。
“她很美。”叶天已经意识到孔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果然,孔雀接下来关掉电筒,用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凄凉语调说:“一旦牛头马面降在她体内爆发,她的样子就会发生彻底改变,由美的极端跌向丑的极端。这种降头术为什么要用‘牛头马面’命名?是因为彼时的她,将变得比黄泉路上拘魂索命的两大阴差牛头、马面更可怖。没有人能忍受这种变化,即使是心理能力超强的男人,都会看一眼吐一次,直到连胆汁都吐净。唉……”
她不想再说下去,用一声长叹结尾。
叶天明白“牛头马面降”的威力,也知道,如果解除不掉这种降头术,他自己就将变得丑陋到极点,并且永远无法逆向恢复。
夜色中,一只栖鸦骤然飞起,呱呱怪叫着,俯冲向另一处更茂密的草地。
叶天咬了咬牙:“莫邪,假如蛊虫进入你体内,发作后的结果也……一定不会例外……”太深的苦涩胶着住了他的唇舌,说到最后几个字,喉头竟变得哽咽起来。
一个男人对自己容貌变化还能忍受,但像莫邪那样的美女,哪怕脸上出现一点小小的瑕疵都会懊恨不已,更何况是变为牛头马面一样的人间怪物?
“比死更可怕的结局……那一定是比死更可怕的结局!”叶天喃喃地说了同样的两句话。前一句,指的是莫邪自己无法承受牛头马面降带来的畸变;后一句,则是叶天无法面对莫邪的畸变过程。
“没错,那的确是比死更可怕的结局,尤其是对于一个爱美的女孩子来说。”孔雀涩声笑起来。
黑暗中,她的眼神灼灼闪动着,盯住叶天的脸。
莫邪幽幽地插嘴进来:“牛头马面降之变,比死更可怕,但有些感情,却比生命都重要。师父,潜入大理之后,我一直有句话想问您——‘您后悔过吗’?”
“后悔什么?”孔雀明知故问,借着夜色掩饰自己的不安。
“段承德欺骗了您的感情,明明有妻子、儿女,他也明知不能舍弃家庭,却对您虚情假意,终于导致了您失去问鼎‘蛊术之王’的机会。您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要把这种伤害十倍返还于蝴蝶山庄。对于这一切,您后悔过吗?如果时光倒流,回到您结识段承德之前,您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莫邪的语调过于平静,令叶天心里也惴惴不安起来。
他的左胸胀痛难忍,那恐怖的小虫既像一块火炭在灼烧,又像一柄小刀在剜割,或者更像是一台专门攻击神经的电钻,间歇性地、不屈不挠地在他体内钻探着。于是,他的脉搏忽快忽慢,忽强忽弱,连喘息也变得急促且困难。如果是在香港或其它有足够医疗条件的大城市里,他会立刻选择入院开刀,把那小虫取出来,以绝后患。可是,此刻是在泸沽湖北的荒山野岭之中,即便是最近的大医院也有三百公里之遥。
“我后悔吗?我应该后悔吗?”孔雀仰起脸,轮廓美好的下巴斜指向远方的群山。忽然间,有两行泪从她的眼角跌落,晶莹如同草叶深处的夜露。
“如果后悔,我何不直接奔袭蝴蝶山庄,撒下‘灭门绝户蛊’,将段氏一族全部绞杀,一个不留?”她转过头,望着草丛中蜷缩着的小女孩段小彩。
小彩的手腕、脚腕被分别绑住,嘴原先是被胶带纸封住的,此时半边脱落,她刚刚才能哭出声来。她一定很害怕,全身紧缩着,仿佛要将小小的身体缩到地底去,直到别人看不见为止。
“如果我不后悔,又为什么连续布下‘血咒’,让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也许我只是想用这种步步紧逼的手法,要他回心转意。可是,越逼得紧,他就越拼尽全力保护家人,越把我当成敌人……”孔雀冷笑着甩头,顺带将余泪甩干。
“不要伤害她,上一代的恩怨,不要让无辜的小孩子去承担。”叶天淡淡地说。他曾答应段承德,要保护小彩,只要自己一天不死,这承纳就一天有效。
孔雀摇摇头,从齿缝里慢慢地迸出一句话:“只要能给段承德带来幸福感的人,都是我的敌人。她是小孩子,但她却分走了本该属于我的感情。你说,她是不是该死?”
叶天哼了一声,不想再辩论下去,因为孔雀在这件事上已经钻进了牛角尖。无论别人怎么说,她都充耳不闻,只想让段承德失去一切,付出代价。
“可是,你还是爱他的。没有爱,就没有恨。爱至深,恨至痛。师父,我现在要走的,是跟你当年相同的一条路,但结局是完全不同的。我替他解蛊,不求任何回报,可他也许会因此而铭记我一辈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心底最火热处,给我留一个小小的位置。我就像这条小虫,潜伏在他心脏的最安稳处……”莫邪把叶天轻轻按倒,靠近她的胸膛,盯着那块红斑,毅然决然地再次请求,“师父,帮我,我一定要救他。”
她的头发触到了叶天的身体,微凉而光滑,如一匹精工细纺的丝缎,带着来源于大自然的原野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