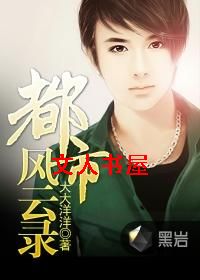故宫尘梦录-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静江同李石曾自然都不去,老西也知难而退。张继如愿以偿,他正位了。
在他正位的一天,阎老西是监誓,我也去参加典礼,他左右挥拳式真像狗熊地在演讲:我只听见他说:“那共产党,左边腰上挂了父亲的头颅,右边挂了母亲的脑袋,以为荣耀,简直是禽兽不如!”
老西儿带着瓜皮帽,垂下眼睛不则一声,正是强烈的对照。然而北平是阎家的势力圈,楚溪春做宪兵司令,派了四名卫队随侍张主席,这四名卫队是左右不离主席的。
一日,主席公毕回府了,卫队方才到门房休息。主席从容进了厅房,忽然大声由厅房传出,卫队大惊,一齐冲进房去。这一冲进退不得,只见那主席矮了半段,原来跪倒尘埃,男儿膝下没有黄金了!那崔氏夫人却颤巍巍手执“惊堂木”立在案前大声呼喝着。那卫队惊惶失措,其中有一个最机警的,他也只得参加礼拜,也跪下了,于是其余的下等黄金一概放弃都跟着屈膝。
张继听得背后有声,急急回过头来,双手乱摆,还是跪着发下主席的命令说:“这不与你们的事。快去!快去!”
他们只有服从退出,第二天却打了一个报告给楚溪春司令,于是这佳话传遍了故都,张主席的治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自农本局 易寅村死沪(2)
张继先生“博雅而好古”,读书虽不求甚解,却喜摩挲善本,手不释卷,借了一部国学大师王国维手批的《水经注》孤本来润饰书房,一天,又以伺候不周得罪了莺莺太太,太太却要他的好看,拿起这本孤本《水经注》做了一次焚书的“秦始皇”,于是几乎坑死这位“沧州大儒”。
由于张太太崔振华脾气太坏,对黄大伟日常颇不尊重,黄自然对她甚为反感,他自告奋勇替我探听他们对我以后的动作。他告诉过我说:崔振华曾经向他提及,说:我知道吴某已经在南京,现在顾不上,找机会再制他。
我在农本局不到一年,易寅村在上海因为积愤,新旧病同发,我的女儿写信告诉我:医生己宣布了最后的月日,我赶到上海去探视,景况甚为凄凉他自己还不大知道,还希望有政治解决的一天。我知道无望了。
我做为他的同窗,老秘书,替他预备撰写了一个遗呈稿交给我的女儿,隐忍着悲痛回到南京,吩咐女儿到必要时将这稿给他看一下。以后不久,上海发动了中日之战,京沪不能通行,我不能再去看他,我们从此长别了。他死的时节,料理他身后的友人,是两个吴姓:一个是吴稚晖,一个是我的女儿吴珊,在上海做药剂师了。
据我所知,当年他所信任的旧部,包括马衡一班人,及北大系的朋友们,没有再去看他。最令人不解的是,李玄伯也因怕事,而未出席最后的送葬。人情淡薄,一至于此。外人也就算了,我对这位晚辈,李玄伯是不能原谅,必须批评的。盗宝大案由他而起,祸延其岳父,他却竟是如此的没出息,如此的不尽人情。?
战事吃紧南京震动了,各机关都在准备撤退。我代拟的遗呈经我女儿吴珊在易培基最后的时刻交与他本人看过,又经吴稚晖审定。其词云:
窃培基自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十有余年,自我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仰荷不弃菲材,承乏农矿,■又兼长故宫博物院事。二十年“九一八”之役,日寇凭陵,侵及华北,以二千年文物沉沦堪震,因倡南迁之议。幸赖德威,及中央诸同志之赞助,力排万难,于以完成,不敢言功,自问可告无罪。事实俱在,可以复按。乃以处世无方,契友隙末,至■莫须有之狱。复以多病之身,不堪囹圄之辱。未能立时到案。始意养息待时,以求昭雪;不谓忧愤交侵,竟玉■■!迩来暴敌侵及腹地,国难日深。培基卧病江滨,亲闻鼓角之声,报国有心,抚膺增痛!此生已矣!深知我公领导国人,振奋抗敌,正国家复兴之会。则培基亦当含笑九泉,自无遗憾可言。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含无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月既极!垂死之言,伏乞鉴察。谨呈国府主席行政院院长。易培基遗呈。
他身后的情形相当惨,留下了一个老妻,典型的旧式老太太,什么也没有了;惟一的女儿,就是李玄伯的夫人了。没有儿子,拿他令兄一个外室所出的儿,留养着预备作为继嗣,此时不长进地日趋下流,声明脱离了关系,当时在中国殡仪馆成殓,在战时乱世的状况下,只有上面所说的两个人以朋友的立场照料着,也不能追悼。法院方面还派人去调查说是假死,一面在报纸上宣传,说是逃亡到大连与满洲国投降日本人了。
我在南京替他递上了遗呈之后,亲访张群说法请求国府明令褒恤,照他的地位是应该的。
“关于故宫案子如何办呢?”张群问我,并对我如此仗义为朋友的作法,甚为惊讶和尊敬,从此更生好感。
“政府可以有两种办法,”我说,“积极呢,可以昭雪。消极呢,可以不提,他在地位上是应该有一明令的。法院并未有结果,政府当然可以不管。”
张岳军于经过内容,是相当清楚,他答应明天约集翁文灏等大家商量。那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魏道明,他同易寅村据说有点宿嫌。
这班朋友,对于一个政治上失风倒下去的人,在“捧生不捧死”的原则下当然不理会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自农本局 易寅村死沪(3)
我当时因为他们对于一个已经因被迫害而至死亡的朋友,即在帝王时代也有给予礼遇的优典,现在竟然是这样予以难堪。真乃令人气吞不下。
我再将遗呈稿寄与吴稚晖过目的信中,发表了对张继讨公道的意见,他复我一信,表示他的意见,如下:
景洲先生执事:由令爱转到赐书,敬悉一切。鹿山先生辞世,不欲其隐没无闻,无以折提包上何处等之口,故即登报声明,当时未想及正式报告公家,其身分虽不希望现今即有明令追悼等之典礼,然说明不能到案,抱憾逐殒之痛,不可不正式布达也。幸先生想到,遗呈且措词悃悃款款,十分惬当,已嘱漱君急缮,直邮行院矣。至于旁人再助说,揣尊意:欲趁此不但为逝者雪憾,且欲为生者缓狱,故有亮聪如何交好,对方将不反对之乐观。然鄙■所及,今非其时。(从前终不得时,今且倍其难也。虽有逝者可原之揣测,恐只据一面,未及想到面面。)因亮聪交好如何,毫不相干,亮则彻底明了沉冤,从前屡嘱想法,彼徒唤奈何,聪自更加明白,然当郑女狱尚急之时,彼恐亮顾此失彼,曾明拒对亮晓晓,此亦非彼之不够交情,实知此狱与金郑皆异,即彼案皆无对方之为难,而此案则“此直矣,彼即曲。”受曲者岂肯默尔。又彼案舆情之惶惑,不如此案之甚,若麻乎而罢,必舆论大■,狗党不平。故此案非公庭明判曲直,不呈雪此沉冤。明判曲直,可有十分把握,因隐微实清白也。然非三番四复,大吹大擂,无从能得究竟,而此大吹大擂,为在最高当局宴然无事,坐听羊咬狗、狗咬羊之时。从前之屡不得时,皆因投鼠忌器,令更国难如此严重,忽歆夹此小事大吹大擂,群情之所不许,即当道之所未乐。故曰仍非其时,且更加甚,因先生所谓“奉”者,彼实超然,然因政治作用之变化,常或左或右,彼有闲情之时,任大吹大擂之起,可以含笑闲观。若碍其安静则必厌恶隐生矣。因彼隐徽之地,实未相信完全冤诬,歆彼晓然于完全冤诬,非有数万字之说明,证据罗列,不为功,彼有暇读数万字,且看错杂之证据乎?弟前年入川,歆试之矣。乃见日无暇晷,得半小时之长谈,不可得也。又歆试其左右,有可代为细谈者,试探未得其人,皆入一般盲说:以为如此,固当相见法庭,何必求助于大力?其距人千里外之空气,即六无庸尝试,因而因循至今。弟信我所谓数万字之经过,与坚强之证据,不但可解一时之惑,且可告天下后世,然而必大吹大擂,相见法庭后,才众喙毕息。否则如当日鸣冤监会等,皆不足以释舆情,若三水公(汪精卫)如何可助,大电公(蔡孑民)如何中裁,亮聪如何助力,“奉”将如何麻■,皆拙劣自秽之下策也。此案岂金郑之比乎?若云大力若“奉”者,一左右,狱可以缓,此更误见,“奉”即不深信此地果然无银三十两,然彼六不歆厚左,亦不歆厚右,狱缓,早缓矣。并未急捕,即如郑者,自由虽得,案并未了。故鹿不能古拔(上海古拔路,易时居此)为深山以待时,徒抑抑以促其生。则生者今亦鸿飞冥冥,何羡于大力之佑(生者,指李玄伯),为低头之自由。姑待之,不必在婆婆正不欢之时,再向婆婆拖鼻涕(至于遗呈,乃名正言顺,自当别论),故弟数万言之准备,要据之清理,必使可告天下后世,并可大吹大擂,大吹大擂之必当经过,乃不但个人之清白存在,即世上之是非亦明,昔日鹿之有所顾忌,决非珠玉有所歉然,乃牵涉古林等恐结果大冤既白,而风流小过,或当上身(此节古林云云,我亦不明所指),此妇对沈宜甲,亦用此法,所以至今尚沈粤狱者,偶女之事,不成为罪而代交通部发明,领款万元,无报销,即不自由矣(详见附录)。
然此自由,万万胜乞大力者,大力者无所左右,固显然也。今日大吹大擂,既不合时宜,歆大力者左右抑左,亦非所能,何必为空费笔墨之蛇足,且钮惕老来言,谈三分钟话,尚抽不出,能看不急数万字之鸣冤耶?至于遗呈达院,乃正式公事,必当伏报而已。万万不想能入“奉”目也。乞台裁。即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十月三日
他这封信内,强调着说似乎我要求“缓狱”,这是不可解的。我的原信虽然不记得了,但是易寅村已死,我那时并不在狱内,为什么要求缓狱呢?显然是说玄伯,我一向是要反攻,绝没有“缓”的意念。若不是他个人的误会或者是李玄伯有此要求吧?“古林”云云,我至今不解,也忘记问他。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从八十八军到国防最高委员会
我有一个老友忽然在重庆相遇,因为刘湘的四位大将之一的范绍增将军要组织88军,他介绍我到他的军幕,于是在抗日之大时代,我从戎了。范绍增是一位草莽英雄而成为川中有名的将领,他因为最早倾向国民党中央而被刘湘所摈弃,为王绩绪、潘文华、唐式遵三个将领所排挤成了光杆。现在中央军入川,他理应复活。因此成立了88军。当时主持中央军事的是何应钦。
范绍增对于我,因为由中央而来,谬诧虚声,于是他在编制以外,给我加了一个秘书长的名目。我在众川人之中,终日吟诗写字作画,居然在此战乱之时创作了一大批自问尚属可取的作品,真乃平生之快不亦乐乎。
吴稚晖说:“你吃了文人的亏,换着同一个武人混。入蜀在乱世,交结一个川人也好。”
1939年88军出发到第三战区上饶,我被留在重庆留守。那时家眷因为避免空袭,到江安去了。我更无所事事,只好也回到江安,有一群亲友去游峨眉,我也同了内子参加,船到乐山,遇到乐山到峨眉一带的日寇飞机大空袭,船停在江边5天进退不得,方才换了一条船回来,几乎还在川江观音滩覆舟送命,涉险回到江安。
忽然接到88军参谋长刘展绪的来电,转达范绍增的意思:屯溪并无兵事,约我去游黄山。
张群此时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了,我去向他辞行。他忽然对我说:“你不要走吧!在此帮我的忙如何?”我自然答应了,他立刻发表我任参议,正是1939年的双十节。我电辞了88军的任务。
这样,我又留在重庆了,又常常遇见张继,虽面和心不和,却仍旧点头招呼,尤其是每次出席中央纪念周,一定要见面,他奈何我不得,倒也相安无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1)
我在重庆时,马衡来渝了,听说故宫博物院运出来的文物,分别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庆、乐山、峨眉等处。当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览的一批,以及张岳军帮忙运出的一部分,此外遗留在北平的全部、以及南京库房没有抢出的都听之任之了。我是比较知道的。而他们的个中人告诉我说,除去文献馆小部分外,都出来了。
马衡一到重庆,不知如何打听得我的住址,来至圣宫造访,他固然好意,我却因故宫是非谢绝了他。后来,他又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