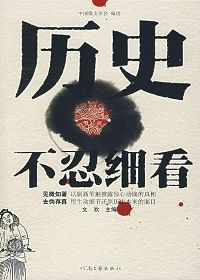历史选择了毛泽-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开口数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罗亦农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作为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指导,这是很对的。任弼时说得更直截了当:
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任弼时所说的“老头子”,指的是陈独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这样,工人出身的工人领袖们,一下子备受重视,被列入中共新领导班子的候选名单。内中有:四十二岁的苏兆征,他是广东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人,从小在海轮上做工,地道的海员工人出身。一九二二年一月,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三月,创立中华海员联合总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另一名受到青睐的是二十三岁的顾顺章,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还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八岁的向忠发,湖北汉川人。论出身,此人“根子正”,“标准”的工人。他青年时期先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后来做过水手、码头工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担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历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他当选过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于是,罗明纳兹拿出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他念道:“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七人”,“正式委员七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七人——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随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名单。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跟瞿秋白预拟的人选颇多差别。根据会议记录,最后的名单连同得票数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二十票)、向忠发(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罗亦农(十八票)、顾顺章(十七票)、王荷波(十七票)、李维汉(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时(十四票);
候补委员——邓中夏(十三票)、周恩来(十二票)、毛泽东(十二票)、彭公达(十一票)、张太雷(十一票)、张国焘(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数颇为耐人寻味。由于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强调了工人成分,苏兆征、向忠发一下子得了全票(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没有参加投票,所以实际参加选举的是二十人),超过了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产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票数居末,全成了候补委员!
毛泽东的得票数与周恩来相同,并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数,中央的新领袖当是苏兆征或向忠发。
对此,罗明纳兹作了如下说明:
至于指导(即领导——引者注)成分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做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指总书记——引者注)。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调查一下他是否能执行此新政策。
这样,在八月九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为中共新领袖。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为首。
从五月九日中共“五大”闭幕式到八月九日,正好三个月。这三个月来常委名单的三变,足见中共领导核心的大变动:
五月九日,三常委即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七月十二日,五常委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七月二十一日增加瞿秋白);
八月九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在三变中唯一不变的是李维汉,一直担任常委。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路线,并载入了史册。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四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如今,召开八七会议的那幢房子设立为纪念馆,坐落在汉口鄱阳街一三九号(即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那是根据李维汉、邓小平、陆定一认定后确证的。不过,一九八三年郑超麟应邀去武汉时,却认定鄱阳街的一二三号是原会址。那座房子跟一三九号的模样很像。郑超麟的记忆力向来是很不错的。只是他的意见未被接受。
在八七会议的记录中,任弼时曾说过一句话:“老头子可去莫。”“老头子”陈独秀后来没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郑超麟等组织了党内反对派,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任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此后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矫枉容易过正。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后,中共开始由右朝“左”偏航。作为三常委之一的李维汉,晚年写下《回忆与研究》一书,很深刻地道出当年批右出“左”的原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滋长起来。
除了这种“左”倾情绪,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的动力。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
二十八岁的瞿秋白上台之后,深感共产党在武汉的基础太差,便于九月底和郑超麟一起坐长江轮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隐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里。从此,中共中央也随瞿秋白迁回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阴影,依然浓重地笼罩着上海。处处谈“共”色变。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里“扫描”,巴不得盯住每一个“赤色人物”。
这时全国中共党员锐减,从中共“五大”时的近六万人,一下子直线下降到一万多人。心急如焚的瞿秋白,却这样深信不疑:“在较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瞿秋白要在中国点起暴动之火。他的头脑在膨胀,在发热,急于求胜的情绪在迅速滋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他的“左”倾路线。
会议作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样,瞿秋白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上去。当然,最激烈地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难怪他来华时,带来了德国的“暴动专家”纽曼。
这次扩大会议,增选了两名政治局常委,即罗亦农和周恩来,使三常委增至五常委。这样,周恩来又重新进入了常委之列。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败:
武汉暴动——原定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八时武汉三镇工人总罢工,举行暴动,进攻友益街,结果因响应者寥寥而作罢。长沙暴动——十二月十日晚七时,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二百人敢死队举行暴动,企图占领长沙。敌人连夜调来一个师,一下子就把暴动镇压下去了。
广州暴动(广州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等领导下,举行广州暴动。暴动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当场牺牲。暴动也迅即失败。此外,上海暴动、天津暴动、唐山暴动也都惨遭败北。
暴动的一次次惨败,使新上台的中共领袖瞿秋白威信扫地,陷入了困境。看来,他在领袖的座椅上席不暇暖,就得另易他人了
谁将替换瞿秋白呢?
一个出乎意料的机遇,使一个并不具备领袖才华的人物,成了中共正儿八经的总书记! 那是八七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忽地发来通知: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即将到来。一九二七年的十月革命节非同往常,乃是十年大庆,各国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团。这样,中国共产党也要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庆贺。为了表示对工农干部的重视,此次所派的是“中国工农代表团”。由谁率领呢?自然应当派工农出身的干部。
最合适的人选,应是苏兆征。他是政治局常委,又是工人出身。不巧,他正生病,不能远行。于是,选中了向忠发。在八七会议上,他跟苏兆征一样,都得了全票。另外,还指派了李震瀛作为向忠发的副手。李震瀛又名李宝森,天津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工人运动。他在一九二二年领导了郑州铁路工人大罢工,出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一九二五年在上海领导“五卅运动”。后来,又成为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七会议时,他是与会者之一。后来李震瀛参加罗章龙派,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此后他在上海被捕,发表声明不再参加革命活动。获释后在天津敦庆隆绸缎庄当店员,后来下落不明。历史把机遇给了向忠发。他和李震瀛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来到了莫斯科,这是他头一回出国,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共产国际的高层领导。这时,共产国际恰巧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以担任中共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这位四十八岁的老工人,正符合共产国际的需要!
这样,当向忠发和李震瀛在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盛典之后,共产国际为了对其加以培养,又派他们前往德国和比利时,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向忠发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报告,并与德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另外,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之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共产国际的着意培养,使向忠发大长见识。
就在向忠发和李震瀛结束了欧洲之行时,他们又应邀前往莫斯科,出席重要的会议——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至二十五日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在那里举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那时,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革命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是瞿秋白的“后台”——罗明纳
兹,他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夺取政权,实现一省数省乃至全国胜利的时候了”!正因为这样,他主张不断地在中国组织暴动。瞿秋白忠实地执行了这位共产国际驻华全权代表的指示。另一派则以米夫为首,他们激烈地批评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米夫在《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八年,第四期。一文中,批评罗明纳兹:“中国资产阶级不算作一种政治力量,这样他就犯了一个错误,轻视中国目前革命斗争的一切困难。”罗明纳兹反唇相讥,嘲笑米夫右倾。
瞿秋白组织的一系列暴动的失败,特别是广州暴动的失败,使罗明纳兹面临被“查办”的危险。虽然他在一九二七年底已回到莫斯科,但还一再鼓吹他的主张。不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都否定了罗明纳兹,批评了他的极“左”主张。斯大林、布哈林会见了向忠发、李震瀛,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由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通过。这个决议案否定了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