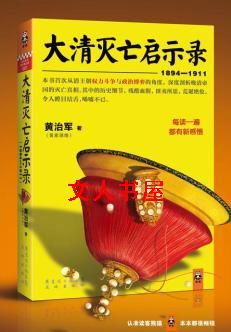18岁给我一个姑娘-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屋的门接着老流氓孔建国哥哥嫂子的房间,从外面无法进去。小屋有一个窗户冲外,透出里面亮的灯光。我走到窗户下面,本来想喊老流氓孔建国的名字,把他叫出来,一起去“大黑洞”抽烟,但是仿佛听见屋子里面有轻微的响动,没喊出声。关于老流氓孔建国的个人生活有各种传说。他还说,根据定义,流氓首先是和妇女联系在一起,否则不能叫流氓。打架再凶也不能授予流氓的称号,只能叫地痞。张国栋从小近视,带个眼镜,严肃起来,论证严谨,有说服力。但是张国栋也不知道老流氓孔建国的婆子是谁。
好奇心上来,我胡乱找来几块砖头,摞在小屋窗户的下面。我站上砖头堆,手扒着窗台,一手的灰土,晃晃悠悠,慢慢直起腰。
屋里只有老流氓孔建国一个人,他斜躺在床上,上身穿了个白色跨栏背心,背心上四个红字“青年标兵”,下身赤裸,露出他的鸡毛信。他一手拿了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一手抓着他的鸡毛信。眼睛一边盯着那本杂志,手一边不停搓动。
我转身要跑,屋里传出老流氓孔建国的声音:“秋水,你站那儿别动,等我出去。”
老流氓孔建国晃荡出来,手里拿着那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我瞟了一眼,肉晃晃的满是光了屁股的国民党女特务。老流氓孔建国把杂志塞在我手里,说道:“尿满则流,精满则溢,尿满了上厕所,精满了打手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要大惊小怪,没有教养的样子。”
我再也没有梦见过大车、二车,朱裳的妈妈也没再派其他什么女流氓钻进我的被窝,黑夜不存在,天总是蓝蓝的。
老流氓孔建国说朱裳的妈妈就是他的绝代尤物,他愿意为她赴汤蹈火。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望虚空,我已经见过朱裳的妈妈和朱裳,我没觉得老流氓孔建国事儿逼。我给老流氓孔建国点了一棵大前门,岔开话题,和他讨论起昨晚在水碓子打的那场群架。
我从老流氓孔建国那里听到有关朱裳妈妈的种种。这些种种往往真伪参半,前后矛盾。
在我印象里,所有大人对于他们少年时代的描述都是如此变化莫测,在这点上老流氓孔建国也不能免俗。他们少年时代的故乡有时候是北风如刀,残阳如血,黄沙满天,白骨遍野,吃不上喝不上,地主乡绅不是天生歪一个嘴,就是后天瞎一只眼,像海盗一样用一块黑布包着,而且无一不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但是有时候却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绿水绕户,青苔侵阶,有鱼有肉有甜点,地主乡绅仿佛邻家大哥,多少有个照应,即使村里的标致姑娘嫁到外村的时候也会唏嘘不已。无论是哪种情况,大人的角色都是统一而恒定。那时候,他们都还小。他们统一地胸怀大志,抱负缥缈,他们志趣高尚,一心向学,他们习惯良好,睡觉前半个小时不看电视、不看手抄本和其他黄书,喝一杯牛奶(家里条件不好的喝一碗面汤),跑一千米然后冲凉水澡。他们不偷着抽烟,他们不梦见女特务或是邻村寡妇,他们不遗精,不手Yin。无论他们现在怎样,他们的过去都是我们现在的榜样。他们说起他们过去的故事,我总是将信将疑。
老流氓孔建国说朱裳妈妈生在陕西米脂,英雄李自成生在那个地方,玩弄英雄于两股之间的貂蝉也生在那个地方。我没去过那个地方,如果朱裳生在那个地方,我没准会去一趟,看看什么样的地方能长出那样一个姑娘。
老流氓孔建国说他去过。那个地方终日黄沙满天,出门一趟,回到屋子里,洗完手还要洗鼻孔。无论男女,鼻毛必须留得老长,否则黄沙入肺,得肺气肿,像今天的北京一样。地瘦得要命,天公不作美的时候,什么庄稼也不长,只长大盗和美女。那个地方水缺得要命,为了一口水井,动辄拼掉十几口人命,但是长出来的姑娘却从里到外透着水灵,肌肤光洁润滑,如羊脂美玉,男人摸过去,滑腻留手,沾上就难放。男人们私下里抱怨都是姑娘吸干了天地间的水气,如果在村子里呆长了,不仅水没得喝,自己的水也会被这些姑娘吸干的。没有法子,男人只有自己出门找水喝,怕人家不乐意给,随身带上了刀。
朱裳妈妈出生之前,三个月没见到一星雨,从地上到树干上到人的嘴唇上全是裂开的口子。出生的时候费了老大的力气才凑够了一盆接生用的开水。孩子生下来,没哭,大家听到的是一声撕心裂肺的雷声,之后的暴雨下了三天三夜。
朱裳妈妈四岁时死了爹,十四岁时死了娘,娘死前对她说:“娘知道你饿不死,只是别太对不起良心,善用自己的脸蛋。”还告诉她,她有一个远房的堂哥在北京做工,可以去找找他。第一句,朱裳妈妈太小,听不太懂,但是第二句里有时间地点人物,她还是明白的。她随便收拾了个小布包袱,把家托付给邻居的一个精壮男孩,说去几天就回来,门也没锁就走了。后来这个精壮男孩为朱裳妈妈看了二十年的门,三十五岁上在锣鼓声中娶了邻村的一个傻呵呵的漂亮姑娘,破了童男之身。
朱裳妈妈的堂哥有五个饿狼转世的儿子,为了一日三餐甘心情愿承受父亲的殴打与谩骂。堂哥还有一个抹布一样的老婆,她常唠叨她曾是一支鲜花,不是牡丹花也是芍药花,反正是那种美丽鲜艳健康阳光的。全是因为这些个恶狼一样的儿子,才变成现在的样子。这时候堂哥常常会跳出来证明,即使他老婆曾经漂亮过,这些年也被她随着大便拉掉了。堂哥的老婆便秘,每天要蹲进胡同深处的公用厕所和共同出恭的大妈大婶聊一个钟头的闲天,那是她一天当中的最高潮。胡同里的公用厕所男女隔光不隔音,堂哥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常常听见他老婆爽朗的笑声。
朱裳妈妈到来的第一天,堂哥做了猪肉炖粉条,饭桌上他的五个儿子看她的眼神,让她觉得他们希望把她同猪肉一样和粉条一起炖掉,这样可以多出几块肉,还可以少掉一张吃肉的嘴。以后吃饭的时候,她总是被这种眼神叼着,不吃饭的时候,堂哥老婆的注视让她感觉在被抹布轻轻地抹着。有时候堂哥会找话和她聊上几句,堂哥正在洗菜的老婆便把水龙头拧到震耳欲聋,然后胸襟旷达萧然自得地接受堂哥的一顿漫骂。
朱裳妈妈的侄子们几乎和朱裳妈妈一般年纪,他们把事物分为两种:能吃的和不能吃的。能吃的就吃掉,他们生吃芹菜、茄子、土豆、鱼头、肥肉。他们把偷来的自行车轮胎剪成碎片,熬成猪血色的胶,涂在长长的竹竿端头。抓来的知了被去了头、腿、翅膀和肚子。剩胸口一段瘦肉,在饼铛里煎了,蘸些酱油和盐末儿,嚼嚼吞进肚子。朱裳妈妈从来没在堂哥家听见过蝉声。不能吃的,他们就杀死它。他们花两分钱在百货店买五粒糖豆,一人一颗,仔细在嘴里含吮,待糖豆完全化掉,他们省下最后一口唾沫啐到蚂蚁洞口,用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半副老花镜聚焦阳光,烫死任何一只敢来尝他们唾沫的蚂蚁。
朱裳妈妈不能吃,也不能杀死。侄子们的年纪还小,上嘴唇的胡子还没硬,看着朱裳妈妈的脸和身子,心也不会像他们父亲的一样不由自主地跳起来。所以他们虐待她。他们不敢让她的身上带伤,他们的爸爸发现了,会加倍处罚他们。他们不怕她告状,因为她从不。于是他们运用想像,让朱裳妈妈在外人看不出的状态下忍受痛苦。
有一天朱裳的妈妈忽然明白,她只有一个选择:逃跑。不然她只有一死,被侄子们搞死或是被堂哥的老婆毒死。终于在一个下午,天上是暮春的太阳,后面是挥舞着木棒的兴高彩烈的侄子们,木棒上绑着棉花和破布。朱裳妈妈跑出院门。
胡同口有几个半大的男孩,或趴在单车的车把上,或靠在单车的座子上聊闲天,说东四十条昨晚一场血战,著名的混混“赖子”被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新锐用木把铁头的手榴弹敲出了脑浆子。说刚从街口过去的那个女的屁股和奶子大得下流,应该由他们以“破封资修”的理由把她斗一斗。朱裳妈妈留意过这伙人,其中胳膊最粗的那个鼻梁很挺,眼窝很深,偶然能看见眼睛里有一种鹰鹫般的凶狠凌厉。天气还不是很热,但是他们都单穿一件或新或旧的军上衣,把袖口挽到胳膊,只扣最下面的一两个扣子,风吹过,衣襟摇摆,露出开始发育日渐饱满的胸大肌。
朱裳妈妈跑出胡同口,斑驳的墙皮上画着巨大的红太阳和天安门,以及粉笔写的“李明是傻逼,他妈是破鞋”之类的文字。她觉得阳光耀眼,开残了的榆叶梅和正开的木槿混合起来发出一股莫名其妙的味道。天上两三朵很闲的云很慢地变幻各自的形态,胡同口两三个老头薄棉袄还没去身,坐在马扎上,泡在太阳里,看闲云变幻。
朱裳妈妈径直扑进胳膊最粗、胸肌最饱满、眼神凶狠凌厉的那个男孩的怀里,声音平和坚定:“带我走吧。”从那儿以后,朱裳妈妈芳名飘扬。
我看着老流氓孔建国渐渐显现的肚腩,我反复问过老流氓孔建国,胳膊最粗、胸肌最饱满、眼神凶狠凌厉的那个男孩是不是他。他说,少问,听着就好了,问什么问。看他那德行,好像至今还和朱裳妈妈有些瓜葛似的。其实我更想听那个胳膊最粗、胸肌最饱满、眼神凶狠凌厉的男性好汉的故事,朱裳妈妈只是落在好汉怀里的一朵鲜花,我更想听大树的故事,想成为好汉。老流氓孔建国脸上有皱纹和刀疤,像穿了很久的皮夹克。他的眼里有光,像个水晶球,我想从中看见我的未来:我能不能成为好汉?成为好汉之后,有没有朱裳妈妈径直 扑进我的怀里?如果有,我应该在哪年哪月哪一天在哪个胡同口候着?朱裳妈妈扑过来,我该用什么姿势抱她?我低头是不是可以看见她的头皮,闻到她的味道,手顺着她的头发滑下去。然后我该怎么办呢?但是老流氓孔建国从来不和我讲这些。
老流氓孔建国不是说故事的好手,关于朱裳妈妈的种种,不是老流氓孔建国一次完整讲出来的。这个题目他讲过很多次,每次讲一点,好些叙述自相矛盾。周围的孩子太多,他不讲(特别是刘京伟在的时候,他从不讲)。没烟,他不讲。啤酒没喝高兴,他不讲。
当时很少有瓶装或是罐装啤酒,像买白酒一样,我们拎着暖水瓶到邮局对面一个叫“为民”的国营餐厅去打。
()
那个国营餐厅只在每天下午三点供应一次啤酒,啤酒很快卖完,周末不上班,没有供应。虽然看不到里面如何操作,但是我猜想,他们一天只能从啤酒厂拉来一大罐啤酒,卖没了就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啤酒可真差,一点泡沫也没有,味道淡得出个鸟来。张国栋天生肾衰,尿出来的尿都比那时的啤酒泡沫还多、颜色还黄、味道还大。但是那毕竟是啤酒呀,毕竟比水泡沫多、比水黄、比水有酒味。喝起来,感觉像《水浒》里面的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吃饱喝足之后大秤分金,分从山下大麻袋装回来的大奶姑娘。我想,《水浒》那时候的酒和我们国营餐厅供应的啤酒差不太多。那些好汉,十八碗下肚,走路不晃,还能施展旋风腿,摸孙二娘的屁股,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供应有限,负责卖酒的黑胖子感觉自己是酒神。手里掌握了方圆十里地方百姓的快乐,得意非凡。
每天三点钟,他睡足了午觉儿,拧开水龙头冲个脸,听着卖酒的窗口人声嘈杂。他总要多慎十分钟,才爱答不理地拨开遮挡窗口的三合板,面对等他好久的买酒人群。我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三合板一打开,迎面升起黑胖子其大无比的猪头,我看见他鼻孔里梅枝横斜的粗壮鼻毛,我闻见他鼻孔里喷出的宿酒臭味。这个混蛋,一定是在午睡前偷酒喝了!黑胖子瞥见我和我后面排队的刘京伟、张国栋,以及我们三个左右手拎着的特大号暖水瓶,吼道:“又是你们。酒钱!”我看见他的鼻毛一翘一翘地抖动,最长的一根长长地弯出鼻孔。
黑胖子是从炮兵部队转业的,据说练过军体拳,三四个混混近不了身。我不信。夏天的时候,黑胖子坐在板凳上在楼下乘凉,他老婆骂他最没用,他大气不出,低眉顺眼,一身肉懈懈地摊垂着,蒲扇死命地摇。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黑胖子为什么没用,但是看见周一到周六每天三点神气活现的黑胖子,软塌塌的一团,心里忍不住开心。
朱裳妈妈芳名飘扬的方圆十里就是东单、南小街、朝外大街这几条胡同。
京城自从被二环、三环路圈住,就开始在环路外大兴土木。就连远郊区县都忙着在粪坑边上盖起两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