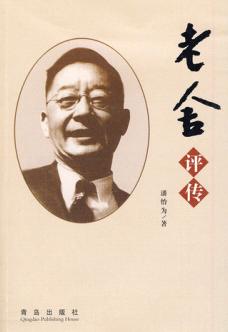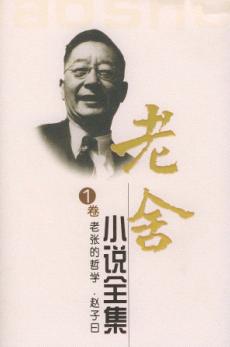老舍新诗-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得不憔悴,谁肯,
就连一钉星儿,自甘憔悴!
在秋风里,就在秋风里,舞吧,秋风送来的到底是音乐。
舞恼了秋风,晚霞儿欲睡,舞吧,乘着那欲圆未圆的明月。
流尽了西风,流不尽英雄泪;舞吧,每一片红叶!
山腰水畔,点染的是胭脂血,舞吧,连影儿,也左右回旋着红的黄的音乐。
生命最后要不红得象晴霞,当初为何接受那甘露甘霖,大自然的宝液?
适者生存焉知不是忍辱投降;努力的,努力的,呼着光荣的毁灭!
草儿低头,虫儿不响,一夜秋霜,只有红叶,哪怕是孤单的一小片红叶,还舞着;菊花虽好,怎奈不会飞翔,是我,只是我,在菊花时节,舞残重阳后的明月?廿一年,九·一八
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微音》月刊第二卷第七、八期合刊号
教授
张先生是位有名的教授,所以最怕人家看他不起;自己太忙,不能写文章,专等别人写了加以攻击;不幸,没有什么毛病可挑,便搜寻点私事出出气:说作者心田不正因为鼻子歪,或是小时候偷过一管笔。
文章不肯写,讲义懒得编,破着工夫为徒弟们写短序,字写得古,图章刻得精,由白话返文言,偶尔才用个“的”。
爱国的言论时时在报上登,一听库伦有难,立刻将家小送到广州去。
薪水不发,懒得上堂,薪水发了,应略事休息。
可是钟点不妨多多的争,反正时常请假显着大气。
提倡国货,收买古籍,介绍中医,租一所洋楼为是有拉水的便器,因为他在巴黎读过四书五经,还在伦敦学了社会经济,西方的物质,东方的精神,一以贯之,死而后已!
不幸,果然有一天他一命归了西,夫人小姐全动了气;
那天和他索汽车,
他说做了院长自然会有的;谁知院长未作身先亡,汽车,况且怎么安置那个女书记?
夫人一怒到校去索薪,只得了预支的几张正式收据!
挽联花圈挂满在灵前,呜呼!张教授的钟点被别人分了去!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她记得
我问你,小孩:你几岁呀?过来!
睁大了圆眼,
带着点惊疑;
天生的圆眼,
后天的惊疑,
自从听见过几次空袭。
她睁大了圆眼,
把食指放在鼻子上,
发娇的不肯过来,
象爹娘还活着时那样。
摇一摇头,她不知,
或不肯,说出几岁;
又问了一声,
她往后退,“我不会!”
你一定会,比谁都会,会说你几岁;
你还会告诉我,
从哪里来的,对不对?
笑了一声,
转身要走去;
半斜着脸儿,
不愿说出小心里的委屈。
娘记着我几岁,
爸回来,先喊妹妹,
慢慢的低下头,
她把食指咬在口内。
娘叫炸弹打飞!
爸!只剩了一只手!
一个白发老头子,
从方家巷把我带走。
告诉我,宝宝!
哪个方家巷?
是上海,还是南京?
那地方什么样?
很远,很远的方家巷,有树,有房,还有老黄,老黄是长毛的大狗,
爱和我玩耍,不爱汪汪。
呼隆!就都没了,
房子,妈妈,老黄;
树上的红枣,
多么甜,也都掉光。
呼隆!就都没了,
爸爸的手,
戴着戒指的手,
掉在厨房的门口。
一位白胡子老头,
带我到了这里,
妈还记得我的岁数吗?
爸,没了手,在哪里?
我记得方家巷,
不是有房有老黄的方家巷,是,是,有血有烟的地方,爸手上的戒指发亮。
哼,我知道!
她睁大了圆眼。
我乖乖的不哭,
那是日本人放的炸弹!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大公报》“重庆市儿童节纪念特刊”
抗战民歌二首
(一)大家忙歌
一
年轻的好汉快扛枪
去打小日本大家忙
胆粗心细志气刚强
保住中华好家乡
有好汉国不亡
年轻的好儿郎
二
年老的人们守家乡
耕田又织布大家忙
五谷丰收完粮纳税
兵丁有饷民有粮
不求佛不烧香
爱国的不遭殃
三
作工的好汉在后方
昼夜勤工作大家忙
制出国货同胞爱用
不教金银流外洋
兴工业国富强
作工的有荣光
四
作买作卖的好心肠
赚钱买公债大家忙
不卖仇货穷死日本
公平交易有天良
我中华无奸商
作商的好心肠
(二)出钱出力歌
有钱多出钱
国亡钱不存
有力多出力
国亡身不存
中华好地富何怕贫
百姓好心好即黄金
毁家去救国
杀敌把命拚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保住中华传子孙
不出钱不出力
失了江山绝子孙
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扫荡报》
空城计
日本小鬼吓了一跳,怎么城里静悄悄!
莫非空城计连琴也不弹,伏兵四起脑袋纷纷掉?
登高一望笑哈哈,
原来老将精勤练赛跑。
大车小车齐向南,
黄沙滚滚风浩浩;
千箱万箱行李多,
悲壮激昂私囊饱。
失城丧地谁管它,
反正没人把咱老子怎样了!
细柳营中打算盘,
十万百万,哟,哪儿来的一声炮?
中军,是不是敌人临了城?
元帅!有三个黑影在远处跳!
啊!哇呀呀呀呀呀呀!
气杀我也,为何不早报?
将军一怒退出城,
越跑越怒不停脚,
一气跑到土耳其,
安居乐业大寿考。
日本小鬼亦欣然,
各得其所哥俩好。
君不见满洲之国何以兴?
只须南向跺跺脚。
载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礼物
我不能供献你,朋友,什么奇伟的思想;我不能供献你,朋友,甚至于一首悦耳的歌;我自幼就懂得,可是,怎么把一个钱当作两个花:
穷困中的经验——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
可是呢,一世界的苦恼还没压碎我的心;我不会用一根头发拴住生命的船;我的想象,象春天才有花,是开在我的经验里:我知道自己不会跌倒,因为我时时刻刻都在挣扎。
那么,我所能供献给你的,只是我;我小,我丑,但自古至今,只有我这么一个我。
在我之外,我没有半亩田;我的心在身里,正如身外到处顶着一块蓝空,叫作天。
除去我的经验,简直不认识我自己;我的经验中有你:我想起自己,必须想起来你,朋友!
能给你的,我已给过;能给我的,我已接收;我还愿再给,再受;咱们是朋友。
这里面并没有较量,咱们愿意如此,这样舒服。
我们交换的也许是钱,也许是件衣裳;但咱们也握手,咱们互视,咱们一同高声的喊……
这就够了,朋友,咱们活着,为彼此活着。
咱们还有个相同的理想——咱们活着,生里包括着死。
死是件事实,可也能变成行为;这应落泪的事实,
及至变成了行为,咱们笑着破坏,以便完成。
最多咱们毁了自己,至少咱们也完成一点,哪怕是一丁点,真正的破坏,建设是另一个名儿。
假若一旦死分开你我,噢,那是必不可免的事实;
我或你先卧在地下,我或你来到坟前——或者连个坟头也没有——我或你踏着那地上的青草,
何必含着泪呢,在记忆中咱们曾在一块儿活着过:
你我的价值,只有你我知道;死去的永远静默,
活着的必须快活;假若咱们没享受过,为什么再使后来的哭丧着脸呢?咱们毁了生命,
就是埋在地下还会培润几条草根,使草叶有老玉样的深绿;这草叶上有你有我,笑吧,死便是生!
笑吧!假若咱们没那样的活过,咱们再活一百回,
有什么意思呢?生死一回就够了,因为这一回咱们尽了力;一个霹雳就收住了雨,那七色的长虹,
那戏水的蜻蜓,雨后自有人来观赏;认定了吧,那不是咱们的事。朋友,我供献给你什么呢?
什么呢?假若不是鼓励,我怎伸得出去手呢!
载一九三五年五月八日《益世报》
恋歌
自从梦笔生花,才思赡富,真乃风声鹤唳,草木皆诗,信手拾来,俱饶奇趣。观已将瓜皮小帽换为桂冠,特此声明,谨防假冒。
自从那天我看见您,姑娘,我才开始觉得了生命。
您看,往常一顿吃四个馍馍,那天,我吃了整整一个锅饼;我那憧憬之胃,正如那歇司特力之心,从那天起,一齐十二分的发痛!
您那满身的曲线,和
那双安琪儿的眼睛,
我告诉您,我若是敢形容,便是天大的反革命!
我愿化为一只可爱的小猫,在您怀中咕噜咕噜,三年也咕噜不尽,咕噜的都是妹妹我爱您,毛毛雨,和请您看电影。
姑娘,你发点慈悲,为您我害着相思与胃病!
我在梦中,唤过您多少声“笛耳”,和多少声“大耳令”,那只因为,慈心的姑娘,我还不晓得您的名和姓。
告诉我吧,您是姓张,王,李,赵,还是洋钱声儿的宋?
您若不肯,我只好学福尔摩斯,四面八方用科学方法去打听。
先告诉您些,我不完全属于无产阶级,但您如愿意,我也可以去革命;您若不以为然,那么,我可以坐着汽车天天把鲜花送。
只要您愿意,什么都成,您一张嘴,咱们马上可以把婚定。
我现在是真正的独身,虽然在乡间,有个老婆脸黑得象吕宋;
那不要紧,您自然也不在乎;您更应当可怜我,那是有志青年的大不幸;假如您在乎,我向天赌誓,明天,明天我就下乡把她往娘家送。
每月供给她块半大洋钱,凭良心说,这总不算侮辱女性。
钻石戒指,您的,我决定去选挑,只等您那玫瑰之唇那么一动。
假如,我的爱之晶,您说声NO,天大的希望与狗命一条将同时坠了井;那么一来,姑娘,您瞧,宇宙,汽车,鲜花,跳舞,便都要一干而二净!
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论语》半月刊第七期
流离
家何在?
前路茫茫!
是万恶的日本,
使我们家破人亡;
家何在?
有血性的,
打回故乡!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抗战画刊》第十一期
蒙古青年进行曲
北风吼,马儿欢,黄沙接黄草,黄草接青天;马上的儿女,蒙古青年——是成吉思汗的儿女,有成吉思汗的威严!
北风吹红了脸,雪地冰天,马上如飞,越过瀚海,壮气无边!
蒙古青年是中华民族的青年!
国仇必报,不准敌人侵入汉北,也不准他犯到海南!五旗一家,同苦同甘。
蒙古青年,是中华民族的青年,快如风,人壮马欢!
把中华民族的仇敌,东海的日寇,赶到东海边!
蒙古青年,向前!
守住壮美的家园,成吉思汗的家园!
展开我们的旗帜,蒙古青年!
叫长城南北,都巩似阴山,中华民族万年万万年!
载一九四○年一月《政论》第二卷第六期
谜
说,什么是生命?
啊,不过给别人制个谜。
你猜不着我,
我猜不着你;(奇*书*网。整*理*提*供)
不然,同床的爱人为何你朝着东,我朝着西?
母子们为何闹脾气?
不然,为何独自祷告上帝?
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活着,最好彼此笑嘻嘻,死了,咱们谁也不理谁。
你说我有点小聪明,
十二分对不起!
我看你脸上没雀斑,
天大的可喜!
就这么着吧,
假装你我是亲兄弟。
哥哥是个谜,
弟弟是个谜;
好吧,多握几次手,
少争几回气,
你知道,咱们死了,
谁也不理谁!
载一九三三年五月《文艺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
怒
作这首小诗的动机,是文协的诗歌座谈会拟于最近出《抗战诗歌》,大家干得起劲,所以就编这么几句,仿佛是先来预贺一下。
怒火胸里烧红,
脸上烧红,
对沧海,
对青峰,
要狂喊,狂喊!
喊哪!
喊出冲杀,
喊出战争,
是诗歌,
是呼喊,
是无可压抑的热情。
喊哪!
喷出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