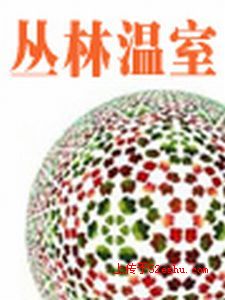丛林温室-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一个阶段。
当种子绽开时,这些人已摔到了地上。他们站起来,浑身疼痛不已,四肢僵硬嘎嘎作响。天空中飘着大雪,他们几乎不能看见对方,个个身体都变成了白柱子,恍恍惚惚。
雅特摩尔急着要把肚皮人召集到一起,以免他们失散了。看到昏暗的光线中有一个影子在闪闪发光,她跑过去抓住它。一张脸转过来对着她号叫着,它长着一副黄牙和火辣辣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她吓得退了回来,这家伙也就一跃不见了。
他们这才知道大山里还有别的动物。
“雅特摩尔!”格伦喊着,“肚皮人在这儿,你在哪儿?”
她吓得僵硬的双腿也灵活起来,朝格伦跑过去。
“这儿有别的动物,”她说,“一种野兽,长着牙齿和大耳朵的家伙。”
当雅特摩尔和格伦朝四下看的时候,那三个肚皮人又开始唠叨着死神和黑暗。
“在这鬼地方,什么也看不见。”格伦说,他脸上溅着雪花。
他们相拥着站在一起,手里持着刀。雪突然小了下来,下起了雨,最后雨也停了。透过最后一阵雨,他们看到了一行十多只白家伙一跳一跳地跳过了峭壁的顶端,朝着黑暗的那面跑去。他们的身后拖着一种装有粗布袋子的雪橇,有些羽茎的种子从一布袋里漏了下来。
一线阳光照在幽暗的山边,好像这些白家伙害怕太阳,急忙进入了一个隘口,不见了。
格伦和雅特摩尔相互看了看。
“他们是人吗?”格伦问。
她耸了耸肩,表示不知道。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样的。这些肚皮人躺在泥地里,呻吟着,他们是人吗?连同格伦在内,他真是难以揣摩,好像他完全被蕈菇征服了,能说他还是人吗?如此之多难解之谜,有些她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更不用说去想怎么回答。但太阳又一次暖和地照在她身上,天空中闪烁五彩的光芒。山上有一些岩洞,他们可以到那儿去生一堆火。他们又可以活下去,暖暖和和地睡一觉。
她往后捋了捋脸上的头发,开始慢慢地朝山上走去,虽然她觉得身子很沉很沉,走起来十分费劲,但她知道,其他人会跟着她走来。
第二十二章
这个大斜坡上的生活还是让人忍受得了的,有时候不仅是忍受,因为人稍有点幸福,就会感到满足。
在这个广袤而崎岖的地方,他们认识了自己。
人类相对来说是那么的无能,简直没有多少价值。
地面上作物的生长和天气的变化顺其自然地进行着,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就这样在云层和斜坡之间,在泥土和风雨中,无声无息地生活着。
尽管夜晚与白昼不再表示时间的流逝,但另一些自然现象都可以说明时序变迁。当气温降低时,风暴加剧了,有时落下的雨寒冷刺骨,有时候又灼热烫人。所以他们大声叫喊着,跑到岩洞里去躲雨。
蕈菇更加严厉地控制着格伦的意志,他变得更加郁郁寡欢了。很清楚,是它的才智把他们引到了这个死亡之地。它越来越快地繁衍着,它急需发展自己的势力,使格伦断绝了和同伴的交往。
第三件表明时序变化的事,是在一次暴风雪中,雅特摩尔生下了一男婴。
这增加了她活下去的信心。她叫他劳伦,心里很满足。
在这偏僻的山边,雅特摩尔抱着她的孩子。尽管他已睡着了,她仍在给他唱催眠曲。
斜坡的上端沐浴在阳光之中,而下端则沉溺于黑暗里,整个下层地段一片漆黑,偶尔被红红的烽火照亮,山峦像是石头生物,探出身子,触到亮光。
即使是在黑暗的地方,也绝不是一片漆黑。就像死不是绝对的一样。生命的化合物会再生成以创造更多的生命,所以人们往往认为黑暗只是不够明亮,是被迫逃避亮光和人多的地带。
在流窜的生物中就有种皱皮飞禽。有一对皱皮飞禽从雅特摩尔的头顶掠过,尽情地飞翔着。一会儿收紧翅膀俯冲下来,一会儿张开翅膀悠闲地飞向温暖的气流之上。劳伦醒了,雅特摩尔把这飞行物指给他看。
“它飞走了,劳伦。咦,它飞到山谷里去了。看,他们在那儿——又回到高空中去了,飞得真高啊。”
小家伙皱着鼻子和她一道嬉戏着。这对皱皮鸟一会沉下来,一会儿飞上去。在阳光下穿梭,然后又钻进阴影里。不一会儿又飞上天,好像从海里飞来,偶尔又飞上云层。云层现出一片古铜色,就像大山本身的景色,反射到下面模糊的大地上。下面荒芜的乡村染上一层斑斓的色彩,有金黄的、淡黄的。
在金色的黄昏里,皱皮鸟来回飞翔着,寻觅着那飘浮在太阳光线下的孢子为食。小劳伦格格地笑着,伸展着他的一双小手。雅特摩尔也高兴地笑着,为她儿子的每一个动作而感到欢心。
一只皱皮鸟这时直直地落了下来,雅特摩尔吃惊地注视着,发现它失去控制了。它盘旋而下,它的同伴在后面拼命地眨着双眼。
一会儿雅特摩尔就明白了它一直向下冲,砰的一声重重地撞在山坡上。
雅特摩尔站起来,她看见这只皱皮鸟一动不动地瘫在地上,一只丧偶的同伴在上面拍打着翅膀。
她并不是惟一看到这一幕的人。那边的大山坡上,一个肚皮人开始朝那只鸟跑下去,边跑边大声地叫着他的两个同伴。她听见“到这儿来亲眼看看这落下来的有翅膀的鸟!”在这旷野里声音非常清晰,她能听见他的脚在山坡上跑的拍打声。她站起来,张望着,手里抱着小劳伦,她对任何干扰她平静生活的事都会感到遗憾。
其他的人也向这只落下的鸟跑来,雅特摩尔看见那边山脚下一群家伙从一堆石头后面迅速地跑了上来,她数了数一共八个人,白白的身子,长着尖鼻子,大耳朵。在墨绿色山谷的衬托下,看上去是那样的醒目,他们身后拖着一架雪橇。
她和格伦把他们叫做山里人。他们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山里人,因为尽管他们并未伤害他们,但跑起来很快,而且身上全副武装。
这时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三个肚皮人跑下山,八个山里人跑上山。那只活的鸟在他们头顶上盘旋,不知它是在哀悼它的同伴,还是准备逃跑。山里人身上带着弓箭,突然雅特摩尔为那三个肚皮人担心起来,毕竟他们这一路上一直结伴同行。她紧抱着劳伦站起来,喊道:“嘿,你们这些肚皮人,快回来!”
就在她喊的时候,跑在前面的那个凶猛的山里人拉弓射了一箭。那只活鸟显然被射中了,盘旋着栽了下来。领头的肚皮人急忙躲闪了一下。那只落鸟翅膀微微拍打着,掉下来时正好打在这个肚皮人的肩胛骨上。当那只鸟掉在他身边时,他也跟着摔倒了。
这群肚皮人和山里人相遇了。
雅特摩尔转身,朝他们栖身的岩洞跑去。
“格伦,快来呀!肚皮人要被杀掉了,他们在外面受到了那群可怕的大耳朵白家伙的攻击,我们怎么办?”
格伦倚靠在一个石柱上,两臂紧紧地抱在胸前。雅特摩尔进来时,他的目光像死人般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又把目光移开了。
他脸色苍白,刚好和他头上到咽喉部闪亮的猪肝色的蕈菇成鲜明对比。这个蕈菇黏糊糊的皱皮把他的脸部都框住了。
“你准备怎么办?”她问道,“这些天你怎么了?”
“肚皮人对我们已经没有用了。”格伦说,但是他还是站了起来。她伸出手,他无精打采地抓着她的手,拖到了岩洞口。
“我已喜欢上这些可怜的家伙了。”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向陡峭的山坡俯看下去,那儿有一些影子在薄雾中移动。
那三个肚皮人正拖着一只鸟朝山上走回来。山里人就走在他们身边,拖着雪撬。雪撬上也有一只皱皮鸟。这两伙人很友好,一块儿走着,肚皮人边说边手舞足蹈。
“喂,你看这事怎么办?”雅特摩尔大声问道。这是一行奇特的队列。从侧面看过去,山里人长着一副猪嘴。他们走得很整齐,有时上了斜坡还推着四个人往前走。虽然他们离雅特摩尔太远,她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要是他们确实在说些什么的话,雅特摩尔只能听见一种像狗叫的声音。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格伦?”她问。
他什么也没说,看着那一群人。他们这时正朝着肚皮人住的岩洞走去。这是格伦指定叫肚皮人住的地方。当他们走过羽茎边上时,他看见他们指着他这儿笑着。他没做声。
雅特摩尔抬头看他,对他近来的这些变化突然感到很可怜。
“你这样老不说话,看上去病得很厉害,亲爱的。我们一起走了这么远,我们只希望互相爱慕,然而现在你好像从我身边消失了。我内心依然爱着你,我仍然念叨着你的仁慈,而你却没有了爱,没有了仁慈。哦,格伦,我的格伦!”
她用那只闲着的手臂搂着他,却感到他要走开。他开口说话了,话语冷冰冰的:“救救我,雅特摩尔。耐心点,我病了。”
此刻她心里还想着别的事。
“你会好的,那些凶猛的山里人会是出了什么事吗?他们友好吗?”
“你最好去看看。”格伦说,声音仍很凄凉。他挣脱了她的手臂,回到岩洞里躺下,又像先前那样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雅特摩尔坐在洞口,拿不定主意。肚皮人和山里人已经进了另一个岩洞。
她无可奈何地坐在那儿。这时乌云密布,天开始下雨了,接着又下起了雪。劳伦哭了,她把乳头塞给他吸吮。
她的思绪慢慢地走神了,忘记了外面下着雨雪。她的身边浮起了一些模糊的图景。这些图景尽管稀奇古怪,却也是她想像出来的。她过去在牧人部落的安全日子就像小红花一样呈现在眼前。
只要做点努力,这小红花还是可能是她的。因为过去她曾一直生活很安逸。她从不把自己看做有什么特殊之处。她现在想再过着安逸的生活,她也只能远离这一部落,去作些想像,想像自己是群体中一个成员,或想像自己是舞蹈中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女孩,提着水桶去长水河提水。
现在红花没有了,只有一个花蕾在她胸前开了花。人群走了,黄色的围巾和红花一起消失了。(多么漂亮的围巾!头顶上永远不落的太阳,像热水浴。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不懂得自己的幸福——这些都是她想像中的黄色的围巾。)她远远地看见自己把黄色的围巾扔掉了,跟着这个流浪者。这个流浪者的优点就在于他是一个谜。
这个谜是一片枯萎的树叶,上面栖息着某种东西。她跟着这片树叶,她自己小小的个子变得越来越近,不知怎么的变出了花穗。围巾和红花瓣愉快地释放出阵阵芬香。现在树叶变成了肉体和她一块儿徘徊摇荡。她个子也长得高大了,四周人来人往,在一片乳白色大地上,甜蜜相处。而在红花中听不到变成肉体的树叶奏出的音乐。
然而,花朵色彩消退,出现了大山,大山和花朵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个无边无际的陡峭的斜坡上,大山连绵起伏,似乎山脚沉浸在黑暗的浓雾中,山峰隐藏在黑色的云层里。黑色的雾、黑色的云在她的幻想中无限延伸,记录着各种罪恶。她的精神稍一振作,发现这大斜坡不只是她现在的生活场所,而是她的永久家园。在她脑海里一切似是而非的想法全然消失,只剩下对个别不同时刻的梦幻。在这大斜坡上所有美丽的鲜花,漂亮的围巾以及情欲都好像是和以往截然不同了。
现实中的山上雷声隆隆,把她从幻觉中拉了回来,打破了她幻想中的景象。
她回头看看洞里的格伦,他还是一动不动。他没看她。她的白日梦帮助她理解了自己的追求。她告诉自己“是那个神秘的蕈菇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劳伦、我和可怜的格伦一样都是它的牺牲品,它在折磨他,所以他病了。它在他的头上,在他的脑海里。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想个办法好好对付它。”
理解人并不能得到安慰。她抱起孩子,两手遮住乳房,站了起来。
“我要到肚皮人的岩洞去。”她说,原以为格伦不会答话。
格伦却说话了。
“你不能带劳伦到大雨中去,把他给我,我会照看他。”
她向他走过去,虽然光线很暗,但她发现他头上和脖子四周的真菌看上去比以前更暗了。它一定正在长大,以从前所没有的方式显现出来,爬满了他的额头。所以当她正要把孩子给他时,又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在蕈菇影响下抬眼看了她一眼,脸上显出一副她难以理解的神情,交杂着愚蠢和狡诈,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她急忙把孩子收回。
“把他给我,他不会受到伤害。”格伦说,“青年人可以学会很多东西。”
虽然他的动作显得很困倦,但他还是敏捷地跳了起来。她愤怒地跳开了,气喘吁吁,抽出了刀子,全身细胞都警觉起来。她像一头野兽似地对他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