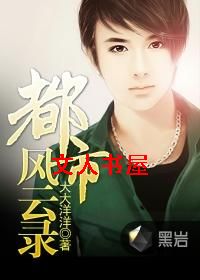高中回忆录-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边是亲情,一边是爱情,我真的不愿意选择啊!李斌追来问我究竞出了什么事。我把上午发生的事说了一遍。他也震惊。
六十九
上课铃响过后,我依旧茫然地睡着。我千万遍地问着自己该“怎么办”,我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天花板,如果它有灵性的话,也该显灵告诉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了,可是它终究是铁石心肠。寝室里真的太静了,静得像死气沉沉地北冰洋,窗外阳光明媚,可我感到好冷,冷的我几乎窒息。几个时辰过去了,我的大脑还是一片空白,空得像一块无边无际的荒漠,视线可及之处,寸草不生。垫在头下的手已经麻木了,我不得不换个睡姿,却发现了枕边的音乐盒。我伸手轻轻地摸了摸它,这段日子,它真的给我带来了不少好梦,它甚至已成了我灵魂的又一个支撑。我缓缓地打开,那熟悉的生日歌又响起在耳畔,莉儿清脆的笑声似乎也夹杂在其中。我知道,我不能失去她,如果没有她,我真不敢想象我的生活会是多么苍白无味。可是父母的亲情又何尝不是重如泰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又怎能做一个不孝子呢?我的头好痛!好痛!仿佛头上戴着一只金箍。
躺着睡不着,不如出去走走,也许能意外地找到些灵感。学校里的一切我已经厌倦,我不愿在这里徘徊,反正都快被开除了,我也不在乎再多一条罪名,于是我大大方方地从大门出去。恐龙惊诧地看着我大摇大摆地走出校门,居然没有拦我。
还是那条小路,那根桥,桥下的流水依然不急不慢地流着,仿佛一个得道高僧在心平气和地讲叙着人生的真谛。潺潺流水从未停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执着,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个音节。也许是想叙说什么,又也许它在暗示着某一种玄机,可是我不懂,就像我不懂为什么学生一定得规规矩矩的读书,考大学一样。
“蛇!蛇!”这不是莉儿的声音?我四下环顾却不见其人,好像是从水中冒出来的,我疑虑地拍了拍脑袋,觉得它好沉重,仿佛里面塞满了铁。怎知这一拍闯了大祸,所有的回忆像捅了窝的蚂蚁,潮水般地涌了出来:“阿海,你要好好念书,考上大学。”“萧海,生日快乐!”“阿海”……我紧紧地闭上眼睛,捂住耳朵,可那两种声音依然响彻在脑间,挥之不去。我知道我根本做不了选择,唯有听天由命了。我掏出一个一元的硬币,紧紧地捏在手中。不管有没有上苍,今天就让天意来决定一切吧。如果是国徽我就选择亲情,去向学校低头认错;如果是茶花我就选择莉儿,哪怕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决心已定,我颤抖地用拇指把它弹向空中,硬币发出“叮”的一声响,翻转着从眼前划过,又迅速地坠落在桥面,打了几个转后,它终于停住了——
原来做一个选择就这么容易!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告诉自己:既然选择了,就该一无反顾。
进校时,我还是堂堂正正地从大门进去。看到恐龙惊愕地眼神,我冲他淡淡地笑了笑。恐龙被我的肆无忌惮弄得回不过神来,又一次呆呆地目送我经过校门。
教室里正在上自修课,所有的人都埋着头在为明天的考试做准备。那紧张的气氛,就像一群战士在做战前准备,磨着刀,擦着枪,摆放手着榴弹,随时准备着跳出战壕和敌人浴血奋战一场。莉儿的位子空着,张敏见我微笑着从外面进来,显得很是惊讶。她忧心重重地告诉我:“大哥,莉儿被老刘叫走了。”我想李斌应该已经把上午的事告诉她了,所以不想再说什么。我冲她笑了笑,然后又出了教室,头也不回地朝政教处走去。
刚出教学楼,我就看见了莉儿,她正低着头朝这边走来,我也装作没发现继续笔直地向前走。她差点一头撞在我怀里。我从容地笑了笑。莉儿抬起泪水迷蒙的眼睛,也羞涩地笑了。(奇*书*网^。^整*理*提*供)唉!开除,既然无法逃脱他的魔掌,那么就让我欣然地接受它吧。无论是福还是祸,我都把它当作是上苍的思赐。在教学楼通往政教处的路上,我紧紧地揉住了莉儿。莉儿并没有显示出惊讶的神情,她顺从地依在我的怀里。尽管我并不知道我和莉而之间的这一份感情,是否称得上叫爱情,但是,我知道让我和莉儿划清界线,从此以后视如陌路我做不到。
晚饭,我们吃得格外香。张敏在席上还给我即兴编了首《大丈夫歌》:风吹雨打当沐浴,电闪雷鸣小儿戏。钢筋水泥加铁皮,惊涛骸浪也不惧。她还糊言道:“大哥比蟋蟀还帅,比裤子还酷。”我哭笑不得地接受着她的奉承。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张敏之所以如此活跃,是为了化解我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是为了能让我走得开心点,也就是所谓的饯行吧!既然是最后的晚餐我当然不想留下一个愁眉苦脸的形象,更不想给他们留一份落寞和无奈。莉儿也和我一样表现地很开心。但心里总是免不了酸楚,必竟开除,不是儿戏。不过得先声明一下,要开除地只是我一人,莉儿没份,也许是因为她的成绩好学校还不想浪费这一点升学率,又也许是因为她是女孩,怕她心理素质差,也会学一中的女孩跳楼。
夜自修,我已无心复习,光明正大地和莉儿传起了纸条。我问她是否害怕谣言。莉儿说她不怕。莉儿的回答让我甚感欣慰。无论我们的感情是否能够长久,今天我的选择无怨无悔。
对于开除,我确实没有多大的恐惧。高一学年已经尾声,我也已经见识了所谓的高中生涯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地方,我并没有丝毫的留恋。对于学校所谓的知识,我本就不怎么认同。我相信自己看书会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此时此刻,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当父母得知我被学校开除后会有的反应。
期未考试刚结束,死老刘再次召见了我。老刘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老刘已经把我父母请来了。看到父亲凝重地面孔,母新呆滞而惊恐慌的眼睛,我只好服罪低下了头。
七十
“阿海!”母亲亲切地叫我,似乎是想叫我解释几句。我无言以对,依旧低着头。
“你这畜生。”父亲见我依然倔强得伸着脖子,没有丝毫悔改之意,他按捺不住愤怒,抡起手给了我一个耳光。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打我,但我心里舒服,一点也没有被老刘打时的那种咽不下气。其实我倒很希望他能痛打我一顿,如此可以让我的良心得到一点点安慰,那样我就不会有太多的负罪感,也就不会太过谴责自己。母亲慌不择径地号哭了起来,她死命地抓着父亲的手,连劝带求地叫他不要动怒,慢慢开导,可是父亲的眼中依然怒火熊熊。我承认我太让他失望了,看着他早白的双鬓,我又何尝不是心如刀割,可是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我还是不想回头。
“思想不开窍,打是没有用的。”死老刘喝着茶,说风凉话。我恨不得狠狠地给他几拳以解心头之恨。
“刘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他只是一时糊途,你们不要开除他,再给他一段时间,我们会劝服他的。”母亲边哭边向死老刘哀求,那抽噎声把话儿截成了好几断。我长十七岁了,还从没见过她哭得这么伤心。母亲的哭声让我不由地悲从中来。死老刘也有些慌乱了,不管怎么说我母亲也比他大了十几岁,他怎么受得起这种哀求?死老刘语气稍软了点,不过他还是那幅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式:“开不开除,还得由上面来决定,现在关键是看萧海的态度如何,如果他依然顽固不化,那么学校也无能为力。如果他能认识错误,并保证以后决不再犯,学校或许是会考虑从轻处分的。具体怎么处分要到休学式才会公布,现在还有一段时间,你们可以先把他引回去,好好开导开导。”
父亲听了老刘的话,紧绷着的脸,稍微松懈了一点,那神情犹如一个行在大漠中的人突然看到了一片绿州,找到了一线希望。母亲一口气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在出校时,我看见了莉儿、张敏、李斌和林平。他们呆呆地看着我离去,茫然地如四株树苗。我想再留下一个笑容,可是没有笑出来。我没想到父母的反应会是如此激烈,更没想到他们会始终不答应我休学。
到家后,母亲依然哭哭,她说都是我祖父把我给宠坏了,这么任性。父亲一直阴沉着脸,抽着闷烟,两只眼睛凝滞地看了看地面。我鼓起勇气说:“爸,读这种书真的没有用,一旦过了高三,不管我有没有考进,都是过期作废的,学的东西根本就用不着。”
父亲愤怒地抬起头,又欲动手。母亲连忙冲到他前面,劝我道:“阿海,别傻了,读书怎么会没用呢,不然哪会有这么多人想上学啊?”
“我真是造孽啊,生出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来,我这每天早出晚归,累死累活为的是谁啊?自己小的时候想读书,家里没钱读不成,现在总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你妈平时肚子饿了买个饼都舍不得,千方百计的节省,还不是不想让你被别人看不起,希望你能安心地读书,考大学。哪知道你拿了钱居然在谈恋爱——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父亲愤怒地斥责着,他说话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显得有些颤抖。我从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习惯了忍气吞声的他,每当心烦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有什么事,他宁可烂在自己的肚子里,也不愿意表露出来。但今天他彻底地崩溃了。这个时候,与其说父亲是在责备我,倒不如说是在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我虽然自认为恋爱和学习、钱拉不上关系,但我不敢解释,此时来解释,无非是火上加油。我胆怯地低着头,任凭父亲在那里大发雷霆,我只是低着头面无表情而又目光呆滞地看着地面。
“阿海,听你爸的话,去向学校认错,爸妈不怕吃苦,只要你考进大学,以后有出息就行,啊!”母亲轻轻地说着,伸手理了理我零乱的头发。她的泪痕依然明晰地存在于我的眼前,我的心,开始了颤抖,我不由地再一次问自己,“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休学式前一天,我又被父母带到了学校,父亲还特意花五百元钱买了一条“大红鹰”和两瓶“茅台”。
其实这两天来,我还是没有改变主意,我之所以跟他们回学校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爸妈死心,因为我认定学校已经做出了决定,根本已不可能再扭转乾坤。父母没有去找老刘,而是直接去了校长室。校长今天居然也在。校长看见我们提着烟酒进来,连忙起身和我父亲握了握手,然后请我们坐下。我想他可能还不知道我就是萧海。这也难怪,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哪会认识自己家的鸡。父亲有些局促,他身上的衣服和校长的相比,实在就像是猪八戒在和朱丽叶比美。向来自卑的父亲,吞吞吐吐地向校长说明了来由。校长知道我们一家人此行的目的后,脸顿时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了下来,神圣的威严之气却像一股炊烟,扶摇直上九万里,他那鄙夷的眼神能把人看成蚂蚁。看见校长急转而下的神色,父亲显得更加不安了,他把烟酒摆在办公桌上断断续续地问校长能不能宽容宽容。校长如我所料地扔出一张布告说,学校已经研究过,做了决定,不能再作修改了。父母好说歹说,校长始终无动于衷,最后竟不耐烦地叫父亲把东西拿走。父亲绝望得神情麻木。他正欲转身回去的时候,母亲突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即而却两膝着地跪了下来。我情不自禁大叫了一声“妈!”脑子中像引爆炸弹,嗡嗡作响。校长也很吃惊,豁地站了起来,他惊惶失措地叫母亲赶快起来说话。母亲依然哭着哀求道:“校长,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他并不坏,你们不要开除他。”已成惊弓之鸟的校长终于答应了再研究研究。我知道在二十世纪未这一跪有多少份量?它足以压跨一座泰山啊!在妈站起来后,校长问我是否知错。我无声地点了点头,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哪!
七十一
休学式上,学校总算是手下留情,只给了我一个留校察看的处分。这样的处分就是在告诉我若再犯一点错误,还是得被开除。回到家里,我答应了爸妈以后再不和莉儿有任何往来,一定会专心职志地读书,考上一所好大学。在割肉的同时,我也向父母提了一个要求,我不想再住在学校里,也不想再在学校里吃饭。原因有三个:第一,我不想见到眼镜蛇,一见到他我就忍不住怒火衷烧;第二,在寝室不犯错误根本不可能,就好像在妓院不可能有贞操一样;第三,我是想给家里节省点开支。父母也希望能更细的监督我,所以就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父亲见我浪子回头,欣喜之余,给我买了辆不错的自行车。母亲也和从前一样,对我关怀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