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我的战争回忆-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咣!”又一发近急了的炮弹砸碎了我所有的梦幻,扬起的尘土迷住了我的眼睛;“炮击!”警戒哨传来了惊惶的喊叫声,我挣起身子一骨碌钻击了防炮洞,刘天明早已醒了,正抱着雨衣蜷缩在洞底,不大的洞子只能勉强塞进两个人,我的上半身子钻在洞里,下半身还挂在外边,“娘的,把你的狗腿缩回去,让我进去!!!”人在面临死亡时总会本能的害怕,总会本能的做出求生反应。还末等我拖进剩在外边的大腿,炮击就变的越发猛烈了。
整个洞子都在晃荡,洞壁上的土层不断的跌落下来,大口径炮弹激起的巨烈震波让人的五脏都涌到了嗓子眼,碎石泥块还在不停的跌落,“会被活埋的!”刘扯着变音的颤音嚷着,“娘的,被活埋也比炸死强!”我红着眼凶煞的冲着洞外叫,不知道是叫给他听还是叫给自已听。炮击开始还能听出批次,到后来根本无法分辩批次了,但是炸点似乎都固定在阵地前沿三百至五百米距离上,很少有炮弹光顾阵地,“是我军的的炮击!娘的,怕死到急点了!”当我开始肯定自已的判断之后,我又冲着洞口或是冲着刘大叫起来,“让我出去!”我的后背被重重地推了一把,但是我没有钻出洞子,无论是敌人还是我们的炮火,惊天动地的爆炸仍然令恐惧占据着我的一部分心智。我被第二次更大力的推击挤出了洞口,眼前的景象状观极了,如果说四月二八攻击老山时由下而上看到的炮火是一场宠大的焰火表演的话,那么眼前的一切就只能用不可言喻来形容了。我军的各种口径炮弹仿若流星雨般划过黎明前的深邃夜空在阵地的不远处筑起了一道宽厚绵密的火墙,各种爆炸的啸声和冲击波仿佛抽空了空气,直接撞击着人们的心房,我与其他弟兄一样大张着嘴喊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声音,挨在身边的刘也喊着一些莫明奇妙的话语,也许是方言,也许根本不是地球上应有的声音,我扭头看了他一眼,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啊:一张被兴奋紧张完全挤变了形的脸,一张糊满眼泪的脸,让人无法还原其人的本来面目,我不惊奇,因为此刻我也会是这个样的:战争本来就是扭曲人本来面目的事情,一切的奇景怪象都不再奇不再怪了。
炮击开始,越军炮兵群立即作出了反应,146/149/100高地方向传来了猛烈的爆炸声,我高地当面越军501高地及清水/汉阳一线越军炮兵火力也对662。6高地地区实施了激烈反击;炮击重点主要集中在662。6高地及103高地等处,处于我高地侧后方662。6高地整个被越军炮火覆盖了,满山植遍的火树银花照亮了整个天空,不时有越军的大口径炮弹落在高地的四周,我军士兵被迫转入防炮洞,高地右侧的一段交通壕被炮火摧垮了,邻近的哨位被越军的重炮掀开了盖,所幸的事洞中无人,不然又是一起活埋。
3时30分,我军的炮火反准备渐渐平息,连指要求高地报告当面敌情,浓密的销烟籍着夜幕完全笼罩着前沿阵地,视线差极了,能见度只有几米远,根本无法有效观测敌情,我高地向连指汇报:目视效果差,耳听范围内无异常声响。连指回复:加强警戒,其余人员休息。此时时间已到七月十二日晨三时五十分。
越军的反炮击仍然在继续,146高地方向炮火依然相当猛烈。我将12。7机枪拖进了射击掩体,刘天明还搬来了三箱手榴弹,按分配他是我的副射手,这小子全身缠满了子弹带,钢盔也不知道哪里去了,“脑袋呢,不要命了。”路过的毕志荣骂了一句。我没有理他俩,依旧趴在射击台上,销烟终于渐渐散去了,借着微白的天光,我的眼前呈现的真的是无名高的前沿吗,昨天依然挺立的石笋不见了,大片的林带不见了,炮火改变了一切甚至连地貌也改变了。我努力分辩着眼前的一切,试图查找出越军存在的痕迹,可惜连个鬼影也没看到,真怀疑我军的情报的准确性了。
五时十分左右,越军终于出现了,先是从越军115号高地、牛滚塘、138号高地前沿冒出了大批的人影,紧接着501高地也涌现出大批越军,他们越过自已阵地的前沿开始成战斗队形向我方阵地逼过来了。“敌人!”各哨位相续传来了士兵们惊恐的报警声,战斗要开始了,我的血又一次沸腾了,脸上泛着酒烫似的红潮,晨光依稀中,越军前沿人影倥惚,近了,更近了,我已经能很清楚地分辩出他们的大通帽以及手中尚泛着烤蓝的冲锋枪了。“轰!”还没容我回过神来,越军攻击队形前响起了爆炸声,手榴弹!我没有细想,扳击早已被我扣到了底,顿时整个高地响起了急风骤雨般的枪声。战斗从一开始就激烈的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自已到底打了多少子弹,机枪从一开始就没停过,这是真正的攻防战,如飞的弹雨带起一片片死亡的浪潮,不时有子弹击中我左近的壕壁以及射击台,甚至有几枚枪榴弹准确的砸在厚厚的掩体被复层上,激起了满天的碎石泥块,我分不清敌人的面目,枪口的火焰严重影响了我的视线,我只能将子弹成片的扫向越军的进攻方向,我只能从身边战友的怒吼声中判断敌人的远近;激战十五分钟,越军第一次强攻终于退却了,前沿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十具敌人尸体,还有一些负伤的越军鬼哭狼嚎着往自已阵地方向挣扎着;高地被打的糟糟的,我的射击台上堆满了弹壳,刘天明甩了一箱多手榴弹,手指上套满了拉环,他的手臂被越军枪榴弹的弹片炸伤了,幸好只是擦肉而过,我木然的替他包扎着伤口,这时我听见右侧的战壕里传来了拉风箱似的呼吸声,一个声音在边上大叫着,有人要死了!我的心仍然然没有太大的震憾,战争让人变的麻木不仁,仿佛死亡不再具有威慑似的。我还是过去看了一下,五连三排的一个兵被越军击中了肺部,血如泉涌,旁边守着他的战友,仍然是不完全的战友,他的手指被手榴弹片齐刷刷地连根切断了;几个赶过来的兵正守忙脚乱的撕着急救包替他们包扎着,我帮不上什么忙,其实也没法再帮上忙了,一分钟后,肺部中弹的士兵在喷出最后几口血后痛苦的死去了,弟兄们仍然没有放弃包扎,似乎只要包扎好他就能活过来似的。断了手指的兵喊哑了嗓子,发出一种令人毛骨耷然的呜呜声,一个弟兄正在周围满世界的找着什么,我知道他在找那一截截手指,找那再也不可能连接的手指,我无力的靠在壕壁上,我没有勇气再想下去,战争,这就是战争,黑色的死亡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也许下一个就会轮到我,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这座标号为无名的小高地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又或者仅仅是为了自已为了身边的这些同历生死的弟兄。
越军的强攻受措后停顿了不少时间,他们也在积蓄力量积蓄怒火。
6时20分,越军的压制炮火开始猛烈地捶击着我们的阵地,树被打着了,草被打着了,山被打着了!这个世界不再有明媚的阳光,只有灰色;不再有鲜花,只有弹片。我把整个人挤进了射击掩体,我的手不住的颤抖,我的心不住的悸动,越军!蚁群般的越军越过山脊线潮水似的象我军阵地漫过来,他们没有跑步,没有弯腰,甚至没有穿上衣,手中的武器扑/扑地打着点射,透过硝烟我还看清了一面旗帜,也是红旗,不同的是只有一颗硕大无光的黄星,越军的军旗!那面旗在风中飘扬,在风中翻卷,旗下是一撮端着上了刺刀的冲锋枪手,越军在唱歌!!!听不清声音,只能依稀分辩音调,军歌!亚州的军队有着不怕死的天生勇气!
“敢死队!越南人的敢死队!”不知道是谁在大喊着,高地上另一挺重机枪突然响了,弹雨倾刻间打倒了越军的旗手,军旗没有倒,越军和我们一样,有着人在旗在的决心。我的枪也响了,这一轮弹幕再次覆盖了越军旗的位置,敌人,旗手,鲜血,死亡;我报复似的疯狂射击着,我想起了郭品华,想起了四连不知名的旗手,射杀他们的敌人也一定和我此刻的心情一样。我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不能让旗子再次前进,不能让旗子再次飘扬!此时我方的炮火压制开始了,大批的炮弹径直撞入了越军密集的战斗队型中,分不清点次的爆炸构成了一条活动的火墙,一忽儿拖左一忽儿拖右,越军的伤亡异常惨重,天空中飞扬着数不清的残肢断臂,破盔断枪,我把机枪调整了射角,弹雨括风似的射向从侧翼攻向高地的越军,痛快!当兵能打上仗就痛快,打上仗就能赶上硬仗更是痛快!我把今生乃至前生后世的痛苦和愤怒都加注到了激射的子弹中。高地上下满溢了枪声炮声,天空中塞满了横飞的弹片,我军的炮火开始在我阵地前沿五十米处筑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钢铁长城,越军后援不继,攻势终于被我们扼制住了:军旗,越军的军旗始终没能前进,始终没能飘扬,尽管周边叠起了高高的尸堆,越军的第二次冲锋被打退了。
六时五十分,天早已大亮了,越军并没有停止他们近似自杀似的进攻,随着越军炮火准备的再次延伸,敌人的第三次冲锋开始了!
早已麻木的我们和早已麻木的敌人一样,根本无视子弹和炮火,人们制造死亡也蔑视死亡。越军以班为单位多层次多波次的对我高地不停顿的攻击着,倒退一波,第二波又抵上来,退下去的一波根本不回撤,仅是后退几米原地残喘一翻就重新投入狂攻。我的机枪开始不听使唤,不间断的射击将枪管烧成了烙铁状,每射击一次就发出滋滋的声音。又一发炮弹在我的近前爆炸了,这次早已千濸百孔的被覆层终于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崩塌了,我和我的机枪和我的生命一瞬间被埋进了黑暗中,我的生命要完结了,最后的念头令人绝望,但似乎老天总爱和我开玩笑,死亡被战友们拖走了,同时也把我拖回了更加残酷的现实中来。我没有分清救我出来的弟兄们,紧张的战斗让人丝毫没有时间去体味去感谢,我半爬着摸索着滚到了临近的战壕里,敌人的攻击丝毫没有停顿的迹象,失去了机枪,我还有冲锋枪还有手榴弹!冲锋枪不过瘾,就来手榴弹,一枚……两枚……三枚………………,我无法分清投弹效果,只能朝着前方朝着敌人进攻的队形机械地甩着。身边不断有人倒下,又不断有人补上来,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但是这些人的加入让我感到温暖感到安全;又一个生命在我近前怦然倒地,他的手甚到打到了我的胸口,我被带倒了,这次我看清了眼前的烈士,刘天明!他死了吗?他的身前布满了弹孔,到处冒着血,我扑上去,我试图按住伤口,但是办不到,按住这里那里留出来了,我大哭着,大叫着,我要救他,可那血,那如泉似涌的血还是不可节制的奔流着并迅速渗入身下的大地里,他就如此安静地死在我的怀里死在我的哭叫里,没有留下一句话。
近了,更近了,敌人跃进了残存的第一道交通壕,肉搏!最原始的拼杀,一个对几个,没人能分清,更多的越军扑入了壕沟,我们抵不住了!第二道战壕的战友已将手榴弹甩到了交通壕里,我拉着一个兵趁着短促猛烈的爆炸翻出了壕沟,我们疯似的奔跑着,我没有枪,似至没有手榴弹,我的念头只有一个:跑!死也不能当俘虏!当我翻身进入第二道战壕的时候,被我拖出交通壕的兵先我一头载入壕沟里,他也死了,他的头被子弹击穿了,脑浆顺着弹孔汩汩地流着;我想吐,并真的吐了。爆炸,扫射,敌人占据着交通壕我们占据着第二道战壕,敌人依着下巴喀打中国兵,我们依着鼻梁打越南兵。
十五米的距离,近极了,我们都能互相看到彼此眼里的仇恨与火焰,不断有手榴弹滚进战壕,不断有爆炸激起烟尘覆盖住身体,我死死地盯着越军蠕动的身体,身边的战友打出的弹雨紧贴着地皮掀起一阵阵尘浪;越军,蠕动,停顿;又是一阵啸声,来自身后营属100迫的火力密集而接近,炮弹下饺子似的落在高地上,越军的冲锋部队仿若人墙一般,炸倒一片填上一片。我身边的战友也被弹片击中滑落到壕低里去了,我没有管顾他,我不能停顿射击,因为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他的血溅了我一头一脸,浓重的血腥味加杂着硝烟涌入我的呼吸道,我窒息,呼吸道里火灸般的痛疼,真想死啊!活着就等于受罪!蒙胧中我忽然直起了身子,我端着枪欢快的叫着,嚷着,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啸音,炮弹!也许这一颗是冲我来的,来就来吧,死了也好,郭品华/张大权/我来见你们好不好?“找死啊!!!”我被谁猛地按倒在地,爆炸就在身后,气浪一下子推开了压在我身上的那个人,喘息,呻吟,又是一个将死的人,为我死值的吗?!我恼怒地回头,眼前的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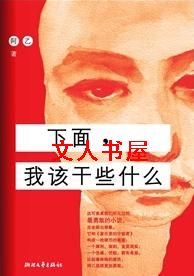
![[HP]耽美大神,我错了!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7/706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