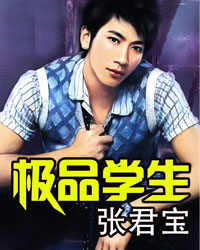女中学生三部曲-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在宁歌最后一天活着的时候,她在晴朗的冬日清晨对宁歌轻轻说一声:“你是我多好的女儿。”会有多少温馨。那这个母亲也许不会有这么重的负疚。
她却不说。她激昂起来,纷乱的长发抖动着,她说的确我从来不说宁歌好,当面从来都说反话,我是激将法,逼她更努力一点。从老辈子就传下来说棒下出孝子,大人物都是打出来的。她一直以为宁歌应该明白妈妈的苦心,应该感谢,但最终却相反。对母亲来说,宁歌走得悄无声息,对妈妈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却写了一生中最长的一篇日记,她说她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呼唤,做出了一件只由自己决定就行的大事,她平静而愉快。这种永远的对内心世界的沉默,也许不仅由于代与代之间年龄的沟。
母亲的嗓子突然哑了,咝咝地响,说不出话。她用焦灼不安的眼光爱抚宁歌,她的眼光像手一样在照片上摸,可她一定只摸到冰凉的玻璃。
她只是问:“这么好的女儿都死了,我活着干什么?”在窄小巷子的路灯下,记者为她感到十分绝望,摇着头:“我实在不知道。你一定也不愿意我说骗人的话。”她点点头,泪水从烂了的红眼角汹涌而下。
她站在那儿,比夜还黑,比厉鬼还不祥。她把一生对女儿的爱都浪费光了。世上只有妈妈对女儿才有的温存的爱,怎么也变得那么严肃那么冷酷那么社会化。如果妈妈爱女儿爱得像一道温暖的清水,为什么不这样温柔地说呢?如果不说,孩子怎么能感到爱是温柔的呢?如果感觉不到这温水般的感情,孩子怎么能不寂寞忧伤呢?如果在别人身上感到了这一切,孩子怎么会不敞开自己的心怀欢迎它呢?
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二十七岁的记者垂下头来,她看见婚戒在手指上闪着亲切的光。人生的下一个角色对于她,是由女儿变为母亲。记者在手指上转动着婚戒想:要是我有了孩子,一定要她第一知道,她的妈妈爱她视她为快乐和生命,她的微笑是我的食物和阳光。我要做全新的中国妈妈。
1985.6.25.
妈妈吃完晚饭连碗都没收就出去了,大概又要深夜不归。我走出门,独自游荡街头。
晚风扑来,里面有白天的太阳气味。突然,我觉得心里有扇小门砰地开了,涌出来一个特别熟悉的旋律:快乐童年已经一去不复返,亲爱朋友都已离开家园,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音乐课学会这支忧愁的歌以后,就特别喜欢它,有时候那小门怎么也关不上,就一遍一遍地唱,不想停。
童年真的一去不复返了。说不出童年有多少快乐,但童年时候单纯安宁,回想起来十分美丽。现在我总被无名的孤独缠绕,又不想和人说。不知道是哪儿不合适。
还有,班上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变得好看了,特别是庄庆,今年穿衬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的脖子长长的很美,手很白很细,指甲是粉红粉红的,像书里写的那种大姑娘的手。可我的手越长越大,大得不可收拾,脚也是,胳膊和腿却细得不相称,照照镜子,心里真绝望。
上次去图书馆看书,陆海明难得那样激情地讲《读者文摘》里那些激动人心的神秘的事,他说我这是一种长身体的表现,说着说着,脸就红了,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红起来,越来越红,血液在脸上似乎翻江倒海。只有这一次,他很有趣很聪明,那许多想法像天马横空般奇丽,一扫教室里的陈腐之气,连在一块的眉毛也变好看了。如果真是因为长身体的缘故,我倒巴望它快点长好吧,别再给我丢人显眼的了!可有的时候心突然没来由地狂跳上一阵,有的时候头昏得厉害,这是怎么啦?生病啦?不懂。反正我以前从来也没这样过,我有点害怕,有点嫌烦。特别是那天洗脚的时候,庄庆突然说:“啊呀,宁歌你的脚怎么这么薄这么大啊?”我举起来一看,真的。夏莉莉和丁丁使劲地笑,说我的脚很像鸭子的脚。我心里真气。发育起来,到底要把我的身体长成什么样子啦?
前面就是太阳公园。已经落栅。小时候这公园不要钱,我常来玩。英文老师总看不起我,我心里气,就逃她的课。那天好太阳,我到这儿来荡了整整一下午秋千,白色的秋千,前面有一排夹竹桃树,开满了红的花,白的花,好看极了,就是味不好闻。秋千环在头顶上咯啦啦咯啦啦地响个不停,像唱歌一样。我往里面望,在绿树丛里,真的看到隐隐约约有摇晃着的白色的东西,久违了,秋千!我心略略地跳,跳得有点发抖。我摇摇栅栏,锁住了,一股铁锈味。我真想爬进去!
四周静悄悄,只有橙黄的路灯无声地洒下许多谅解的光亮,像个和气的大眼睛。我心里一热,抓住栅栏往上爬,小时候上树的本领竟不翼而飞了,身体像木头一般重'奇+'书'+网',手和脚吊上去了,屁股却无论如何抬不起来,栅栏响个不停,有打雷那么响!我心里很气愤,退化了退化了!
远远听见有人声,我连忙跳下来,跳得脚好疼!我装作什么事也没有,慢慢往前走。秋千仍旧挂在粗粗的绳上,在风里晃荡,晃荡,晃荡。小时候我好荡高,人像飞起来一样,绿的树白的花在四周像万花筒,那真美。
心里那旋律又来了,快乐童年已经一去不复返。很惆怅。我不知不觉失去了许多,得到的和面临着的却让人琢磨不透。
人在拐角消失了。又去爬,小时候男孩都羡慕我爬树的功夫!这次爬上去了,跳到洒满明亮月光的水泥地上,绿树森森的气味立刻环绕了我,白色的影子突然近了许多,天助我也!
我向秋千跑去,满心喜欢。那树,那花立刻就会像万花筒一样了。我好像在过完寒冷一冬初次脱下棉衣,脱胎换骨样的轻松。秋千在月光下白得那么耀眼,那么美丽。连夹竹桃的气味都变了。突然,我突然看到粗粗的秋千绳上别着纸条:油漆未干。我的天!
猛然有一道手电筒光直射过来,“干什么的?’我看见一个红袖套,“干什么的?”一张核桃般满是皱纹的老脸。
“看秋千。”我说。
“秋千有什么好看!”
不知道有什么不好看。
“你怎么进来的?”他拉着我到栅栏那儿,手重极了,我拼命挣脱他的手,他回过头来瞪着我,放开手:“对啦,小姑娘,油漆未干,碰不得。”看到门没弄坏,他奇怪极了,拿手电筒上上下下在我身上照:“这么大姑娘,爬墙啊?新鲜事!”我真恨!
马路那边又听见有人说话,会不会是熟人、邻居。舅妈?我十四岁了,一米六几的个头去爬墙进夜公园,他们怎么说?不庄重?复杂?联系出生,会说什么难听的?要是再来两个男孩一块起哄,我真是死了的好!人声更近了。我一步步往暗处退。老头品过味来了,嘿地笑—声:“也知道爬墙见不得人呐!娃娃。旧社会有你这高这大,该抱娃娃了,你还爬墙打秋千?我要是你爹,不打断你腿?”
“现在不是旧社会了。”我把脸退到树阴暗处顶一嘴。我宁可像现在这样没爹,也不愿意有这样的僵板老头,祝英台的爸爸!
“新社会也有规矩方圆。”老头用手电筒照着我眼睛,怒冲冲地吼。栅栏外停下一对情人,紧紧偎依着,像鸽子一样咕咕地说着什么。老头扔下我,对他们大喝:“走开走开!”真正是祝英台的爸爸!
他拿出一大把钥匙来打开门,我挤出去,对老头呸一口,我恨他!他把我赶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一定要我适应它,照他振振有词而荒唐的法则行事,我真恨!他一边锁门,一边说“乱了套乱了套”,锁完门,他看见我还站在那儿,对我吼了一句:“还不快回家!”我偏不回家,我往前走,我就愿意我行我素。
扫兴!
1985.6.26.
进入大考,上午一连考三门,一小时一门,中午吃饭的时候,顿时发现许多人的眼角都累得耷拉下来了。丁丁有一门感觉不好,在食堂里一边哭,一边吃饭。眼泪一滴一滴打在匙勺子上,好可怜。我很自信。
何老师大而翘起的上嘴唇上,整整齐齐像化学价一样排列着一串大泡,上火了。一到我们考试,她就急得上火。她头上的头发这些天又硬了几分,白了几缕。随着考卷翻动的声音,她的目光变得非常非常敏锐。这让人觉得受到压迫。
考试啊!没顶一般的考试!
下午学校规定了体育锻炼的时间。听到操场传来像跑步一样轻松的乐曲,心像上岸的鱼又跳回到水里一样,突然一片清凉。我忍不住蹦起来,带倒旁边陆海明的铅笔盒,哗一声!陆海明吓了一跳,突然挺直身体,额头上的青春美丽痘忽地红了。我说:“体育锻炼时间到了!”他一惊一吓的样子,像个善良可爱的书呆子。突然,我看到何老师又吃惊又愤怒地瞪我。全班同学都还坐在椅子上没动弹,有的还在抓紧时间算最后一道数学题,明天一早要考的,陆海明不满地嘟嚷着用力并上铅笔盒。
校长助理在外面敲窗:“何老师,放班级到操场上去。”
何老师非常不满地瞪我一眼,说:“我知道读书苦,但没有法子,古人尚能做到头悬梁锥刺股呢,何况我们。我们要艰苦奋斗。”说着说着,她脸红起来,这是激动了,喷过来的鼻息,热得焦急。
大家三三两两地站起来,庄庆从后面挤过来搭住我肩膀,轻轻说:“堂吉诃德,烦!”
何老师跟着我们往外走,一边说:“现在争分夺秒,多复习一分钟,也许考起来就多一份把握,你们要明白。”她跟到门口,扶住教室的门框,“早去早来啊!”
丁丁笑起来:“像我妈。”
到操场上,体育老师说因为考试缩短体锻时间,但运动量得保证,所以绕操场跑十圈,男生十五圈,以后回教室继续温课。
把我们当成什么了?牛还是羊?我想跳绳!想打羽毛球!
排队时候,陆海明环顾左右后偷偷摸摸对我说:“老师是对我们负责,脾气不好,别伤心。”我却实在看不得他那鬼头鬼脑。我瞪他一眼,在分数面前,大家都变成任其驱赶的羔羊。
晚上晚自习的铃还没有响,大家就都到教室里猫着复习功课去。何老师又坐在第一排等着大家,她的脸总吃力地仰着,对每个进来的人劈头盖脸拳拳地微笑,笑的时候苦楚地缩着满是燎泡的嘴唇,她能使考99分的人都感到负疚。我不敢看她。
我实在复习不进功课。我实在是不想没完没了地做习题,我是有才能的,我要找一种充满灵气的学习方法,而这种大运动量的训练,是训练运动员的肌肉,不是训练一个中学生,特别是重点中学学生的思维能力的,我觉得。
烦极了。
星星是淡黄色的遥远的灯。
何老师突然把手放在我肩上,像纺织女工发现这匹布出了毛病,她的手火热火热。
“宁歌,听老师说你今天复习题没有抄?”我看看她,我能跟她说什么呢?“你要珍惜在龙中的学习机会。”她嗓子哑了,说话时总有从喉咙里挤出来那种嗡嗡声,“我们要求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升学率了,我们要求的是专家和出国留学的比率,你也知道,因为要求高,所以淘汰率也是很高的。”
何老师说着把一卷纸塞给我:“这是我厚着脸皮向老师借来的,丁丁说题目她也要用,我想今晚你就把题抄了,明天自己去还老师,向他道歉,你们这些孩子真不懂事啊,老师找这些题来就容易吗?”
不接是不行的,纸上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刺鼻的粉笔灰味,吸进去真难过,我拼命往外呼气,但那股生涩尖利的气味就是停在嗓子里不出来。
做吧。桌上不知哪一届的同学曾潦草地写着:学海无涯苦作舟。
何老师走了,又回来,说:“你看陆海明同学多认真,他本来就是年级里的尖子学生,但仍旧兢兢业业,希望你能向他学习。”又走了。
复习题铺天盖地,无从下手,我像只小鸟在这死寂的水面上停不下脚,潜不下心。
做吧。
陆海明做得如痴如醉。在那夕辉里眉眼间的灵气一扫而光,那时我多喜欢他!喜欢得不敢看他。但现在他变成了勤奋而愚蠢的大蚂蚁。可惜啊!
他发现我在看他,转过半个脸来威吓般地神秘得不得了地说:“这些题能捞七十分。”
我叹口气:“太多了。”
“你不想做?”他瞪大眼睛,“你看看我的!”他举起草稿纸,小小的字像蚂蚁军一样排了整整齐齐的队伍,满满五张。我的天!
我实在有点看不惯他那种样子,有点狐假虎威。
他怜惜地看我,我心又软下来。
头挑,何老师花白的后脑勺往前一冲,一冲,慢慢垂下去。她累了。我心里突然又涌起一点点柔软的东西,老师这么累,不就为我们考得好些吗?我何必呐,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