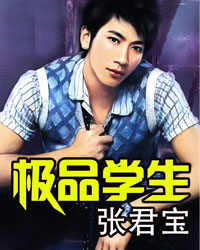女中学生三部曲-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母亲看见庄庆脸上又显出惯常的出神来,母亲懂得女儿那个反抗的不服管教的心已经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只是由于母亲最后的权威,她的躯体还温暖地拘束地留在这里。看着亲手养大的女儿,母亲十分心酸。她把桌上的饭盒朝发愣的女儿推过去:“哪,这是给你准备的,你不想着我,我却想着你。”
庄庆犹豫了一下,很不情愿地拿起一个生煎馒头,馒头还是热的。她瞥了母亲一眼,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心里有一点负罪感正在化开。母亲哼了一声,说:“吃饱了更有精神来气我啊。你们庄家的人少长了一颗心啊。你先吃,吃完了我们接着说。”
庄庆用牙齿慢慢磨着生煎馒头上的白芝麻,母亲的追问终于是没结果的。她的脸从愤怒变得空落落的。她把吃空的饭盒收拾起来,拿起包走出门去。庄庆跟在她身后走着,可母亲并不理会,庄庆简直像个垂头丧气的、被抓获的小偷。母亲整个脊背上都写着失意、气馁和哀伤孤独。她头也不回地走进春天的阳光里。校园到处都挂着亮晶晶的水珠,好像还听见了鸟儿的呢哺。庄庆在学校门口停住脚,看母亲走进广场,心里滚过从母亲身边解脱出来的轻松、刺伤母亲的内疚和对母亲的惋惜。她看母亲,像看一个不幸而且不祥的物体,怀着背弃的隐约希望。母亲一天天衰老枯黄,而庄庆一天天欣欣向荣,像花一样绽开。
广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母亲孤单单的身影长长地斜在广场上。
庄庆用心地看了看,没有男孩。也许以为女生们都回家去了,一到下午返校时间,这些人又会出来,像蚂蚁牵线一样在广场上来往。
金色尘埃
今天下午放学以后规定是劳动日,春天到了就种树,在礼堂前的一块空地,包给了高二(1)班。走在去礼堂储藏室拿工具的碎石砖路上,有人哎哟哎哟地叹息,说都什么年月了,还得劳动。
储藏室很小,庄庆进去“砰砰”地开窗,才得见阳光。曾惠心想,恐怕解放前是连着礼堂的祈祷仟悔的密室,可她当学生的时候从来没发现过。庄庆从狭长的门里挤出来,“呸呸”地吐着什么说:“这里面气都透不过来!”她拿着一个又大又重的喷水壶,扛着把铁锨,摇摇晃晃住空地上去。她把冬天的高领毛衣脱了,露出捂得白白的脖子,像只撒欢的小狗。曾惠远远看着她。
曾惠是最后一个走进储藏室的。这时的储藏室射进一道阳光,阳光里飞舞着许多细小的金灿灿的尘埃,通过活泼的尘埃,曾惠突然看到木架上堆着许多生锈的大把剪刀,老式的铁剪,碎砖一样堆在架子最高一层。
这剪刀是曾惠熟悉的,她探过身去取下一把仔细看看,没错,红卫刀剪厂的,没错,也许这把就是十多年前她用过的。那时这剪刀都是才出厂而且到处都买不到,像白皱纹纸一样突然就买不到了。那个冬天,周总理逝世,学校唯一的一棵松树被各班你砍一枝我砍一枝剃了个光杆。各班都不上课了,做花圈,心头凄凄,充满不祥的无助的预兆。那时还是男女合校,男生一下子懂事起来,买剪刀和皱纹纸都抢着去。班长是个矮个子但眼睛十分严肃明亮的男生,那天他抹着鼻血走进教室,后面的男生扛进来最棒的松枝,茂密而且修长。那时曾惠负责剪纸花上的长瓣。讲台早已移开,男生们竖起一个直径有一米半多的花架,女生们要做上千朵小白花。
对一九七六年的十七岁孩子来说,从来没见过老师失态的同学们看到他们一个个哭得要命,教导主任抽着肩膀,像小女孩。大人和老师们默默的忧愤沉重使他们突然懂事起来团结起来,心里也怀着对整个国家的担忧,虽然这担忧是模模糊糊的,但足以煽起少年心头的苦苦寻找世界的答案和揭竿而起的热情。有时候一个危急的关头,像点燃了炮仗的捻子,少年们心头对激情勃发的生活和对英雄崇拜那本来潜流般流淌的东西会喷发而出,突然之间光灿灿直射四方。
曾惠一直暗自认为那以后的几天,是她一生里最干净最灿烂的日子。曾惠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团员,但她知指挥起全班女生做花圈。她心里激荡着担负起国家兴厂的热情和悲壮。那时哥哥们已经插队的插队,当兵的当兵,她有个单独的小屋,她在桌L做了一个周总理的灵堂。临睡前,她看着周总理那么神气地微笑的照片,常常热泪滚滚,怀着决一死战的决心。每天早晨,她都拼命改正贪睡的习惯,起来做早操。那是一种志愿贡献出自己捍卫什么的少年的激情。
一月十三、十四日,为周总理追悼会准备花圈和自发的追悼仪式到达了高潮,走在街上常常能听到哀乐。以致曾惠现在永远不会忘记的曲调之一,就是哀乐,规定的全国禁止娱乐活动的三天早已过去,但曾惠还时时警告着自己那爱随口哼歌的嘴沉默。
但全校接到严肃警告,十五日追悼会不准学生上街搞追悼活动,不准去市委参加追悼活动和送自己做的花圈。老师毫无表情地宣告这个通知,她的眼睛却不敢看怒目而视的学生。
曾惠眼里一下子涌出了泪水,她觉得如果现在有个秘密组织派她去杀张春桥(她坚信一切坏主意都是电视上看上去没有一丝笑容的张春桥出的),她敢杀人。这时,坐在她前排的班长转过头来,说:“曾惠,我们把班上的团员组织出去送花圈,你敢吗?”
曾惠泪水模糊地看着班长长出一排金黄绒毛的嘴唇使劲点头,突然抽泣了一声。老师像受了惊吓似地看着曾惠,班长压低声音吼:“哭什么,没出息,干就是了!”
下课等老师一出教室,班长就对团员说了这事,他压着声音说:“有种的明天上街,没种的别出声。”谁知道全班同学都要去,平时调皮捣蛋的男生也争着去。
班长通知好十五日一早大家分头去操场树林,那里从来就是全校没人去的地方,在那儿向花圈上的周总理像宣誓,然后抬花圈走到市委去。
十五日是平常的一个南方冬日,没有阳光,阴冷阴冷的。曾惠领着全班对花圈宣誓,花圈很大,很白,围绕着洗干净的绿色松枝。誓词是班长写的,曾惠直到现在还保留在她最珍贵的一个盒子里。誓言简单而且充满了七十年代的夸张言语和政治套话,但曾惠能体会到在这样的外衣里蕴藏着的一颗真诚勇敢而悲哀的心。她读着放声大哭,班长的声音没有跟上来,她看见黄土上落下两滴水珠。
接着他们抬着自己做的花圈出校门去。走出校门他们才发现老师默默地跟在队伍最后。路上他们看到有两个装着花圈的卡车过去了,有队伍过去了,大家都不说话,只是走。
市政府门口集满了花圈和队伍。班长举着学校的红旗走在最前头。大人们纷纷让出路来,曾惠和几个一路没轮上抬花圈的女生突然从队伍里跑出来,紧跟着全班女生都从后面一拥而上,冲散了男生准备保护她们的队形。她们从男生手里接过花圈,曾惠感到有利扎进她的手掌,而她竟在这刺痛里感到了愉快。男生们手拉手围着她们走。老师跟在后面,泪流满面地向让路的悼念队伍致谢。……曾惠抚摸了一下粗糙的剪刀柄,全身沐浴在那金色的尘埃里。
突然,她看见潘莉莉的脸,她眉毛修长,还听见她说:“你倒会找地方躲啊!”她以为是幻觉。曾惠环视着到处都是怀旧到处都散发着过去气味的小储藏室,一时不知道身在何处。
窗外空地上已经零零星星竖起了几棵树苗,徐亮扯直嗓子在埋怨:“人都到哪里去了?到评奖学金的时候来了,劳动的时候都溜了,人也活得太精明了!”方欣欣和庄庆都埋头挖着地。
曾惠猛地醒悟过来,刚才潘莉莉说的是自己,自己不正藏在这充满金色尘埃的小屋里吗?她连忙拿了把锨,跑出门去。
徐亮看见她,哼了一声,说:“到底叫出来一个,你们倒聪明来!干脏活的时候统统溜了。”
曾惠找了块地挖土,一边说:“我真不是躲,我要躲就躲到底了。”
通往图书馆红楼的小路上有人影小跑着闪过,眼尖的徐亮大吼一声:“潘莉莉!潘莉莉!回来种树,潘莉莉!!”
庄庆突然直起身来向徐亮喝道:“你怎么也像个女人似的?干自己的就是,她们爱怎么就怎么!”庄庆突然顿住,扭头狠命挖土,全然忘记了刚才学会的正确姿势。曾惠感觉到心里有什么动了。那是种共鸣。曾惠挖着土,土一层层地从地上剥去,坑深了,土越来越潮湿,那是星期六晚上的雨水还没有散尽,有红色小虫急急爬出。曾惠努力分析着庄庆和自己秘密地息息相通的感觉是怎么来的,现在,从小屋里出来,这感觉越发强烈起来。前方有一团亮光,好像一直骚扰着她的答案就在前头。和庄庆接触的一幕幕飞快地在曾惠眼前闪来闪去,可她就是抓不住心里已经感觉到的东西,她只是感到这是她理解在庆以及金剑党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她看出了破绽却阻止了她去教导主任办公室的那个东西,这东西伸手来抹开本来已经沉睡了的少女时代的眼睛。
这时,曾惠正在听着自己向那团亮光飞奔而去的脚步声,虽然有什么轻轻挤了她一下,是庄庆提着喷水壶去提水,那些女生种好树纷纷散去,可树苗不浇透水,等于不种。曾惠扔下铁锨追去,和庄庆一块提那个笨重的喷水壶。她们沉默地走到水龙头那儿,水流在空壶里闷闷地响起来,打得壶底冬冬地响。曾惠心里挤满了和庄庆此时此刻的同情和共鸣,突然她觉得自己补到了那东西,她看着庄庆削得短短的头发看到她漂亮的粉红运动服和富豪鞋,想:一代一代那么不一样,只有十七岁在心头鼓起又落下,落下再鼓起的追求不变,十七岁向在激情勃发的生活,这向往是永远的。这青春的激情在和生活腐蚀过的心情拉锯。而打群架的金剑党,是这激情的一件不合身的外衣吗?
曾惠感动而痛惜又有些怀疑地看着庄庆,庄庆却错误地理解了她的眼光,她以为是好不容易找到了知心朋友的感慨。远远往空地上看,树倒是都种起来了,但最后只剩下了金剑党人,还有这个凭直觉也会合拍的曾惠。在庆愉快而安慰地看了曾惠一眼,心里暗暗说,感谢上帝,来了一个新同志。
她们合力抬着水壶向空地走去,水在壶口啪啪响着,散发着清凉湿润的气味。在春田阳光里嗅着这气味,曾惠和庄庆都感到接下去必须发生点什么了。
夜自修通常都是做作业和读书。这天的夜自修曾惠刚坐定拿出书来,庄庆的手肘就向她亲热地伸来,撞撞曾惠的胳膊。那次夜自修她们一直在聊天,庄庆说她最喜欢太阳,最盼望马科斯和阿基诺打起来,将来最可能爱上的人,是敢说敢做剪小平头的男子汉。她爆发出的热情使曾惠尴尬。她总觉得自己是走进别人家密室的小偷,要被乱棒打死。她只是诺诺地应着,听到庄庆说到金剑,她心头一跳,赶紧转开眼睛,而庄庆却以为曾惠是没有反应过来。她特别再细细地解释,从前在一本画报上看到介绍,好像还是庆祝反法西斯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据说在波兰,犹太少年中有一个反法西斯的党,叫金剑,他们写反法西斯的传单到处散发,四处活动参加救亡组织,他们的标志,就是一把朝天竖立的金剑。金剑象征着正义,斗争和英雄主义。最后,金剑党被破获,全被杀死在集中营里了。画报上还有他们被害遗址的照片,是一段矮墙,墙上爬满紫色的小花朵。金剑是一种高尚奉献而且勇猛不屈的标志。庄庆用狡黠又充满希望的眼神打量着曾惠,她想唤起曾惠心里的正义感和好奇心,启发曾惠崇尚积极向上的激情。在她看来,她应该发展曾惠,而本来悟性很强的曾惠对她的启发总不开窍。
其实曾惠与庄庆最初认同的亲切过去以后,立刻被庄庆的热情推进慌乱之中。曾惠发现教导主任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她们班附近,她的眼神一次比一次焦躁,曾惠只是拿准希望能为庄庆开脱。但她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不出卖庄庆又完成这入学考试似的任务。庄庆的热情使曾惠预感到了金剑党正在伸出双手欢迎她,她却对庄庆的信任十分恐惧。从心底里来说,她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参加进去。她埋下眼睛,只管装聋作哑,心里又紧张又为难,又感动又慌张,一直把成年以后还能重新唤醒自己的少女时代视为奇迹的曾惠,现在开始受它的煎熬了。
曾惠的装聋作哑却大大刺激了庄庆也刺激了教导主任,她们都觉得曾惠对自己是全心全意的只是没明白她们的意思,于是拼命明显地暗示。而这样的暗示越发使曾惠为难,她开始在可以说话的时候尽量多地找出奇奇怪怪的话题堵住庄庆的嘴,把话题引开,而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