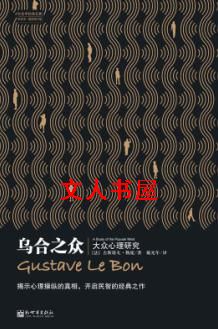卤煮研究生院-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邓的回答就只有这两个字。细细品来,的确回味无穷,“等待”,既是种示弱,又隐含着示威,只有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人才敢平静地看着年华慢慢老去。
“那大约要等多久呢?要是过了很长时间他还不……”中国人做事最喜欢预先找好后路,就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希望就在脚下,又怎么能指望幸运女神的眷顾呢?
“如果能预先知道成功有多远,那就不叫等待了,充其量算个中场休息,”袁莱笑笑:“死是容易的,活下来才需要勇气。”
《三十六计&;#8226;李代桃僵》里讲到:“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大千世界中,最常遇到的情形往往不是是非之辨,而是高下之别。虽然王佐断臂并没有舍鱼而取熊掌那样实惠,但常人大都还能懂得丢车保帅的道理并忍痛割爱地实践之,可对于过分洁身自好的那些唯美主义者来说,任何不如意都是致命的,不论多少。诗佛王维每天要把屋子清扫几十遍,自己忙不过来,又打发童仆跟着一块儿折腾,加上那会儿轻工业生产效率较低,有时连扫帚都供给不上,结果把正事儿全给耽误了,正常人为了全勤可以省去刷牙洗脸,王摩诘却宁愿让安史叛军逮着也舍不得离开他的宝贝别墅,大概是怕自己跑了没人定时扫地,果然是轻重不分的典范。
多数情况下,即便不能保住万全,却也至少可以维持下脆弱的平衡,但进退维谷的窘境毕竟在所难免,每当此时,袁莱便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其实他刚刚听说这对师徒的韵事未必风流那会儿就险些把煞费苦心的治疗成果付诸流水,好在亲疏有别,出于复杂的历史纠葛,袁博士向来对魏一诚的夫唱妇随持保留意见,也就顺势与远航结成了天然盟友。其实,咱们这些普通人也一样,为了保持乐观和自信,无论盲人摸象、甚至掩耳盗铃,都不失为备选答案。事实上,陆远航之所以会不辞劳苦地大老远跑来进行咨询,袁莱的态度恐怕至少是其中的必要条件,良药也未见得非得苦口,偶像加实力才能人见人爱,即便是统一战线也得先辨别青红皂白,用毛主席的话说:“分清敌我友乃是一切革命的首要任务。”
“但愿魏丹能正确对待这件事情,”很明显,袁师兄不可能想当然地把误伤作为战争的必然代价而无动于衷:“相信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儿,会明白爱与亲情的关系,”其实我们内心的都存有多多少少的洁癖,比如对性本善的基本假设,或许,这才是对人类道德本能的最好解释:“她都十几岁了,已经能做出独立的判断,不会有什么问题。”
远航垂着头,看得出来,尽管曾经以及正在让自己坐立不安,但她对魏姑娘所流露而不是表现出的关心并非仅仅出于自身战略目标之考虑。很多时候,qi书…奇书…齐书无意的伤害往往会比蓄谋更难以弥补,既然连始作俑者都只是被命运附体,恐怕就更没有谁知道该如何让灾难回到魔盒里了。
或许是长期与精神医学专家们捉迷藏的结果,自始至终,袁莱一直坚定地认为,陆远航之所以会和富于成熟男士魅力的魏老师“关公战秦琼”,与她那位长期从事工科研究而秉性沉默寡言的父亲有很大关系。弗洛伊德的分析学派认为,孩子从出生到成年完全要经历若干必不可少的心理阶段,而其中任何一环的缺失都将导致或明显或潜在的人格障碍,比如与直系双亲交流不足就被认为是恋父或者恋母情节的罪魁祸首。实践证明,虽然假设多于实证,但这派观点的解释力极强,否则也不会从它诞生伊始便统治心理医学界至今。
“我大概该回去了吧,”浮云正在不知不觉中渐渐聚拢,袁博士抬了抬嘴角、淡定地站起身,他身形清癯,但看起来却比实际还要高些,已经发白的病号服在微风中有些摇曳。
“其实道理我都明白,”远航还是那样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只是总觉得……怎么就偏偏让我给赶上了……”
“你该感到幸运才对,”枕流终于打破了难得的沉默:“这个世界上,总需要有人用生命的长度去丈量忠诚与背叛之间的距离。”
袁莱转过身,这次,虽然稍纵即逝,但男孩儿发现,他盯住了自己的眼睛。
十二、共枕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娶妻娶妻,挨冻忍饥。
能让女人过上“伸手张口”的日子才算好老公,而讨媳妇却更关注脸蛋和三围,两性在择偶中怀着不同的目的和标准,千百年来,我们始终把这当成天经地义。在多数情况下,男人显然更加欲火焚身一些,而女性则恰巧可以借此实现温饱、小康、乃至先富起来,可后者别高兴得太早了,审美这个东西的半衰期比贵重金属要短得多,用不了太久就会“总把新桃换旧符”,还别抱怨命运不公,恰恰相反,正如你当初掰着手指头计算崇拜者们孰长孰短那样,既然大家玩儿的是同一种游戏,就得愿赌服输。很多年轻姑娘以市场经济的模式选择老公,却指望后者对自己有着宗法式的忠诚,这不是做梦么?
达尔文告诉我们,之所以始乱终弃的悲剧会重复上演,说到底,还是进化规律在作祟。两性对“那件事情”的不同态度的确是造物主的鬼斧神工:设想一下,如果善男信女都效法大熊猫、成为禁欲主义者,恐怕人类种群难免会像后者那样日薄西山;反过来,倘若红男绿女全干柴烈火似的二一添作五、扒拉脑袋算一个,大概用不了多久,咱们一窝不如一窝的后代就得都让狼叼去;飞禽走兽的性伴侣之间并没有太多忠诚可言,它们就是借此才保证种群最优秀的基因得以一脉相承,只有男女在择偶标准上的分工合作,才能既让传宗接代的冲动连绵不绝,又不失精挑细选的消费者权益保障。当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从来未曾走向过文明,不论虚伪的道德看起来有多么天花乱坠;更有甚者,我们正是因为把这个无耻的法则发挥到极致,才牢牢占据着进化链条的顶端。而这一切的记忆,都被烙在了血液深处那串花花绿绿的DNA密码上,就像囚犯脸上洗不去的刺青。
原罪。
那天,当枕流和远航告别铜墙铁壁的“医学禁区”返回学校时,因为不再火急火燎,二人决定改乘轻轨,一路上瞻仰着沿途正在被钢筋水泥逐渐吞噬的城乡结合部。大概是经过咨询疏导后心情不错,远航的话明显多了起来,据这位“内线”透露,多年前,相思公子扬轻羽,袁莱也曾拥有一位琴瑟友好的“你侬我侬”,属于那种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美学典范(要知道,十几年前的情侣可不像如今那些只为在穷极无聊的校园生活中找个乐儿的男男女女),本已经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关口,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擦肩而过。令陆远航颇有微辞地是,即便不能守住“insicknessandinhealth(教堂结婚誓言‘无论健康或疾病’)”的海誓山盟,至少也该给人家一个哀莫大于心死的时间,可那位一直被寄予厚望的准新娘却干净利索地良禽择木而栖,没过多久就和某贼心不死的追求者比翼双飞,据说在爱河里过得还不错。
就像在我们身边上演的那些日复一日,这又是个俗套得不能再俗套的故事。
“哦,那是…”晚上,枕流见吴雨像往常一样给自己收拾书包时拿着意外掉出的垃圾袋和湿纸巾发呆,才想起分手时忘了把这两件“法宝”还给远航,毕竟,女孩子玲珑的背囊里也装不下太多的零七八碎:“那是我在超市顺手买的,您用吧,”陆远航反复交待过,今天的所见所闻不足为外人道,尤其是和与院里有关的那些七嘴八舌,最后又重点叮嘱他万万不可告诉吴雨,并一本正经地威胁说否则就会永远失去武陵溪畔的那座桃花源。要不是明显感到远航似乎有更为多姿多彩的水下冰山并未一吐为快而打算继续探个究竟,徐枕流真不愿意和可爱的小吴老师“同床异梦”。
“以前…以前没见你用过,”吴雨的表情变得很不自然,她把这意外发现塞进最底层的抽屉,其实这个少人问津的角落并不是此类日用消耗品通常的所在:“够用的,下回别再买了。”
枕流这才注意到,家中使用的是种不很常见的蓝色垃圾袋,且始终如一、从未更换,据说只有在几站地之外那家舍近求远的小超市里才偶尔出售。
王朔老师有本书叫《无知者无畏》,的确,很多恐惧是要等到痛定思痛之后才会显出它的威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想起来就觉得后怕。”经过通天观医院半日游后,枕流同学的心情整体上还算不错,这种百闻不如一见的“奇观”原先只在传说和笑话中存在,没想到果**之大无奇不有。在这样一个“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的新时代中,报刊媒体当然不会把可以换成现金的宝贵版面拿来大煞风景,而信息照耀不到的角落往往都有着丑恶得以滋生的土壤。
徐枕流虽没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般的历史使命感,但还是多少有些为那似曾相识的袁师兄牵肠挂肚,否则仅仅在病区门口有过一面之缘的“白大褂”也不会到梦里来“出诊”,弄得他辗转反侧,闭上眼似乎就能听见个喋喋不休的沙哑女声:“你是不是失眠啊?嘀嗒,嘀嗒…有多长时间了?我们这儿条件很好的,脑立体定向深部核团伽马刀、无麻醉周身抽搐电击休克仪,全是美国货,来了就睡着了……”
“你怎么了?”见客厅地灯开着,云髻半偏的吴雨踱了出来,从依然泛有微光的双眼判断,她似乎也没有很快进入梦乡。
“没事儿,”虽然细语悠扬,但心里有鬼的小胖子还是吓了一跳:“可能是兴奋过头了,不太困,”事到如今,白天的“绿野仙踪”就更不好和盘托出了。
“害怕了吧?”她半坐到枕流沙发的扶手上,抽出张面巾,轻抚着男孩儿布满汗水的额头:“都大小伙子了,至于么?”
“没有,”尽管知道自己那点儿起子从哪个角度说也瞒不过了如指掌的小吴老师,但还是在口头上维护着四项基本原则:“我看会儿电视,马上就睡。”
“都一点多了,”她并没有抬头看近在眼前的那座老式挂钟,大概是有备而来:“大期末的,你明天还得上学呢,”随着一阵清香,吴雨起身、拍了拍枕流:“你到我那儿睡吧。”
天地良心,虽然曾经多次密谋,但这回他的确不是装的,正所谓该是你的想跑也跑不掉。徐枕流明白,此时片刻的犹豫或推辞都会搅浑原本见底的一泓净水,也便顺势“恭敬不如从命”,但以前的那些狼心狗肺却都不合时宜地来让此刻的心无杂念变得充满负疚,看来阴谋诡计的确要不得,连想都别想。
最初换岗那会儿,吴雨本想还回自己原来的小屋而把双人床让给肉大深沉的胖墩儿,但枕流却以刚刚睡惯为理由抵制了这一倡议。其实,他之所以如此布局,虽算不得险恶,但也决没有那么轻描淡写,个中原因还是离不开那架愈发拥挤的合用衣橱,也为了你来我往中能多些抬头不见低头见。果然是成事在天,尽管算尽机关,可枕流还是万万没有想到,当初的小九九竟会有如此香艳的后续作用。
怀着如此鬼胎,等真躺到吴雨身边时,徐枕流自然是更难入梦了,尽管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可事到临头时,却往往要紧张得手足无措,倒不如一张白纸那样的平常心。尽管佳人在侧,可小胖子却要比刚才更加左右为难,在自己床上好歹还能辗转腾挪,到这里却连个姿势都不敢换,憋得全身都难受,只好机械地调理着那忽快忽慢的砰然心跳。据说举重运动员平时的训练成绩都高得出奇、二流选手也能和世界纪录平起平坐,可真要走到镁光灯下就难免大打折扣,无论是谁。因此,大赛时三次宝贵的试举机会中,与其说是在拼实力,还不如说是在比心理,也就是所谓的实战经验。
“这样还害怕呀?”吴雨原本背向男孩儿侧卧,听到沉重的呼吸声久久难平,便转过身来,逆光的黑暗中,依然能分辨出她朦胧的双眼。
“不是,我…”尽管已经习惯性地把一条腿晾到被子外面,但枕流还是能感觉到自己潮红的双颊如何发烫,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解释。
“你呀,”小吴老师笑着将枕头向上拉了拉、右臂越过头顶环到男孩儿肩部,又顺势把他向自己身侧靠靠:“你多大了?”
卧室里弥漫着阵阵柠檬清香,似乎来自“Glade”品牌的某种室内雾剂,枕流记得,这个词原指森林中的开阔绿地。不错,此时此刻,就像是沐浴在秋日和煦的阳光中,温暖而不燥热,渐渐平静下来的他似乎坠入云深不知处的太虚幻境,好像回到了孩提时玩闹嬉戏的游乐场,又像是花季年代尽情追逐的午后……
再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