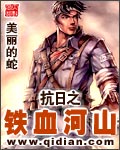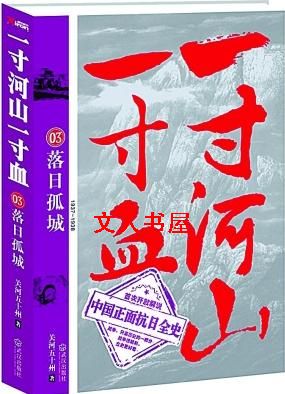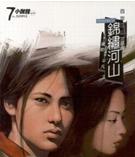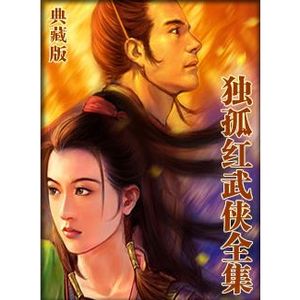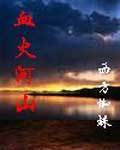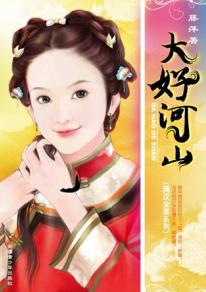一寸河山一寸血-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光像一把无情的刻刀,会改变每一个人的模样。
抬头仰望,似乎只有满天的星斗才记得那三个年轻人曾对天发下过的宏愿,也才记得他们曾有过的理想和友情。
黄郛被迫辞职后,心情异常苦闷彷徨,乃至于四顾茫然,无所适从。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曾经去过的莫干山。浙江多佳山水,然而在他的印象里,莫干山却是一座既不秀丽,也不雄伟的土山。
但也许恰恰是这一点,符合了黄郛当时的心境。
于是他走进莫干山,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隐居生活。自进入这座大山起,黄郛就决心不再从政,与政事一刀两断。
他疲倦了,真的疲倦了。
山水看似没有生命,有时却要比人可靠得多。
让所有的伤心都远去吧,让所有的诺言都成为青春的祭奠,我只有莫干山。
黄郛夫妇与莫干山结下的不是一般友谊,那是生死之交。他们走过山里的每一条小径,认识周围的几乎每一个人,莫干山渐渐成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此,知我者,二三子。
——《亦云回忆》
然而这一对神仙人物却终究没能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隐退江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艰难的选择
打破平静的是“九一八”,从这之后,黄郛开始重新关心时事,并为山河的破碎而深深忧虑。
这时蒋介石的征召书来了,要请他出山,可是黄郛不为所动。
蒋介石亲自发去一封电报,言称:为了我们之间30年的友谊,你不应该推却。
黄郛复电:欲保30年友谊而不败,我们就不应该再共事!
济南那件事给黄郛的刺激实在太深了。现在请他,给人感觉,就好像蒋介石是不小心口袋漏了一个洞,把棋子给丢掉了,现在日本人出来制造麻烦,终于又想起了他这颗棋子。
可我不是棋子,我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请不要随随便便把我丢掉,也不要随随便便把我再次放上棋盘。
不仅蒋介石想到了黄郛,汪精卫也想到了,但是两人谁都请不动这棵大树。
黄郛如此热门,并不是因为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而是蒋、汪都知道,黄郛有20年从政经验,对日本国情又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在当时无人能及,并且他还不是国民党员,个人身份相对自由。
概言之,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之相安”的不二人选。
见黄郛这么难搞,蒋介石也很无奈,只好用上了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
他不停地给黄郛发电报,除唠唠叨叨重叙友情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抄录自驻日公使的往返电文,为当时政府一等一的顶级机密。
蒋介石这么做,其实就是一种亲近信任的表示,他希望借此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也使黄郛慢慢适应和进入角色。
这一办法果然有效,一方面是黄郛本身就有一种担天下兴亡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他确实看到了此时的蒋介石有多难。
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后,蒋介石在给黄郛的私人电报中几乎用上了哭腔:举世处境最艰苦的,就数你弟弟我了。
黄郛的心软了。
终于,他答应蒋介石,时隔多年之后,双方再见一次面。
沈亦云知道后极力反对,这位极其聪明的女子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而且认定他们平静的山居生活将就此结束。
这是你的那位义弟在“请君入瓮”,你知不知道?
济南案的遭遇还没有受够吗,日本人的事非常麻烦,不要再去过问了,你只会因此白白受苦。
可是黄郛还是去了。夫妇二人从来夫唱妇随,到哪里都结伴同行,唯有这一次,沈亦云并未随行。
她的预感是对的。蒋、黄见面之后,黄郛果然再难脱身。
“黄先生”又成了“兄”,“蒋先生”又成了“弟”,蒋介石承认自己以前有亏欠兄长的地方,并重新把铸剑上的那句话搬了出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我做弟弟的现在有极艰难之处,哥哥你一定要帮我!
这个世上,哥哥帮弟弟,确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黄郛重回莫干山,已经是为北上打点行装了。
沈亦云深知华北局势的糟糕程度,她悲伤地对丈夫说:你这一去,必定是焦头烂额。
此时的黄郛已经50多岁,身体并不好,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而山外的那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多得数不胜数。
黄郛沉默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
此行“非仅为弟,更兼为国”,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事外逸民”,国家一旦垮下来,覆巢之下并无完卵,我们将无山可入。
不作努力,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尽力了,则心安无怨!
第2章 知己知彼
黄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他几乎一无所有,能依赖的,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当时中国外交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重西洋,轻东洋”。所谓“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就像普通国人一样,基本都浮于表面。
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
到了“九一八”之后,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都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没有,在野也少有。
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过招?
为了知彼,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哪怕是到“旁门左道”中去扒拉。
在黄郛的政整会中,“日本通”占了一半。这些人以殷同、李择一、殷汝耕为代表,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或为名士所不屑,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辈在刺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有的甚至还是超强。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若无“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
世间万物,但尽其用而已。“鸡鸣”也罢,“狗盗”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让他们出轨,则事无不成。
换句话说,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20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
政整会的另一半,却不是人才,岂止不是人才,有的还是蠢材、废材、垃圾。
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不得不如此。
黄郛对国内情形的认识十分清醒:在华北,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只能退不能进,对内则尽扯后腿,胸脯拍得震天响,谣言造得满天飞。
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在旁边跟你捣乱,黄郛的办法是拉住那些跟他们有联系有交情的“皮条客”,实行以彼制彼。此类人物以王克敏为代表。
过去黄郛做官,在选人用人上向来不肯苟且,更不容许冗员的存在,如今也只好尽量往政整会里塞人,哪怕是把这个临时机构塞得满满当当。
1933年5月15日,黄郛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后者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挂了,那可实在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
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雨,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黄郛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对方能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因为不久前关东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滦东之战,东北军再次溃退,兵败如山倒,日军即将兵临天津城下。
黄郛到了北平一看,那里还要紧急,已经三面被围了。
在华北军事会议上,出席的大部分将领都对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只能以小时计。
徐庭瑶从南天门撤出,三个主力师伤的伤,残的残,连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强。
29军刚到喜峰口那会儿,还“进时如虎”,自丢失喜峰口后,便“退时如狗”,等到第二次滦东之败,士气已一蹶不振,到了“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的程度。
倒是因丢失冷口而颇受非议的商震,在会上答应再守一天,成为全场最能负责的人!
原先的“双巨头”何应钦和黄绍竑束手无策,连军队都指挥不动,大家眼巴巴地都在等黄郛拿出“脱困之法”。
黄郛的策略,就是联系日本外务省中的“稳健派”,展开停战谈判,以期获得喘息之机。
事情其实已进展得大体有些眉目,不料外交部突然取得的一个“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向国联告状无效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宋子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上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须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能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中的“强硬派”重占上风,他们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面对面谈,背地里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毫无诚意。
谈判大门突然被关,黄郛对此始料不及,前期的所有努力也全部付诸东流。
打仗打不过,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华北形势只会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600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大一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担保之一的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他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无兵的黄郛,到北平后的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象,但就在这种困境下,他仍然天天召集“门客们”开会,苦思良策,乃至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
第3章 鸡鸣狗盗
5月22日,看到大势将去,黄郛决定撤离北平。
众人打包的打包,装箱的装箱,只有黄郛自己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中午,他接到了李泽一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中,李择一显得非常紧张和神秘,要求黄郛赶快跟他到一个地方去,而且身边不能带任何人。
黄郛听罢,放下话筒,返身急出。
直到第二天凌晨,黄郛才返回公寓,他的精神极度疲惫,然而含笑告诉人们:可以不走了。
多少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日本方面同意停战谈判!
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孟尝君被软禁在秦国,并即将面临杀身之祸。这时他派出了一位善于钻狗洞偷东西的门客,后者盗来狐白裘,献给秦王的妃子,从而化险为夷,这就是所谓的“狗盗”。
李择一本人名声不佳,却长于刺探日本情报,几乎就是传说中“狗盗”的化身。他得到绝密消息:原先反对停战谈判的“强硬派”突然又软了下来。
软是没有办法不软。因为“强硬派”之所以有底气推翻“稳健派”,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像“满洲国”一样,自己复制一个“华北国”出来。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