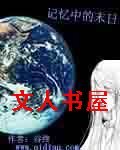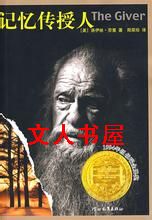记忆与现实交错-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转眼,已经是父母了,有了他们的小谦谦。
心情愉快,往车边走,提醒背包的爸爸留出奶瓶。
主动开了车门,把孩子的大提包放进车里,手习惯的挡在车门顶,怕她又会撞到头。
藏青色的小杉,弯腰要跨进车里,露出腰线上一点点肌肤,白白的。心里东西太多,只想赶紧带她们回家,好好抱一下,从见面到现在,还没有抱过,碰也没碰一下,怕吵醒孩子。
可面前的身子一滞,回过身来,脸上表情古怪。
不知她想什么,总之手臂伸出去的时候,话赶到了一起。
“给你抱!”
“给我抱!”
“老刘,慢慢开!”
一听参赞的口气,老刘刚想踩点儿油门又收回了脚。车子已经过了交流道,在最慢速的一侧稳当当的前进。
高速公路已经慢慢延伸进市区,总是飞,对这样的景色已经习以为常,多是拿着文件读上一路,现在则不同,臂弯里软软的小身子,移不开目光。
手指在毯子的流苏上滑动,碰到她的,相视一笑。
睡着的眉眼很像多年前的亦诗,穿着黑色的蓬蓬裙,裹一件裘皮大衣,躺在他怀里,哭得太累,倦倦的闭着眼。
需要被保护,嘴角永远藏着读不懂的脆弱和坚强,六岁的亦诗失去了母亲,现在却长大了,他们有了孩子。看着她的笑,知道其中包含了太多争取、放弃和眼泪。
十二岁,她允诺了未来,原来一笑了之,可十八岁再见,心里被深深震撼,随着陷入其中。现在完全相信了,也得到了。千头万绪,除了幸福又多了一丝伤感。
“别紧张,不要那么用力。”
他的样子确实太紧张,初为人父,挂在眼角眉梢。即使在外交事务上纵横驰骋,现在看来,也只是个手足无措的大男人。
眉皱得好高,像是谈判僵持时审慎的思考,可又比以前生动很多,眼神深邃的写了疑问,都是关于宝宝吧。
在车外接过襁褓时,呼吸都不顺畅,手指相碰,感觉他在发抖。就像自己第一次从护士手里接过宝宝,也是慌乱的掉眼泪,除了远介和和子在身边祝福,就是孤单单一个人,亲吻着宝宝手腕上的配牌,上面除了名字,注明了母亲和父亲。
为那个名字,心心念念的过了二十年。
偷偷孕育的艰辛,没有他的参与。第一次让宝宝躺在怀里,只会把脸埋在香软的小肚皮上,掉着眼泪想他爸爸。
过去的一切,不堪回首,又总难以忘怀。
父子终于见面了。还有好多来不及告诉他,但是并不着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梳理着胎发,凑近就是沁人心脾的香,爱到骨子里。
他一定也是爱极了,越抱越用力。
“太高了,放松点。”
软软的婴儿,托得高了些,几乎端在肩上,都闻到毯子里的奶香。心坚强不起来,眼角有些酸。
太喜欢了,说不出来,听见亦诗在旁边说话没有回答。额角撞到的瘀痕疼,她的手压在上面轻缓的揉了揉。
躬身带孩子上车急了些,砰的一声,接着慌手慌脚的摆位置。不是司机在,她差点笑出声。
谦谦那么小,他的块头又大,强烈的反差。后排空间马上狭小起来。她抱着提包让了让,故意不帮忙,眨着眼睛偷笑。
毕竟头一次,之前除了她,他没接触过什么孩子。现在自己的儿子躺在怀里,看起来实在太脆弱,粉嫩的脸庞还没有他手掌大。身体僵着适应孩子的睡姿,浑身使力歪在座椅上。
她看不过去,一支手臂插过来,细长的小臂滑过手背,心里又受了震撼,抬眼看着她熟练的托起孩子的头部,在他臂弯里摆好位置。
“放松,宝宝会疼的。”调整好襁褓,不忘亲了亲露出毯子的小手。
也想像她那样亲一下,眼睛里写着询问。亦诗来不及回答,宝宝却动了动,打了哈欠,回应了爸爸的问题。
倒抽凉气,左右晃着僵硬的手臂,怕他醒了,又希望他醒醒,睁开眼看看自己,毕竟到现在还不认识。
愚蠢的念头,动作笨拙些,老刘从后视镜里瞄了一眼,都笑了。
宝宝没有回应他的期盼,连眼皮都不眨,又在怀里睡熟了。婴儿都这么能睡吗?不知道,只是小小的一个哈欠,心情起伏,嚼着温暖的复杂情绪。如果父母和让看到了,一定会宠坏他。
以后,要带着他打棒球,滑雪板,上一流的大学,出国深造。回家首先要改造公寓房间,晚上就要着手,什么婴儿用品都没有,要准备的太多了。
心里满满的筹划,没抗拒过诱惑,凑到襁褓的边缘,亲了亲小毯子,沾了些奶味,谦的脸上已经挂着满足。
“刘叔,开快点吧,没关系的。” 手放在他腿上,安抚着,好像自己才是那个年长十四岁的人。
窗外的色彩斑斓起来,最喜欢布鲁塞尔的这个季节。看他脸上随时变化的情绪,感觉分开的一年很值得。其实宝宝就是在这里孕育的,现在只是回家而已。
摩挲着奶瓶,掌心里暖暖的,他腾出手拿走了奶瓶,拉着她的手一起搂住孩子。
亦诗靠到他肩上,两个人十指交缠。
孔宝宝很给面子,做了那么久飞机又换汽车,就乖乖的睡,嘴角冒着口水泡泡。
争取了八年,这一刻就是她要的。现实还是记忆里,只渴望这样和他一起。
很小声,从耳边滑过,虽然不是他习惯的表达,但是听起来还是一样的窝心。
“谢谢,一一!”
一条泪线,消失在他肩上,“谦,不谢……”
……汽车开下了高速路,这本该是最团圆幸福生活的开始,可是,二十年前开始的波折,并没有因为宝宝的到来而结束。
到达布鲁塞尔的第二个星期,亦诗和孔谦失去了这个孩子。
孔谦很难忘记第一次见到亦诗的一幕。
那是个冬天的清晨,山腰上还有积雪。部里的车队从山脚一直排到村边的公路上,一水的A字车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穿着黑西装的工作人员几步一岗,一段路滑的山道上甚至铺了毯子。
墓园就在绕山而过的溪水旁边,据说是上风上水的地方。忍着困倦,看了眼身旁的让,也是一脸的茫然。
从学校被叫来参加丧礼还是第一次,电视里领导都在城里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这次却来了郊外。路上才听说去世的是厅长的妻子,今天只是骨灰安葬。
能有这么多人物出现很难得,那时亦诗的爷爷在任上,来的人都是冲着老领导的面子,所以排场很大。
下了车,孔谦和让走到父母的车边等候。
“一会儿你们去鞠个躬。”孔父严肃的发号施令,母亲给他们整了整领带,拍拍肩上的皱褶示意他们先上去。
“知道了。”
谦和让一前一后走在上山路上,每几步都有几个扎得华丽的花篮,写着敬赠人的名字。菊色并不浓艳,但铺陈开去,又觉得刺眼。
墓园尽头,一块空地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等了好久,仪式才开始。
看着父母随着亲友入场,一位老人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一脸肃穆的中年男人。
仪式是基督教形式,长老会一位牧师主持,很简短,只为故人入土为安。三五个孩子一身黑衣裙,手里拿着白色的玫瑰花,依次上前把花放进墓穴旁。
最后面的小女孩,个子最小,手里拿着一支长颈的白玫瑰。
五六岁的样子,黑色的蓬蓬裙,头发扎成两个小辫子,面容姣好,却挂着超出年龄的情感,好像哭过好多了,眼睛红肿着。
别人献完轮到她,举着花怯怯的上前,停在牧师面前。蹲下身要放,又犹豫了,似乎舍不得,把花抱回怀里,转身求助的找亲友席里的人。
“诗诗!”男人的声音很严厉,吓得她一振,失手掉了玫瑰,愣在原地不敢捡。
墓室的盖子很快合上,小女孩哆哆嗦嗦的站在墓碑前,眼睛里已经蓄满泪,被亲友席后排跑上来的中年女人抱走。
静默的哀悼,牧师念了一段往生的悼词。冬日的风穿透外衣,谦觉得山脚下很冷。
隐隐传来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听着悼词,有点分心。诗句很美,可孩子的哭声揪心。不能回头看,心里猜测着孩子的身份。默哀结束的时候,哭声停了。
来宾献花,排在队伍的后面下意识抬眼寻找,发现那女人抱着她在远处拍哄。
队伍里有人叹气,也有私下交谈。
“怪可惜的,刚刚三十岁,那么年轻。”
“孩子才六岁,不知道以后谁带?”
“哎……”
和父母一起祭拜,走到亲属席的时候,由父亲引荐。
“亦部,翰臣,我儿子孔谦,孔让。”
一板一眼的问好,祭奠鞠躬,献花。回到等候区域,看着父母和家属谈话。
“哥,人死了信仰还有什么意义?是教徒还在意风水!”
“也许家里老人讲这些吧。”
看向不远的地方,搞不清仪式什么时候能结束。
工作人员送了件裘皮大衣披在女人身上,刚刚鲜花的小女孩侧趴在她肩上,一个辫子散了,鞋也掉了一只,女人没注意到。
风很冷,女人披着大衣抱着她,也没给她披件衣服,裙摆被吹得荡来荡去。
隐隐的哭声从远处传来,叫着妈妈,妈妈……过世的是她的妈妈吗?
下山的路上,孔谦和孔让走在前面,超过抱孩子的女人,余光扫了一眼。女人脸上表情平静,只是机械的抱着。孩子的袖子蹭高了,细小的手臂露出大片皮肤,女人还是缓缓地走,完全没在意,身上的裘皮大衣随着步子垂坠,显得格外雍华。
谦在山脚下等待与父母汇合,抱孩子的女人停在路边,也像是等人。
孔父终于来了,依然和老人走在一起。女人抱着孩子上前,已经把大衣脱下来裹在孩子身上,脸上多了些情绪,走到中年男人身后。
“部里难得见,休完又要回去了吧。有机会来家里坐坐,也多帮帮翰臣。”
“不敢当,还要您提携。”边说,孔父边随着老人上了警卫员开来的车,中年男人跟在后面。
宾客相继开车回城赴宴,传统的习惯,即使在这个基督教葬礼之后依然不变。
剩下孔母陪着抱孩子的女人。
“抱了这么半天,不哭了?”
女人费劲的换了词手,孩子差点从衣服里掉出来。
“也怪沉的,让谦替你送到车上吧。”孔母就手扶了一把,把大衣盖回去。
本以为提议只是客气一下,那女人听了也没推辞,真的把孩子交过来,带着大衣往谦臂上一放。
孔谦一愣,开始感觉有些不自在,可又不好推辞。低头看了眼怀里的小女孩,好像睡了,被裘皮大衣包着,挡住了脸。散乱的辫子垂在手臂上,又黑又长。
第一次抱孩子,后面的路走得小心了很多,让在旁边跟着,一脸严肃,像是共同执行一次特殊任务。
亲属的车停在最靠近公路的地方,司机已经开了车门等着。这条路的尽头,就离她的母亲很远了。
臂弯里动了一下,衣领翻开,露出那张献花的小脸。眼皮哭肿了,眯成一条缝。泪水被风吹干,脸颊和鼻尖上都是红红的。微微睁开,自己揉了揉眼睛,黑透的眸子沁在水里,看到生人,难过的把脸藏到另一边。
那么稚气的样子,怕摔到抱得更紧些,让她趴到肩上,裹紧了大衣,手揽在单薄的背上轻轻拍了拍。
第一次离孩子这么近,瘦小身子趴在怀里寻求着温暖。她的发梢碰过脸颊,心里却感觉酸软。
她还那么小,已经失去了亲人。小小的生命,这么脆弱,又没有人好好呵护她。
臂上很轻,托着她放在后座上,没忘记把袖子拉好。袖笼盖到手背,握着那只小手看到上面涂鸦的字迹,歪歪扭扭,勉强认出是“妈妈”两个字。
她躲了一下,在后座上蜷起身子。
谦把大衣盖好,退开想说什么,知道她又在哭,但没时间了,中年女人已经跟上来,在身后抱着手臂催促,敷衍的说了句谢谢。
车门关上了,小小的身子完全被挡住。
一辆接一辆的黑色轿车驶离,山里又恢复了宁静,只留下漫山遍野的菊花。孔谦走到母亲身边,注视着远去的车里女人挺直的背影。
“妈,那女人是谁?”
“她……亦部长的新儿媳。”
让想插话,车来了,母子三人坐了进去,孔母打断了这个话题。
“哥抱的孩子是谁啊?”
“是亦部长的孙女。”
“死的是她亲妈妈吧,抱的是后妈!”
“……行了,让,不许问了,说点别的!”
谦坐在前排听母亲和让说话,还在想刚才的一幕。她并不疼爱那孩子,可身份已经是她的继母了。她会对她好吗?
郊外的景色被甩在车后,孔谦的脸印在车窗上,望着窗外千篇一律的街景,孩子清秀的眉眼在眼前清晰起来,她的眼泪没有干透,窝在他怀里时小手慢慢的收紧。
心里像被什么箍住一样,一时又抛不开。
那双小手上歪歪扭扭的两个字,看了着实让人心疼……每次车子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