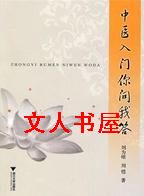我答应离你而去-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半个钟头后我红着脸跑到前厅里接电话,此时电话筒早放回了话机上,张妈垂首站立一旁不语。
“张妈,我母亲有没说是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就是让太太多注意老爷。”
我放下心来,忽然瞧见张妈又在以一种探究的眼神注视我,心里一紧张赶紧回房,不妨身后张妈喊道:“太太,你是不是不舒服,怎么踮着脚走路。”
“这个……”我不好意思说身体是被骆桢弄疼,想了想编个谎瞒了过去。
中午吃过饭后我和骆桢便在卧室里练习舞步,晚上去酒店参加舞会的人都是熟识连兮的朋友和同学,稍有个不慎便会很容易被他们发现问题。当然复杂的我一时半刻也学不会,只练习了简单的快三慢四,骆桢说只要我不接受其他人的邀舞,基本上不会被人发现破绽。
他要求我千万不能离开他的视线,否则无法及时过来替我解围。
夜色在城中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和骆桢到达了夕照路的云天大酒店,骆桢将他和连兮结婚两周年的庆典安排在这里。这座酒店我曾经坐公交车的时候曾仰视过,只知道是个外国人喜欢聚居的场所,而且还听说里面的酒水价不便宜,料想承办一场舞会和宴会需要花费不少钱财吧。
我瞟着身旁的骆桢,他花钱做戏,请人做戏,这最终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我不再问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和他相处的几天提出过不下十回,可没有一次他从正面回答过我。
“在想什么。”他忽然一笑,满眼的柔情蜜意。
我心里只觉一软,暗想到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为了骆桢就算到头来蹲大狱,把牢底坐穿也是值了。
乘电梯到五十楼,这是个旋转式的顶台,面积有数百平方米,可同时容纳近千人。我们到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来个人,看见骆桢忙迎了上去。
“骆先生,舞会的音响灯光已经全部筹备好,另外酒席也已备好,现在只需要等待宾客到来。”
他点着头,偕我去门口迎接宾客,不一会便开始陆续来人。我随着骆桢和他们问好行礼,果然来的许多都是骆桢给我看的相册上的人。
“骆桢。”门口走来一位身着青花瓷式长晚礼服的大|波浪发的年轻女子,她满脸含笑,神采飞扬,我看了一眼只觉眼熟,忽而瞧见跟在她身旁的俊逸男子便想起了她的身份。
上次我随骆桢参加什么酒会时曾见过这名女子,这女子当时和骆桢打得火热,不过我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她,她身旁的男子比她更吸引人,就是当日酒会上的季宁非,骆桢口中所指的吃软饭的小白脸。
当然我并不是对他的相貌感兴趣,他的职业更引人遐思,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为何不去体面地工作,而要陪些富婆出卖自己的身体呢。如果那些富婆像这位女子一样年轻那倒没什么,但要是个七老八十皮肤没弹性满脸老人斑的老太婆,他也能装出很享受吗。
不得说身体里埋的八卦因子又在作祟,我目不转瞟地盯着季宁非搭在那女子腰上的手。
“看什么。”骆桢的声音有些不高兴。
我笑道:“你朋友被人勾跑了,你说他真的是只鸭吗。”
他拉了拉我的衣袖,靠近我低声道:“注意你现在的言行,不要像个小流氓,等回去后你再说。”
我无语,明明真正的大流氓是他骆桢自己,今天早上他还把我给强占了两次。
“连千山来了。”骆桢突然压低了声音。
我往前瞧去,深红色的地毯上踱过来两道人影,是一男一女,男的是连千山无疑,五十来岁的人依然气宇轩昂,眸光四射,端的是有神彩,是个精明的企业家的形象。我又瞧他身旁的女子,那是个极年轻妩媚的女子,她的手腕轻轻搭在连千山的臂膀上,我细瞅了几眼,竟无法把她和相册里的任何一个人对上号。
“爸。”我还来不及问便被骆桢拽了上去,跟着也喊了一声。
连千山看了他一眼,目光便停留在我的面上,我看得胆寒,这老头子的眼神非常锐利,一双眼就好像要看到我心里去,赶紧又叫了他一声。半晌连千山才收回我面上的目光,我忙见机地把骆桢教的套话说了一遍,连千山搂着我的腰轻轻拥抱,我脸孔略微一红正要躲开,忽想起这正是连千山遵从的西方礼仪便也迎上去,想着这连千山好歹也算个老帅哥,被他抱一下也不算吃亏。
接待小姐引领着他和那名女子步入宾客席位,我这才问道:“那女人是谁啊。”
“不知道。”
我又瞅了几眼,那女子的目光一直围绕着连千山,面孔森冷的连千山偶尔会对上她。立刻身体的八卦因子又沸腾起来,我不无肯定地道:“我知道了,是连千山的小蜜,你看你看他们两个的眼神绝对有奸|情。怪不得不要我们去接,原来是想和小蜜在宾馆里鬼混。”
“回去再说。”骆桢满脸尴尬。
我只得打消了继续八卦的兴致,但眼睛仍舍不得离开那两位,虽然连千山的老婆迟秋鹤年已迟暮,但是风韵犹存,这女子只不过年纪轻些,论样貌却不及秋迟鹤一半,咋的这连千山就看中她了,难道是老家伙都有啃嫩草的习惯。
绝对是啃嫩草,我点着头。芳芳上次相亲遇到一个老头,对方居然嫌她年纪过大,说要找个刚20的女子。现在的男人年龄越大,就越喜欢年龄小的女人。
晚上九点庆典正式开始,主持人上台宣读庆典词,由于太长我也没怎么仔细听,众星拱月般的注视早令我疲乏,满脑子都在想自己还没结过婚就先进行了婚礼两周年庆典。骆桢被拉上台去讲话,然后我也被要求说上几句,我按照骆桢准备好的话语背诵完。
整个庆典办得很热闹,在我们分别讲完话后便有明星出来演唱,我一眼认出请来的明星还正是当红的歌星孙某。趁着众人都在听歌的空当,骆桢拉着我来到了一直坐在最后面的连千山面前。
“爸,很感谢你来参加我和骆桢的婚礼庆典。”
连千山面上的微笑很淡,以至于我不能肯定他是否在笑还只是板着一张脸。“爸,这位小姐是……”不管是礼节还是我的八卦天性我都想弄清楚连千山身旁的年轻女子是何许人,秋迟鹤在电话里让我注意连千山,莫不是已经发现了连千山的外遇。
“她是我的秘书江若,这次来B市除了参加你们两个的婚礼周年庆典,另外我还有一个业务需要洽谈,所以就带江若过来了。”
我点点头,内心得意,瞟了骆桢一眼,那意思告诉他,就是小蜜嘛。
骆桢视若无睹,和连千山有一句没一句地寒喧,我便和那叫江若的女孩闲扯话,不过她却对我没什么兴趣,眼睛欢喜地盯着前面舞台上高歌的明星。
一曲舒缓动听的音乐奏起,我和骆桢相拥着进入舞池,周围谈笑的人群自觉地退去,所有的灯光打在了我和骆桢的身上。
“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我常在骆桢的车里听到这首曲子,每次开车的时候他就会不停地放这首曲子。略微伤感带着无奈的调子,依稀可见一个清凉而寂寥的世界,飘浮着一天一地的冷艳空气,可即使这样却仍不免怀着期盼和渴望,仿佛超越了许多的尘土与狂躁,藏在身体里不安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宁静。
“With An Orchid,和兰花在一起。”
和兰花在一起,那果然是一个兰花的世界,满世界都是兰花冷冷的清香。我瞧着骆桢,他的眼眸里全是柔和的灯光,这种眼神不像是在看我,当然也绝不是在看连兮。忽然一道耀眼的强光闪进眼里一阵针刺样的痛,顿时所悟,我现在所站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大舞台,我和骆桢都在卖力地表演,而他对我所做的一切是否也都是戏中所安排的故事呢。
舞会进行得很顺利。中途没出什么差错,我牢记骆桢的吩咐,不答应任何人的邀舞,也绝不离开他半步,或许我有什么话说错,骆桢都能在旁边帮我圆回。
结束后我和骆桢送连千山回下榻的宾馆,但他阻止了我们,车门前他仍是用那似笑非笑的神情对我道:“连兮,你不像以前了。”
蜕变
送走连千山我和骆桢面面相觑,连千山临走前那句话颇有些意味深长的味道,也许他已经认出我不是连兮。这也难怪,做父母的哪会分辨不出自己的孩子呢。
“走吧。”身畔骆桢轻声道。
我答应着,回身相望那幢高耸入云宵的摩天大楼,此时它也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也许我和骆桢之间的表演随着连千山那句看似鉴定的话落下,似乎也该有个结束了。毕竟做演员,我还太青涩。
“不要想了,没事。”他拥住了我,溶溶的夜色里那双眼眸好像湿了一样。
上车,不语。
车里又响起了那首《与兰花在一起》,但此刻听着却是那么地忧伤和无奈,好多难解的心情。我瞧着前面驾驶室聚精会神开车的骆桢,犹豫半天道:“如果连千山发现了怎么办。”
他没有答理,于是我又追问了一次。
“如果他发现你是冒充的。”骆桢将车停到了路边的辅道上,回过头歪着脖子笑道:“那我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我会向连千山说并不知道你是假冒的。”
他明亮的眼眸中的笑意那么温柔和光辉,仿佛这车窗上随意洒落的无边月光避无可避地挤进眼里,我心里倏地便冷下来,面上有冷汗在渗出,连嘴角都僵硬得说不出话。
好冷的月光,我不由瑟缩着双肩打了个寒颤。
今天我们还……
他微微地侧过头,似乎仅用眼角的余光在瞅着我,眼皮向下垂着露出一道深深的褶皱。“有些事只能在真正面对的时候才知道会怎么做,那时的想法和做法才代表真正的内心。”
车里又开始响起《和兰花在一起》的忧伤调子,骆桢回过头去,车开动起来。
心纷乱如麻。
此刻不能再管骆桢会做些什么,而是如果我将要面对他所说的这种情况时,我该怎么做。是将一切和盘托出,还是怎样。或许不管怎么去撇清,火已经上身了。
“到了。”
我抬头往车窗外看,外面是我在五华村的老宅子,骆桢这次是真正地送我回家了。从上车到现在唇角僵得冷冷地,我也没说什么推开车门下车,骆桢没有下车,也没有看我,车向后倒了两米多远便向前方驶了出去。
他身旁的副驾驶位上仍是空空如也,仿佛只有沾染着尘埃的月光当仁不让地坐下了,那个位置,他是留给心底的谁呢。
于是,那台车便在我的眼眸中和心里呼啸而去,和着几千年的尘埃与月光不再来。
我想着,自己对骆桢大概没用了。
夜里翻来转去睡不着,爬起敲开了村里的一户小卖部,她家有公用电话可打。在老板娘愤愤声中我拨下了骆桢家中的电话,这个电话在前厅里面,过会张妈就会接起。不敢直接拨打骆桢的手机,只怕有个三言两语刺得我更加受不了。
电话拨了几次张妈才接起,我也不敢直接说自己就是连兮,怕露底泄密,鬼知道骆桢回去又和张妈撒了什么谎。“你好,请问骆桢在吗?”我捏着鼻子说话。
“先生他不在,今天是他和太太结婚两周年庆典,晚上舞会结束后两个人在酒店订房不回来。请问你是哪位,等先生回来我告诉他。”
我挂断了电话,事情总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骆桢竟然没有回别墅,会不会是因为心情不好路上出了意外。我惊惶失措地拨下了他手机号码,手机那端一直是等待,我更加担心了,不停地拨。
终于耳朵里听到了他的声音,简短的两个字:“是谁。”
喉咙里的那个“我”字正待要吞吐出来,耳朵尽责地却又捕捉到另一丝不属于骆桢的细小的声音,那是个女子的哧笑声,脑中顿时炸开,话筒从手里“碰”的一声砸到了柜台上。
“怎么回事嘛,别把玻璃砸破了。”老板娘打着呵欠更不满了。
我赶紧从衣袋里掏出钱放到柜台上跑了出去,外面月光满眼,身体早已冷住。回家上床,倒头大睡。
清晨,像往常一样早起,我将自己的包中的所有银行卡和存折找了出来,一个个去银行取款,最后都存到一张卡里面,约摸还有个六千多元。想着要给叶袭留一半,我又往另一张卡里存了三千元,这才回家收拾屋子,翻箱倒柜里给叶袭找出几件衣裳装进包中便出了门。
和叶袭总该有个了结。
料着这个时间叶袭应该在学校,我便坐公交车直接去B大,结果却扑了个空,他的同学告诉我这几天他没来学校。我只得去他租房处,寻着记忆中的破败的小路,密集的房屋,我找到了那间平房。
平房顶上的小棚屋还在,但外面系着的麻绳上没有晾晒任何衣物,我从屋后面踏着薄薄的水泥板的楼梯走上去,褐黄色的小门依旧关着,从半开的窗户里我往里面打量,里面仍是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垫着石头的桌子,但床上的被褥和房间里曾挂着的衣服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