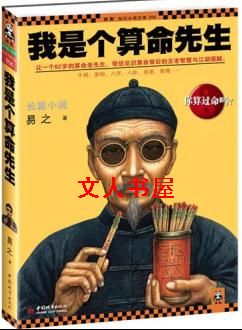我只是个言情文女主-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不知道被他的话还是目光弄得失了神,她暂时不出声了。
他说:“敌人在的地方,你就不去?再教你一笔商场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有压力,不一定进步,但一定能生存。”继续用薄唇追寻她的脸蛋,半天还是挨不上,亲不到人,干脆把她肩一捏,嚯一声又反抱起身。
她的长发甩到他脸上,想细细的小鞭子,打得他刺疼,疼得他又很痛快。
她的脸色突如其来地冰下来,用手继续挡住他:“还有一件事。”
“快说!”他勉强的温和没了,开始愠了。
他的耐心一向充足,除了跟她相处。
丁凝说:“那天匪徒挟持我,威胁你,你最后还是选择开枪,并没受他要挟,是因为你看见了安安在他背后爬起来,准备跟他同归于尽地来救我。”
沉默。
丁凝见他不置可否,“啪”一声,一巴掌摔向他脸孔:“自私,阴险!你明知道他会死!”
越想越钻牛角尖,她把郭劲安受伤的事情统统赖在了他头上,甚至觉得说狩猎区的劫持事件说不定也是他搞的鬼,蛮横不讲理地咆哮起来:“是你对不对!是你害了安安!”
手掌小小的一个,离得也近,并没多大冲击力,并不重,也算不上疼,可是他怒了,捏住她的手腕子:“打我,没问题!但不要为了别的男人。”
前面阿男简直不信这是从邵老二口里说出来的,他宁愿相信明天股市全线崩盘。
那天丁小姐跟小男友迟迟不归,老板撇开他,下坡去找。
作为一个专业水准的合格私人保镖,他怎能放心。
叫吉莲安排厂子里那些老东西后,他沿着开放式狩猎区下了山坡,巡到最后,一记枪声,格外响亮。
狩猎场里的枪声最寻常不过,可阿男天生警醒,闻出些味道,等循声找过去,才看到地上横躺着的两名人,一死,一将死。
老板捂着鲜血汩汩流出的胳臂,用一只手把丁小姐挪到旁边的斜坡靠着,见到自己来了,只抬起疲倦的脸,就像是刚刚不过扭断了一只山鸡的脖子:“报警,跑了一个。”
车里气氛很憋屈。
阿男忍耐不住了,第一次在车里开声打破僵局,有些话,明明当事人就能解释,无奈这当事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丁小姐,郭先生救你是他的决定,当时那个情况,难道老板还能阻止他做那种危险动作吗?”
这一刻,邵泽徽决定给他即刻加薪。
好像是这样的!但是丁凝就是想打他,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痛恨他一个人独揽了功劳,怜惜幕后功臣郭劲安一个人躺在医院。
可她还是举起手,皱着眉,摸了摸他的脸:“疼?总不能比挨一枪还疼吧!”
她对自己从来没这么温柔地主动关心过,邵泽徽觉得这一巴掌挨得值,嘴皮一抽,扬得高挺。
【文】他觉得自己都快分裂了。
【人】丁凝从来没见过他笑的尺度这么宽,揉揉眼,还以为出现幻觉。
【书】他的笑容却骤然一止,收得迅猛,又恢复了面无表情。
【屋】转瞬即逝的笑,太难得。
笑得眼睛弯起来,还挺好看。
丁凝莫名其妙想再看一次,想得几乎忘记了继妹要残害自己,忘记了郭劲安还躺在楼上,忘记刚还跟他怄气,蹭他脖子窝,指头一勾,鬼使神差去挠正常人的痒处。
冷血动物果然都是不怕痒的。
非但没笑没躲,他还有些烦躁,把她的手揪下来,眉一立:“干什么?”
丁凝吐舌头,决定看在一耳光的份上,还点甜头:“你笑起来还行,也没那么老,以后多笑点……对着我。”
拧成一团的眉毛顺了毛。他的心情好到爆,淡然应声:“看情况。”
**
送丁凝回了学校,邵泽徽叫阿男径直开回度假村,路上开口:“叫吉莲帮她准备一下去H城的手续,再通知一下那边部门的人。”
阿男嗯了一声,试探:“叫丁小姐同去H市,除了工作缘故,是因为怕再有什么闪失?”
一次没成功,不代表放弃猎杀。
她那个继妹,不可同日而语,他的甜心蛋糕,决不能这么大喇喇地曝露在吞噬者的垂涎目光下。
带在身边,总放心得多。邵泽徽没有回话,下巴略略扬起来,望向窗外。
阿男见他脸上带着一抹犬科动物护着盘里粮食一样的骄傲神色,继续:“要我同去吗?我跟丁小姐也算熟。”按着合同,他只负责邵泽徽P城行程安全,并不会跟去H城。
邵泽徽眼皮一抬,望向前面这名保镖,眼睫半阖,猜到了他去H城的真实目的,谑道:“你没开玩笑吧,男哥。”
阿男脸色霎时涨得通红,却再没说什么了。
手机响了,邵泽徽看了看屏幕上的来电者的名字,放松的脸色凝注起来,肌肉一动,却依旧没有太大波澜,接通放在耳边,吊着绷带,带着节制的笑意,声音浑厚而明亮:
“你好,DANG。”
作者有话要说:谢谢肉鬆的手榴弹 …3…
专栏求收藏~(≧▽≦)/~啦啦啦
☆、58
半月熬过,这天早晨刚起来;丁凝接到郭教授从医院来的电话。
郭教授从来没有通知过自己郭劲安的病况;拿着电话的一瞬,丁凝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不会是郭劲安出了什么问题吧……
那边的声音却很冷静沉着;病人清醒了。
假都没请;跟齐艾打了个招呼;丁凝兴奋地跑去了医院。
住院部的走廊上;郭教授似乎早就在等。丁凝觉得自己有有点孬,到现在还是不好意思跟这老人碰面;可郭教授的态度却显然和蔼了很多,应该是儿子病情好转的愉悦;甚至还亲自开了病房门;带上门一刹,面上的笑意却凝住,有些复杂。
秋日阳光暖得迷人,照得医院楼下的草坪一片金黄灿烂,洒进玻璃窗里,英挺青年坐在病床上,盯着窗外的风景,后脑勺朝着门。
丁凝踮脚过去,双臂一开,轻轻捂住他的眼。
她感到他温暖紧致的面部皮肤微微一动,缓缓回头。
拆了绷带,戴着医用防护帽,他的脸清瘦了不少,皮肤苍白得透明,下巴尖出个叫人心疼的形状,五官更加出挑。
他慌里慌张摸到床头柜上的眼镜,戴上,看清面前人,吸了口冷气,嘴唇一扬,贯起个漂亮的弧度,脑神经受损,就算未来复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眼下口齿还不伶俐:
“你……素?”
语气难为情,是那种明知是熟人,但就是想不起来的错愕和尴尬。
起初,丁凝以为他在捉弄自己,突然醒过来,眼前这个,是绝对不会欺骗自己的人,心里凉了大片,一把抱住他。
病人受了惊,可还在自责地念叨:“肚不耻……”
子弹取出来了,可淤血沉积,压迫神经,高级植物神经受损,导致解离性失忆,可能短暂,可能终生。
忘记的诸多人事中,丁凝算一个。
四面白墙的病房突然冷气十足,郭教授把丁凝叫到门口,简单说完,再无别话,用眼光提前目送她的离开。
丁凝心里发寒,转身回去,坐下来,继续抱住郭劲安:“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郭劲安的脸上的是抱歉和愧疚。
他只是不记得一些人事,并不是成了白痴,面前女孩跟自己关系匪浅,不用旁人交代,他也看得出来。
甚至,她身上的味道也很熟悉,可是偏偏叫不出她的名字。
失去了大脑区域某段时间的记忆,不多不少,刚好是她出现在自己生活的那么一段,真可惜。
他好像十分的揪心,就像鬼压床似的陷在噩梦里,怎样也睁不开眼睛,只能看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抱住自己。
***
下楼时,邵泽徽依旧在车子里等。
想必郭劲安的情况,他知道的比自己还早,她混混沌沌地望着他。
省了面纸,他把她连绵不绝的眼泪珠子全部舔干,把她打横抱到腿上,挺身相拥,用肉体的贴近去安慰她,硬生生蹭得她生出了安全感,一点点填平眼下的苦楚。
那男人不记得了她了,她在痛不欲生……
他的心头宝眼睛珠,在为了别的男人伤感,自己甚至不能说什么。
安慰?不好意思,自己没那么大度,发自肺腑的畅快更多。
那个年轻的男孩,干净剔透,温润谦和,有一副讨不同年龄层异性欢心的好相貌,眼睛里含着天生的笑意,嘴角又透露着坚定和独立,这种相悖在这年轻人身上有种并不矛盾的调和,站在那儿,好像天生有阳光做背景,随意一笑,伸出长臂,就能叫不同年龄的女人心折。
这样的气质,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沉越厚。现在那男孩已经像一颗珠子,灼灼发亮,再过几年,有了属于一个男人的事业作盔甲,他的光辉在女人眼里,只会更闪耀。
到时,她也许更加离不开他。
邵泽徽认可郭劲安的优势,才会紧张。
不是每个男人都有资格和条件当情敌。
现在,这颗明珠陨落了,或者说,跟她的关系,暂时中止了。
邵泽徽打心眼庆幸。他摸了摸包裹在衬衫内刚能沾水的手臂,咧了咧嘴,多么也想示个弱。
懂得示弱的人太吃香,世人都不喜脸冷嘴硬,都爱看好脸孔,听温和话。
只可惜不用照镜子,他也知道露出的表情很诡异,就不是这个路线。他嘴一勾,有些自嘲,何必拿自己之短,搏对方之长?天生若是狼虎,怎么扮羊也难。
他收回那可笑的神色,表情又变得骏毅如钢塑。
这才是自己,总有一天,他想叫她为了真实的自己,真心地掏心掏肺,死去活来。
哭就算了,不舍得。
怀里的女孩还在哭,到了最后,泣不成声了。
汗水贴在颊上,湿淋淋的,他帮她拨开。
她决定什么都不想地沉沦,快要昏迷的一刻,抱住他的颈子,朦胧着水眸:“二叔……怎样才能不难受。”
他的宝贝在受苦。他挥手,叫阿男开车,奔赴目的地。
进了华府豪廷的枣红公寓,上电梯,关门,他把她竖挺抱起来,勇猛地像只花斑豹,来不及上楼,丢她到长餐桌上。
桌子上的水果盘和茶具禁不起震荡,随着餐布的歪斜,啪啦滚下去。
她往后撑起身体,跟他隔开半米远,抬起腿,伸到他小腹下方,盯他:“二叔,救我!”
邵泽徽发现了,她不像以前那样是浑浑噩噩的软绵。
以前缠着自己时,虽然也主动,可是总感觉是迫不得已。她这次的姿态,分明持着一种进攻状态,比以前热情!
她像个娇憨的女王,主导他的感觉,可又有种被害者的可怜楚楚,在餐桌上半裸着身体,扭得腰快要折断,眨着睫。
她好久都没戴镜框,习惯了隐形,他倒是有点怀念了。
她放空地望他,眸子里是动人的秋波,勾引得他死死。
邵泽徽松了领结,匍匐上去,不客气地来拯救她:“宝贝——”
她用手圈住它,不让进,一分钟变导师:“要、要带套!”
他一滞,裸着精赤身体,半垮着西裤,噔噔噔地快要踏穿楼梯,抱住她上楼。
走到一半,她中途变了卦:“流了一身汗,黏黏答答……”
……
于是,在这宝贝女王的指挥下,他只得先忍着痛,把她先抱到了浴室。
他在外面听着淋浴的水声等着,拨开门缝,看着哑光玻璃浴室内的身影,甚至异想天开里面没了毛巾或者沐浴露,就能自告奋勇地帮她递进去……
这种小男孩的心思越来越多了,真是越活越转去,他又自嘲一次。
他竖着耳朵,悄然整装,以待动静。
梦寐以求的“哎”一声响起,虽然轻微得几乎能略过,邵泽徽眼睛一亮,还是找到了借口,像一头矫健长豹,跃起长躯进去,手一拉,拉开玻璃门。
浴室里的女孩站在莲蓬头底下,水还在哗啦啦地打,波光胜雪的身体滚满晶莹水珠,沿着缝隙往下滴。
她被突如其来的闯入弄得呆住,身体一偏,还是免不了被他捕捉到关键处。
门口的男人倚着玻璃门:“怎么了?”
丁凝想了半天,才意识到可能自己刚叫了一声……不过脚打了个滑而已。
水声噼啪地打在瓷砖地面,她伸出手臂把他推出去:”没事!”
手一抬起来,两颗饱…满在胸脯前晃来晃去,像个勾引人着去捏爆的气球!
他的强迫症适时地发作。
进来了,就别想那么容易出去!
他把她送过来的手一拽,反手关紧了门,穿着衣服站到花洒下,大力把她架起来,抵到墙上。
水刷刷的打得睁不开眼,她视野一片雾蒙,缠在他精瘦腰后,光溜溜的脊背顶在硬冷墙壁上,擂得很疼箍他脖颈,倾前往他怀里凑,避开水的撞击:“——等一下——等一下——”
她湿发结成一缕缕,洗发露和沐浴乳以及她身上本来的香味,杂在一起,弄得他等不了,奋力耸…腰,去摆脱碍事的裤子,附耳过去沉沉:“洗干净了,可以了。”
猛烈的水柱把他的西裤已经淋得服帖透湿,正好通行。
丁凝吞了一口,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