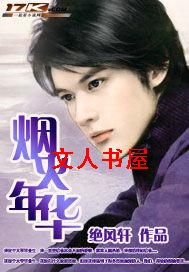流光十五年-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梁肃深吸一口气:“我……”
柳蓉忽然一抬手,把床头柜上罗放得高高的一栏水果整个打翻下来,声音近乎尖利地说:“你听不明白么?看见你我就觉得碍眼,走开!别在我眼前晃!医生护士呢?你们医院里不相干的人是可以随便打扰病人休息的么?”
梁肃站起来,退后半步:“你听我说,别生气……”
柳蓉费力地把自己半撑起来,一把抓起床头柜上的一个水杯,劈头盖脸地冲着他砸过去,尖尖的下颌绷得紧紧的,微微地扬着,充满敌意,傲慢防备,看着不锈钢的杯子毫不留情地砸在梁肃的肩膀上,水洒了他一身。
梁肃站在那里,头发脸上都湿了,心里难过极了。
柳蓉爸妈听见声音,赶紧进来,柳蓉爸爸轻轻拍拍梁肃的肩膀,低声说了句什么,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出去了,柳蓉妈妈近乎低声下气地说:“蓉蓉,妈妈知道你……”
柳蓉像看陌生人那样看了她一眼,重新躺下来,把被子拉到脖子上,抗拒地扭过头去,生硬地说:“我困了,别吵我。”
不知过了多久,柳蓉听见悉悉索索的声音,知道她妈妈又出去了,她这才睁开眼睛,手指紧紧地抓住被子边,无声地流起眼泪来。
她想这原来不是做梦,自己再也不能去北非了。
第五十三章 各奔东西
柳蓉开始变得不爱和人说话,她不再发火,不再哭闹,每天默默地配合治疗,该吃药吃药,该检查检查,不说多余的话,和任何人的交流都变得很简单。有人来看她,她就装作很困的样子,翻过身去睡觉。
在她二十年的全部生命里,她一直都处在一个让人羡慕位置,同龄人羡慕,同龄人的家长也羡慕,她习惯了这样一个位置——高高在上,漠不关心。而今,她游刃有余的生活忽然戛然而止,每一个来看她的人都眼含泪光,带着一副不知该说什么好的模样。
柳蓉忍不住想别过头去,她冷漠地想,这和你们不相干。
她开始痛恨起别人的关心来,甚至包括父母的关心,柳蓉妈妈想抱她一下,也被她因为不方便拒绝掉了。那些关心就像是某种不祥的空气,呼吸得多了会让她暴躁,柳蓉有时候默默地盯着身上盖的被子,心里想,现在已经很难看了,再暴躁就更难看了。
当她成功的时候,她也不反对别人亲近,从她这里蹭走一点喜悦走,如果别人来求助她,她甚至会热心帮忙。而当她的人生走到低谷的时候,她却不希望有人看见她现在的模样。梁雪,常露韵,胡蝶,梁肃……他们都是别人。
别人没办法理解她的疼,她的痛苦,别人的目光对柳蓉来说,是一场新的酷刑。她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了,一个同情的目光,就足以让她身陷地狱。
这一年,对所有人来说,都特别漫长。常露韵远走西北,走进她的大学年代,她没有去看柳蓉,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常露韵的她爸还说要给她拿点钱,叫她带点礼物去看同学,毕竟是高中同桌三年的好朋友。
不过常露韵想了想,还是拒绝了,她爸妈都觉着她有点不会做人,好朋友之间,别人发生这种事,怎么能不关心呢?
可是关心不能顶饭吃。
她想柳蓉现在,就像是当年她自己偷偷躲在厕所里,用食指抠嗓子往外吐东西的时候一样,是不希望别人看见的。她们天生不是柔柔弱弱楚楚可怜的类型,尤其柳蓉那个性情,又是和谁都不说心里话的,那样骄傲的一个孩子,要是别人在这时候贸然过去,看着她掉两颗眼泪,或者柳蓉嘴上不说什么,往后心里也就划清界限了吧?
像柳蓉这样的人,只有在拿对方当朋友、当重要的、打算一直有来往的人的时候,才会在这个时候躲着不见。
否则不相关的人怎么看,又和她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临走的时候,常露韵却忽然很想再见秀秀一面。她拨通了秀秀留给她的电话号码,接通以后,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很不耐烦,她一个“喂”字没说完,对方就匆匆忙忙地打断她,很没礼貌地问:“你谁啊?找谁?”
常露韵愣了一下,客客气气地说:“你好,我找于秀秀,我是她……”
对方冷冷地说:“不在。”就挂机了,常露韵拿着话筒怔了很久,心里有些惴惴,觉得男人的口气很差,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给秀秀惹了什么麻烦。
她无从揣测对方的生活,尽管她们同在一片蓝天下。
这一年,胡蝶鼓足了勇气,用她最漂亮的模样报考了电影学院。可她不够漂亮,她在普通人里算好看的,很多男孩子喜欢跟着她跑,很多同龄人会嫉妒她的美,她是当年五中的校花,可是全中国的“五中”有那么多,漂亮女孩子浩如烟海,胡蝶遭遇了她的另一个滑铁卢。
她回来去医院看过柳蓉一次,被她那一夜之间变得不通人情的朋友拒之门外。胡蝶就默默地把花放在病房门口,当天,她带着一个小小的行囊,再次登上北上的火车。
人这一辈子,怎么也要有点什么追求,胡蝶想。
她走的时候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她那整天忙于生意,每次匆匆见她一面都只是甩下几张人民币又匆匆离开的妈,包括她那每个月往银行卡上给她打固定金额的爸。胡蝶其实一直有一句话想表达,但是没有机会说出口——她想跟她的父母说,养孩子不是养花,只要浇水晒太阳就行,一个孩子只浇人民币,是不行的。
可是说了能怎么样呢?
胡蝶这么想的时候,就会冒出一点假沧桑的难过来,她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年纪了,晚了。
传说养女孩和养男孩不一样,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
这样环境里出来的女孩会大气,会对很多东西宠辱不惊,会慎重地考虑自己的未来应该怎样,而不会因为一点诱惑就跟着别人跑,她不会自卑,不会像孔雀一样炫耀,也不会像巫婆一样嫉妒,当她长大以后,就会有一个相对同龄人宽广的心胸。
而心胸,决定了她这一辈子将会走到什么地方,站在什么样的高度。
可是对男孩子的“穷养”不代表可以不闻不问,对女孩子的“富养”也不代表每天只喂她吃人民币……当然美金更不行——她不是ATM机,喂多少将来能吐多少。
“穷”是让他知道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所有扶着他的手都会老去消失,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需要背负很多东西,跌跌撞撞地直起腰杆来。“富”是要给她很多很多的爱,充足到能让她明白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爱,能在光怪陆离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清醒地来往。
火车在铁轨上奔腾而过,田野房舍都纷纷远去,胡蝶忽略了坐在她对面,一直企图和她搭讪的大叔,侧着头看着窗外,心里委屈起来。
曾经有一个朋友跟胡蝶抱怨过自己没人疼没人喜欢,末了唉声叹气颇带酸味地看着她说了一句:“你就好啦,这么漂亮,天生有资本。小学老师说人心灵美才是真美,长得好不算好,要有内涵才是真的,全他妈狗屁。大家都那么忙,能看清楚个皮就不错了,谁有工夫扒开你的皮看你的瓤长什么样?我呀,要是有你那张脸,那真是什么都不用愁了。”
胡蝶想她说得其实才都是狗屁,因为此时此刻,她照样举目无亲,无可托付。
她原本可以去向柳蓉倒一倒苦水,说我命有多不好,说我其实每天每天都有那么多不高兴的事,人活着,如果都是不高兴的事,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可是现在也不能了。
梁雪去医院的时候没有惊动别人,只是自己和打工地方的老板请了个假,一个人去了。她在楼道里徘徊了很久,跟在风雨无阻地来医院报道、又一次一次地被拒之门外的梁肃身后,没有打招呼,只是看见他进到病房区以后很快又出来,绕了个弯从医院大楼里出来,蹲在侧门门口,烦躁地一根一根地抽着烟。
家庭、贫穷、事业失败,这些都没有打倒他,但是命运这种抽象的玩意总会搞出更离谱的事情来玩人。梁雪压低了鸭舌帽,不想被人看见,她远远地往病房那边看了一眼,突然也不想去看柳蓉,她觉得很累。
梁雪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她有柳蓉那样的家庭环境——不用大富大贵,只是普通的三口之家,开心快乐、衣食无忧就可以,有通情达理的父母……哪怕他们不通情达理,但只要他们是健全的,哪怕他们天天在她身后追着唠叨抱怨,那也是好的。
或者如果她有柳蓉的先天条件,她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呢?
每个人都觉得如果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自己会比别人优秀。
即使梁雪多年来,在外人的眼里看起来那么坚定、那么优秀,好像一个总也打不倒的超人一样,她也不是没有彷徨过。在她眼里,有一类人,他们天生优渥,可以快快乐乐毫无后顾之忧地实现自己的梦想,比如柳蓉,甚至是常露韵。
第二类人,是那种出身不幸,像她一样,却有更快捷的“发家致富”之路的人。比如……她的一些同学。她们做一些见不得光的服务,甚至会去拍一些不雅的照片,在这个人们为患的社会里,屈服于自己的弱势。
第三类,就是比如梁雪。
她除了上课以外,做三份家教,晚饭时间去餐厅打工,从打工的地方回去以后,还要做接的翻译活——笔译这种东西,没做过的人不知道,其实是非常费神的,千字三十到八十块钱,她每天晚上弄到很晚,眼睛都花了,不过千十来字——何况她一个礼拜只有几千字的资料可以做,这年头会几门外语的人实在很多。
她在最美好的年龄里,穿最朴素的衣服。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样美的,但它们并不一样美好。
为了她这份坚持,梁雪不知多少次在半夜里哭醒,这些话她从来没对别人说过,如今看来……也没必要说了。
梁雪把果篮放在护士那里,托她转交,自己转身走了。她现在明白了,人这一辈子,怎么顺,也总会遇到三长两短的劫难,才能过得去,老天对她算是慈悲了,尽管贫穷的后遗症在二十年的岁月里已经在她的骨子里扎了根,根深蒂固成她灵魂的一部分,可那也毕竟是隐形的。
她还有梦想和未来。
两个月以后,柳蓉配了一对假肢,开始重新学习走路。
第五十四章 冬天
走路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因为很疼,就像是在刀刃上跳舞一样,还因为她每走一步,都会重温一遍,自己的身体已经不是完整的这个事实。
“刀山火海”这个词说出来的时候可能轻轻松松,喝多了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过,“谁谁谁我能为你上刀山下火海”,柳蓉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哭笑不得,因为谁也不会真的去上刀山,可她不行,她现在必须要上。
高中那会,有一个校友到学校做过一个报告,讲的是自己的真实经历。大学长已经毕业十二年了,高中没能读完,得了淋巴瘤,一度无法吞咽东西,连唾液都要吸出来。
他说:“吞咽唾液这个动作,很多人很多时候恐怕做出来的都是无意识的,只有我那时候明白,能做这个简单得大家都注意不到的动作是多幸福。”
只有柳蓉明白,能做走路这个简单得很多人都注意不到的动作,是多幸福。
她甚至想,如果不能活得像个人一样,那不如立刻去死。可她不能死,她觉着不甘心,她恨这个世界,还没有好好报复过它给予她的全部不公平。
人在最最难过的时候,总是想要找一个具体的什么东西去恨的,愤怒能迅速地提升一个人的潜力,是一根最坚挺的支柱。柳蓉本能地想恨点什么,可是周围没什么好给她恨的,每次看见她爸妈强颜欢笑的表情,她都只会想哭,于是她只能反社会了。
她每天在医院里低着头,一步一挪,低着头,不声不响,牙关咬得紧紧的。她现在明白为什么电视上或者杂志上拍出来那些很痛苦的人都低着头了,因为人紧紧地盯着地面上的某一点的时候,心里会产生某种麻木的感觉,好像一时的苦是苦,一辈子的苦就不是苦了。
人要是抱着“熬一阵吧,熬过了就……”的想法,就会觉得这一步一步特别难捱,可是当他觉着这样的日子将会绵亘到他活着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反而就淡定了。
都这样了,还能怎么样呢?
有人说精神上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肉体上的痛苦,譬如失恋,譬如人生低谷,都能让人生不如死,其实这种说法大多数是不客观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失恋失业、被什么人伤害过心灵的人,都没有断过腿,所以得不出一个更加客观公正的结论。
其实身体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脑里就一片空白了,也就无所谓精神上痛苦不痛苦了。
柳蓉撕掉了她的假面具,上了C大以后,有时候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乐观开朗且善于交际的人了,而今,她又重新变成了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