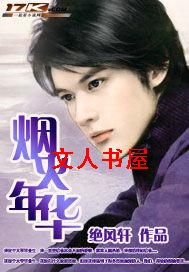流光十五年-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柳蓉想了半天,才犹犹豫豫地说:“我听说文科班最高分有……六百三十几?”
看见梁雪的表情一下子暗淡下去,她赶紧改口:“没有吧,也可能是我听错了,好像是六百二十几?要么是六百一……嗯,六百一差不多。咳,现在也不大关心这个,要么回去我再好好给你打听打听。”
梁雪听得出她话里德安慰,勉强笑了笑,常露韵赶紧在旁边试图转移话题:“哎,柳蓉,我听见内线消息,说这回F大咱们班保送名额是你让给顾清阳的。”
这回连梁老板都凑过来了,端了一个放满了小点心的大托盘过来,给考生们加餐,柳蓉和梁雪立刻扑上去了,还惦记着体重问题的常露韵矜持了一下,也妥协了。
梁老板把围裙和手套脱下来——他现在在店里增加了面包业务,雇了一个点心师傅,越做越正规专业了,把她们三个的奶茶杯子收拾下去,还顺手拍拍柳蓉的头:“保送都不去,那么牛?”
柳蓉嘴里塞得满满的,咕嘟了一句:“看不上。”
常露韵就顺口调侃:“咦?我怎么听说是顾大班长用的美男计?”
“砰”一声,梁老板被手里的大托盘遮住视线,走路撞到了柜台上。
第三十六章 少年JUMP!
一声巨响,打断了姑娘们热火朝天的八卦精神,梁雪看了看她哥,不厚道地说:“哎哟,真疼!”
梁肃揉着被撞疼了的地方,强颜欢笑:“没事没事。”
就见梁雪一脸心疼地摸摸柜台,然后目光犀利地翻了她哥一眼:“谁说你呢。”
梁肃郁卒,有心抬手照着他这败家妹妹后脑勺上来一巴掌,又不舍得,生怕手劲大了,把这全身上下无处不金贵的高考生给打傻了。
他一偏头,看见柳蓉咬着吸管,没心没肺地跟着拾乐,到嘴边想说的话,就忽然说不出来了,化成那么一团,卡在胸口里,又闷又胀,脑子里却好像被冷水搅过一番,出奇地凉了下来。
他的目光好像有自主意识似的,装作自然而然地从柳蓉身上溜过一圈,又划过整个被傍晚下沉的阳光充斥的小店,若无其事地落到柜台上,随手翻动着账本,嘴里满不在乎地说着:“行,小丫头够牛掰,什么都不当回事。”
这句话就像是一把小刀子,切断了他的视觉神经,要不然怎么账本上射到眼睛里数字和文字都进不了脑子呢?
唉,春风无计悔多情,少年心事几人知。
他沉默下来,几个姑娘却无所察觉,仍然围坐在角落的小桌上,叽叽喳喳地说着话,话题以“高考完了以后我要去干什么”展开,像是这群小小的、坚强的行人,正在用言语支撑起了一个尺寸大的空间,在行路的间隙里,三言两语,便搭建起一个别人插不进去的、梦想的舞台。
常露韵说:“我要先睡个昏天暗地,对了,暑假还得减肥。然后要去学东西,现在特后悔小时候没多学点艺术,大了想学了就没时间了,还没决定好是学钢琴还是学古琴,我还想学一门语言,大学一定要考到远一点的地方,以前一直没时间旅游,但是很羡慕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想看看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就去……江南或者西安,学社科类的专业,然后闲下来就可以看见长安古道或者小桥流水,哎呀,让我跳过高考直接穿越到那时候吧。”
柳蓉含糊地说:“我不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就咱们这块地方混个大学就成,不然每年春运火车票机票就够让人掉头发的,看电视里那么多的学生,背井离乡的就为念个破书,每年过节的时候买不上票回不了家,一脸忧愁地看北风吹雪花飘,多凄凉啊。”
常露韵鄙夷地看着她:“你太没追求了。”
柳蓉半死不活地用吸管戳着没化开的冰块,沧桑地说:“常露韵同学啊,你可千万别被古诗词给骗了,据我的经验,全国各地哪都一样,那年跟我妈去上海,从火车站一出来,好,我还以为火车打了个来回又把我给拉回咱们这了呢。除了楼就是车,除了车就是人,没什么新鲜的。”
常露韵说:“瞎说,十里洋场和北国冰雪必然不一样的。”
柳蓉眨巴眨巴眼,诚恳地表示:“嗯,大概我看不出来。”
常露韵揪着她的两条麻花辫玩,判断说:“柳蓉同学啊,等你能看得出来的时候,语文就不会不及格了。”
这句话踩中了柳蓉的死穴,她“嗷”一声惨叫趴在了桌子上,猫似的抓挠着桌面:“这轱辘得掐了别播,咱换下一个话题!”
梁雪忽然说:“我也喜欢江南,上回我一个同学旅游回来,拍了好多那边的几个名校的照片当励志,有好多二三十年代的小洋房,墙壁上都有青苔斑驳的痕迹,特别沧桑,还特别有感觉。”
她垂下眼睛笑了笑,故作轻松地说:“可惜考不上啊,再说我也不能去那么远的地方,我爸谁管啊。”
梁肃这会终于回过神来,插话说:“你考哪算哪,放心,你爸我管。”
梁雪目光复杂地看了他一眼,开玩笑说:“你得管你自己,还得管你爸妈,隔三差五地还要管你那些小兄弟家,再加上一个我爸,要把你累死啊?”
梁肃混不吝地说:“我能者多劳呗。”
梁雪抿抿嘴,没说什么。
这世上的大多数人能顾得好自己就不错了,他却轻描淡写地就担负起那么多人,三年前少年在路边大言不惭地说“我供你”,三年后在这里,他又用同样的语气说出那句“你爸我管”。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天生就这么大,还是因为别人都不能像他一样,狠下心来逼自己?
她想着,梁肃只比她大两岁,他当年能做到的事,自己也可以做到。
六月,高考倒计时牌子被拆下来了,它的没了意义,凡是长了十根手指头的人都能数清还有几天高考。
然后是考前动员、放假、休整。
考前动员大会拉出的横幅叫做“成人仪式”,煽情的年级主任励志讲话完毕,又开始大展歌喉,唱完了《那些花儿》又唱《栀子花开》,常露韵的目光终于从手中的英文单词书上抬起来,愤懑地对一边的柳蓉说:“他是花痴么?”
柳蓉和一边的几个姑娘于是笑得“像花儿一样”。
前排的黄磊回过头来,看了看小声开小会有说有笑的几个姑娘一眼,然后好像想说什么似的,给自己做了半天心理建设,大概是他回头的时间太长,被姑娘们察觉到了,柳蓉于是不怀好意地伸脚隔着椅子踢了他一下:“看什么看,女人说话,男人少多事。”
黄磊慌张地张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另一个女孩就跟着起哄起来:“干什么,你还要插话啊?女人说话,男人少插嘴,那么不懂事啊你,还不回家做饭哄孩子去。”
女孩们被带动着起哄起来,仗着势众欺负人。
黄磊的脸“腾”一下红了,最后柳蓉终于良心发现,问:“有话说话,你什么事?”
被姑娘们群起而调戏之的黄磊同学目光慢慢地移动到了常露韵身上,可是看了她一眼,又不知该说什么好,柳蓉说:“咦?黄磊,你看谁呢,脸怎么红了,让人给煮啦?”
“哦——”
台上的《栀子花开》的演唱已经进入了高潮,台下有跟着唱的,有觉着离别在即触景伤情的,也有完全不买账、各自为政脱离群众开小会的,乱哄哄的活像个集贸市场,于是她们得以肆无忌惮地调戏黄磊。
黄磊那张脸红得都紫了,憋了半天,吸气,呼气,连柳蓉都跟着他紧张起来,最后,他眼巴巴地看着常露韵说:“那个……你理综复习总结的那个本,能借我复印一下么?”
“噗——”
这是全体围观群众一起漏气的声音。
柳蓉看着常露韵一脸也不知是真淡定还是假淡定的表情,从包里把复习本递过去,一脸呆滞地说:“我感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被森森地浪费了。”
常露韵的手悄悄地从底下伸出来,掐住她的腰,拧。
然后……没有然后了,高考时间到了。
白玉列出了整整一页“高考注意事项”,从集合时间到答卷顺序到注意饮食,事无巨细地全部写了出来,叫顾清阳打印了几十份给全班同学发下来,柳蓉目光诡异地看着那张纸条,觉得这位不苟言笑的班主任好像忽然化身成了喋喋不休的老母鸡。
七班墙上贴的锦旗奖状以及励志条幅再次被摘了下去,教室的墙壁被清空,临走的时候,柳蓉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教室,忽然有种人去楼空的萧条感。
高中的最后一天了,就要离开这里了——她默默地想着。一边是释然,一边又不知为什么,有些隐约的伤感,好像无论是什么事,无论自己以前是多么不情愿,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总会让人有些怅然。
顾清阳在和白玉说话,看见她走过去的时候,顾清阳特意停下来,和她打了个招呼,他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却也只是眯起那双很像狐狸的眼睛笑了笑,说了一句:“好好考。”
算是和解。
好好考——我们虽然不是一路人,可我想要看看,你究竟能走到多远。
高考第一天,送考的家长和送别的学校来一中考场的学生的校车排出了十里长街,天气还算好,门口很多家长,一中本土人士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学校找班主任集合,放眼望去,整个操场都是不同班级各自的小圈子,各种“必胜”的口号此起彼伏,活像给出门右拐三百米处的“必胜客”做广告的。
刚上高中那会,柳蓉那极其跳跃的大脑里有时候也会没边地畅想一些事,比如一生一次的高考会不会很紧张啊,会不会像别人说的那样,紧张到极致,一屁股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啊。
事实证明,她其实是多虑了。
经过了无数次模拟考试,好像两个小时做一张数学考卷,两个半小时做一张理综考卷,都已经变成了一种吃饭喝水一样理所当然的本能一样,如果有一天真的出现一张一个半小时的数学试卷,估计她还会很不屑地想,这也是考试么?
总之,就是她坐在高考考场里,听见监考老师开始宣读考场纪律的时候,居然有些诧异,想着……这就是高考了么?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啊。
做几张卷子而已,可老师家长们如临大敌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十二年战斗的决战,于是就特别了……
命运,其实命运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随波逐流得很,也顽固得很,什么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东西呢?有人说是性格,有人说是有没有一颗强大的心,有人说是机缘巧合、三生注定。
反正……不应该是青春期时候进行的一场基础文化课考试,否则就太儿戏了,也太可笑了。
高考真的是一件没什么特别的事。
第三卷 我的大学
第三十七章 那年盛夏
最后一门英语考试终于结束,柳蓉觉得好像自己整个人都懒了下来,身上有什么东西忽然没了,整个人都是轻的,轻得她有些迷茫,背着包迷迷糊糊地在车站等车,第一班来了,由于她神游得太远,等车开走了,那已经脱离地球绕太阳系飞行一周的思维才反应过来,自己应该上去的。
只能等第二班。
经过了高考,她的身份就变了,不再是被家长老师们监督的小孩子了,没有人会再规定不可以烫头发、不可以谈恋爱、不可以进网吧,他们开始共同拥有了一个美好又沉重的名字——成年人。
公交车依然人满为患,柳蓉斜跨着书包,双手吊在拉环上,耳朵里塞着耳机,放着很吵闹的音乐,试图把公共汽车上“咣当咣当”的声音盖过去,身体随着颠簸晃来晃去,然后不着边际地琢磨着——呀,这回可连看小黄书小黄片都能光明正大了吧?
对了,她老爸明确宣布了,高考过后就放她自由,再也不会过问她的耳机里放的是英语听力还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歌。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她才发现,原来“成年”加上“高考后”,并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每次自以为走到了更宽广的地方,人心也会变得更大,那曾经仰望过的宽阔的空间很快又会逼仄得让人窒息起来。
这就像是生命永无止境的过程。
之后的日子柳蓉过得很颓废,彻底变成了一个死宅,一开始每天中午才起床,早晨她爸妈上班不叫她,结果就是中午下班回来做饭了,一看人家还在睡,大有死在床上不起来的意思。可是这样过了没几天,她就想睡也睡不着了,于是开始过上了黑白颠倒的日子——好像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她终于自由了的价值和意义一样。
之前和朋友们畅想的“学这个”“学那个”“要这样”“要那样”都成了空谈,每天的内容就是半死不活地爬起来,百无聊赖地在网上挂着。
她在学校很多作业压着的时候,总喜欢抽时间挤时间看闲书、租漫画,“戒掉日漫”的口号喊了好多年,却好像比戒烟戒白粉还难似的,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