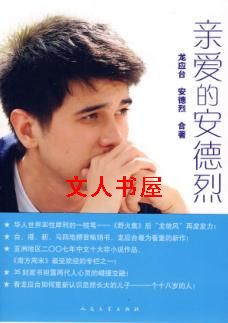爱的价值投资论-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并不想代替你来抉择。”
深黑色SUV在灯火辉煌处停下来。
为首便衣扫眼车里,说:“莫检察长,您应该还在休假吧?希望您能保持一贯的作风,理智理性地看待这件事。”
莫南长笑,对着慕憬说:“不用害怕,他们只是例行问话。只能捎你到此,我先走了。”
----------
慕憬无声无息坐于车后,目不斜视,感觉着车子驶向未知的地方。很远很远,怎么也到不了终点。还是要进那个地方吗,她莫名地想起自己这半年来的挣扎,不禁嘲笑一声。
车终于停在偏僻的一处小白楼前,门口无任何标识。她听见自己还是松了口气。
刚被人拥着进门,就看见一名中等身材西服男子起身,朝慕憬走过来。他扬声说道:“我是慕小姐的代表律师。我想先和她谈一下。”
感受到警方的踌躇,他继而质问,“我的当事人并非嫌疑人,外籍在华人士难道连最基本的人权都不能享有了?”
争取到五分钟时间,他拉着慕憬于一隅小声说:“待会,你只需要表示完全不知情,就好了。”慕憬抬眼,他用更小的声音耳语:“程先生交代的。”
慕憬环顾四周白墙水泥地,他恢复正常声调说:“程先生他在里面。例行公事,谈一谈。”
麻木点点头,突然间有如醍醐灌顶。诚如MK所说,程氏与简氏十几年利益攸关,他倒台,他们亦不会超脱。但他们自信一向做得比简氏更干净利落,没有丝毫把柄留下'奇+书+网'。大概只除了——慕容震手头的那份材料。
原来,那东西里还有——他,程熠微家族,最致命最害怕的东西。所以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让简垮台以摆脱其压制,另一方面更费尽心思要拿到那份东西。如果拿不到,也不可能让其随意出来见光。
他在意的,从来都是她身后——他动之以情,希望骗得她心甘情愿拿出给他;一次次未果之后,他用她致命弱点,来胁迫她。
如今肉在砧板上,剁成碎沫,她自动落进他们嘴里变成可口的一餐。
还有什么好说的?她只会木然点头,随公务人员进审问间。
鳄鱼的眼泪
“是的!”对着刺眼的白炽灯光,泪很快落下来,轻松得如同掌控着眼底闸门。“……从小远离父亲,对他的事一无所知。父亲仅十年前来看过我一次,让我不要牵挂,在美国结婚生子。之后至今从未曾联系过……不回来?这是我的祖国,游子又岂有不回家的道理?我一直很渴望回国看看,不管父亲发生什么事,现在不是封建社会,没有连坐制度,我相信党和政府对我这个罪子是宽容的……
……
巨额资产?我能力有限,一直只是个朝九晚五上班族,刚从慧新咨询辞职,没什么存款……海外帐户都在这里……辞职?噢,遇到美国老师MK Young,他替我买好机票让我回美国发展,……G市?只是随意去散散心罢了。
……
结婚?噢,是的。我和先生Abel Jiang 在拉斯维加斯登记注册,他是普通华裔,已经过世七年。如果可以,我不想再提及亡夫的事……
……
程熠微?是的,我认识。曾经被慧新委派去RC做项目,为期一个月……往来甚密?特别吗,那不过是男人和女人间最自然的交往关系罢了,他很英俊,很慷慨,我不自觉地受他吸引……结婚对象是…部里高干子女……我不知道,毫不之情。好的,我懂了,多谢您好意提醒……”
……
慕憬无意识地捶打麻木僵硬双腿。整整十多个小时,厚重帘子将小房间牢牢笼罩起来,她只能从漏网的一个缝隙里瞥见辰光暗了又亮,亮了又暗,随时间变幻。
很久之后,她昏昏欲睡起来,眼皮沉重得撑不住,来来回回仍是那些话。再后来,他们就作罢了,扔她独处房间。
她复又清醒起来,在心底警惕着戒备着,害怕稍有不慎陷乔木母女于万劫不复之境。
-------
不知道过了多久,夜再度深沉。终于有辆轿车载着她离开。她什么也不想问,默默坐进车里看窗外树木萧瑟,秋风狂卷万物。冬天,快到了吧。她慢慢想,控制着潮涌般扑过来吞噬她的睡意。她不能睡觉,至少现在,还不能睡觉。
车子换了又换。慕憬觉得自己如同一块待价而沽的猪肉,在肉贩中间来回辗转。终于停到潮白河畔别墅区,一处独栋三层小楼前。她独自下车,越过篱笆,慢慢穿过残荷稀疏的私家泳池,走向大门。
泳池种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她在面上挂了大大的嘲讽之意。
简洁华贵欧式装修风格,水晶灯没有流苏坠。她似来过一般,熟门熟路攀上二层,朝暖色灯光的房间而去。那灯光似乎变得刺目起来,她的指尖和心底一样冰凉。
他独坐书房阅读一份资料,低着头,十分投入的样子。听见她的脚步声,头也没抬地招呼她,“你来了?”
见他如此自然,如此镇定,她干涩地说:“您的吩咐都照办了。”停顿片刻,他没有丝毫抬头的意思。她不由说道:“如果还有什么剩余价值,您也尽管来榨取吧。如果没有,我,先走了。”
她总是怀疑他,从头至尾地排斥他,从来没有选择过——信任。看着她白皙面孔上浓烈的眼睑阴影,干涸嘴唇失却血色,眼底深深的忧惧,心中蓦地一痛。他动动嘴皮,“去把自己洗干净上床等我。”
她抬起眼来,既震惊又嫌恶的样子。他慢条斯理说道,“不需要我再说一遍吧。”
她仍不动。他只得又说:“如果你想让她们母女好好活着的话,麻烦照做。”
她立即转身奔出去,几乎是夺门而逃。他放下材料揉揉眼睛,慢慢拨通一个电话号码。身体异常疲惫不堪,刀伤混合着枪伤,愈合得极慢,伤口隐隐作痛。“我答应你。把那东西发过来吧。”他清晰地说。
磨磨蹭蹭好半天,足足搓掉两层表皮,热水浇在身体上疼痛难当。她擦擦头发,如蜗牛般套上他准备好的内衣睡袍,慢慢踱进主卧室。
程熠微倚靠床头拿一本书,假装没看见她满脸犹豫,全身刺猬般戒备的样子,终于等到她咬牙钻进被窝里。他放下书,亦躺下来。
他们共枕于一起。她深呼吸几次才开口,似乎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至少,先把你的资本拿出来。”她说。
他扔给她手机。“自己看吧。”
那是一条来自“F”的邮件。视频里,远远的两个背影,互相搀扶着于江边散步。尽管只是背影,不难发现她们的脚步走得十分安定从容。
“请一定——善待她们。你知道的,她们是好人,应该有好报。”她闭上眼睛,双目干涸,话刚出口便恼恨自己不知道为何还对这个邪恶的男人抱有一丝希望。手指麻木地开始解纽扣。他将手伸过去轻轻搭在她的手背上。“睡吧。”他在她耳畔,说道。
他的怀抱在轻薄丝被里十分温暖,气息清凉而安定,如同松柏般值得倚靠。她太困了,真的很想就此深眠下去。但她不愿让自己沉溺,胳膊强硬地抵到他的胸膛,借力挣脱。一道若有若无的吸气声响起来。她直觉头皮发麻,抑制不住地将手伸向他的衣襟。他一边用胳膊阻挡,一边退到床沿。“乖乖睡觉。”他命令地说。
慕憬手指已经触及睡衣里面厚厚的绷带。“你受伤了?那晚?”她低问。
“不是为你。”他沉闷地说。
“上帝其实不总在睡觉。”她复又闭上眼睛,神色冷淡下来,“你们这种人,多行不义,总会被收拾。你只是活该!”
接受到他的怒意,她突然噤声,及想到捏在他手中的乔木母女,怏怏入睡。
夜里起身,她挣脱他不知何时圈上来的手臂身体重重束缚,籍着微弱壁灯光,突然发现他沉睡的英俊面庞上,挂着一点泪痕。“那也是鳄鱼的眼泪罢了。”她强迫自己这样想着,掩饰心底的震动。
-------
慕憬第二次开始被程熠微“包养”的生活。她不愿亦不敢想将来。只要,他一天不放开她,她就无法摆脱他。
她别无选择地穿着由他提供的带着浓厚他品味的衣服,食用钟点工按他味蕾精心制作的三餐两点,睡在他豪华别墅的奢侈大床上。
然生活并无想象中那般“米虫”。她一直以冷静自持自居,在他面前却总管不住自己的嘴,一不留神嘲讽挖苦打击的词汇就从嘴里如小李飞刀般指向他。他的脸色因此无可避免地黑了又黑,后来每次听完她嘲讽的话便连威胁带报复地指使她去为他做各种家事,从一开始的洗袜子洗内衣进展到做饭洗碗拖地收拾屋子。最后,他干脆把钟点工给辞了。
慕憬俨然成了程熠微家的保姆。当然,考虑到同床共枕因素的话,她大概已经不是普通的驻家保姆级别了,而是类似“袭人”那样的暖床丫鬟。不过他虽长了一副好面孔,却完全不像宝哥哥那么心存善良,那么怜香惜玉,那么相信所有女儿都是水做的……她敢肯定,那家伙必认定她是铁打的,从早到晚不让她有一刻停歇。当然,她更没有袭人那丫头的觉悟——她每晚侍寝的时候简直怨气冲天。可是,因为身体上太累太累了,还没顾上表露出来,就已经深深陷入梦的泥沼,被缠绕。
每次醒来,无可避免地发现他将她圈得死死地,仿佛她是个惯逃犯,他正在对她用刑和宣判。
怒却不敢言出来,害怕他的睚眦必较总有一天迁怒到乔木母女身上,只得尽量避开他。白天的时候有多远滚多远,这样方能控制着自己不与他讲话。然而每个夜里,她不敢思想起,他是如何用淡淡的温暖来极尽可能地贴近她,软化她。
她想起数月之前,她和他第一次“约会”。她竟然傻到将自己的软肋那么主动地讲出来。很多很多,爱……很好,现在统统变成了觊觎者手里很多很多的,武器,束缚……
天天耗在这座豪华“耗子”里做苦力,他亦没有一天要外出的意思。而且,他渐渐地无所事事起来,连工作邮件都不查阅了,十分悠闲地晒太阳喝茶读报纸,看她楼上楼下抹灰拖地,满额头的汗珠。并总挂出一副可恶的笑意来,似乎以此为乐。
她显然没意识到,在他逐渐康复起来的同时,她的面色也添了几许红润,即便穿上最简单朴素的家居服,素面朝天,怨气冲冲,也难掩窈窕身段,如雪色花朵般动人的面庞。
他总是在她上楼下楼风一般穿越过他身边的时候,敛去些许笑意,正襟危坐,假意看报纸。毫无意外地,她丝毫不抬眼皮,当他是空气,提着水管迳自洗车去了。
手机铃音终于打破两人之间诡异的安宁。他逐渐敛去笑意。她在不远处的地方,竖起全身毛孔。
初始于STAQ
沙煲里浓汤翻腾着,慕憬调小火候,边切菜边计算采取何种步骤才能将几个菜的做菜时间最优化,亦即时间压缩到最短。暖气烧得厨房有点热,汗珠地从鼻端渗出来。
程熠微无声无息自背后紧紧抱住她,下巴凑过来贴近她光洁的面颊和额头间。她微微懊恼地挣扎两下,就听见他在耳畔呵气,用极具蛊惑力的嗓音央求:“就一下。”
这是他们第一次于日光下拥抱。身体不自然地僵硬,手里拿着不知道该扔掉还是该一直举着的菜刀。如果扔掉,会不会砸到自己的脚?从厨房窗户看出去,天空阴霾,浓墨重彩。忽然生出一丝非常可笑的悲情来。她大概永远都是见光死,只适合将自己一直埋于他脚底,如淤泥般烂在那里。阳光,永不可能照到心间。
“你该——走了?”她听见自己干巴巴地问。
他没有应声,恼恨她的洞悉,将她拥得更紧一些,似乎想捏碎她揉进自己的血肉里。停了片刻,他为她拭去鼻尖汗珠,柔声说,“只是跟几个银行的朋友吃饭。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她摇头。
他很快地说,“你也出去走走吧。总在家里会闷坏。”
她动动嘴,说出来的话还是免不了讥诮,“原来我还没有被宣判监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啊!”
他慢慢松开怀抱,对她的嘲讽充耳不闻,若无其事地说,“车库里的车子,你可以随便挑着开。晚报独家披露之后,上面关注得很密切,不仅部里的人不会轻易放松调查,简远山的死忠、政敌们也蠢蠢欲动。那几个人——训练有素,不会打扰到你,只是远远地保护而已。走的时候记得把手机带好。”
“暴露我的人——是谁?”她对着他的背影追问。
他顿住离开的脚步,淡淡地说,“初步肯定由简远山秘书交代出来,并提供了一段录音。至于谁买通调查组泄露机密,有何目的,就不得而知了。”
目送黑色轿车驶远,慕憬蹲在池边拔几支残荷杆玩,旋又扔回池底,拍拍衣襟朝车库走去。
之前已经受命前来为五部车子洗刷打蜡过一番,因此对车库里的情况并不陌生。无一例外的进口车,她朝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