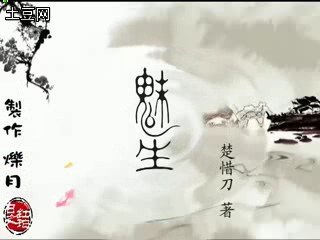魅生-第9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许他必须失却一些,得到另一些。真是不胜寒冷啊。高处望见的风景纵有万千气象,自身却在极度的落差中倍感寥落孤寂,回首看去,竟没法重回过去的路。
柏根老人端详他眉宇间的神情,七分正气,三分妖气,奇怪的是那股子妖气并不邪佞,如绝世的宝玉,骨子里清清荡荡,些许微小的杂质亦成了魅力所在。
“我们的人肉究竟有什么用?”老人直截了当地问道。
“人的颜面或形体破损,通常可取自身的皮肉弥补,只是往往供不应求。如用他人血肉,或取下即坏死,或无法合而为一,纵然亲生父母亦是如此。唯有若鳐人肉非常奇特,不但能完好融和在他人体内,更能生肌化淤,提前愈合伤口。”紫颜道,“上天给了你们一族特别的恩赐,你们平时如果受伤,也能极快康复,对么?”
柏根老人叹息,这是一柄双刃剑,给了他们更强的生命力,也迫得他们险些失却自由。
“你说得没错。即使被猎人捕到后剜去血肉,身体残缺不全,只要内脏不损,我们依然可以活着。可是那样的活命,有时生不如死。”
红光浮泛,侧侧仿佛被刺眼的鲜血扎得撑不住眼皮,似乎看见血肉模糊的若鳐人,带了一身伤疤走来走去,触目惊心。
紫颜道:“伤口能快速愈合,血肉就会渐渐长回来。”柏根老人摇头,“受损太重,则形体仍是不全。好在我们知道有种小鱼可吸食淤血,修补形体……只是……”紫颜不禁动容道:“真有这样的东西?能否让我瞧瞧?”柏根老人殊无喜色,招了招手,对侍从吩咐了几句,那五人走去打发众族人退下。甲虫向紫颜和侧侧欠了欠身,消失在一条地道的入口处。
“你们跟我来。”柏根老人面容黯淡,矮小的身子钻入一个洞口,紫颜和侧侧跟随其后。这条路够宽敞,走了几十步就到了一处石门前。柏根老人打开门,侧侧神情凝重,紫颜的眼里则扬起了神采,皆没想到会有如此惊异的场面。
一张铺满皮毛的土床上,躺了个肥硕无比的胖子,肚皮高耸如坟头,看不见他的脸。一个清瘦的中年男子守在他身边,面上满是倦容。那胖子盖了厚厚的毡毯,听到动静“哼”了一声,却无法起身。柏根老人对他说了两句若鳐语后,胖子“咚”地一下,像是放低了头。
柏根老人叹道:“这是三年前从猎人手上抢下来的孩子,叫阿杰那,就是红草之意,今年十七岁,很久没下过床。他和他娘一起外出时被抓,猎人害死了他娘,算他命大,流了满地的血倒救活了。当时他浑身只剩了骨头,像个骷髅架子,我们把他投进碧漓海子,引来无数僧葵叮住他的身体,勉强在一夜间止了血。僧葵医好了他残破的伤口,也让他落下了病,上岸后躺了三个月,他就胖得没了人形。唉,碧漓海子也救不了我们。”
红草是极北之地一种顽强的小草,在冰天雪地里恣意生长,从不见衰败。紫颜这样想着,走上前掀开红草身上的布衣,层层堆叠的肥肉翻滚出来,气味依旧是香的,模样令人作呕。紫颜看见少年变形的胖脸,挤得五官挪移了位置,浑似一个怪物。见有外人来,他小小的眼睛里射出灼热的目光,用力地向紫颜眨着眼。
若鳐人本就身材矮小,一旦发福则更臃肿难堪。紫颜问:“他吃得多么?”柏根老人摇头,指了光秃秃的四壁道:“我们每日给他送些水和果子,想让他少吃些瘦下来,不想饿了两年多,还是老样子。”
紫颜想了想,对红草说了声“得罪”,捏起手臂的一块肉仔细端详片刻,继而问道:“有可以写画的东西吗?”柏根老人道:“你们走吧,我带你们来看他,是想让外族人知道我们的苦难。你们帮不上忙。”
侧侧知道紫颜的心意,忙对老人道:“他是医师。”
老人半信半疑地看了看他,叫人取来一盘辰砂。紫颜用木条沾水调匀了,在红草身上划线,“臂膊内从这里切掉多余的肉。”他画了两条线,又揭开毡毯,在红草的肚子上勾勒,“由脐处下刀,切开腹筋,剥离皮下肥腻油脂……”
他尚未说完,柏根老人瞪大眼道:“等等,你要切开他?”
“我能令他恢复原样。”
柏根老人略一犹豫,紫颜续道:“用药麻醉,红草不会有任何痛苦,醒时就是一个正常人。他可以自由行走,甚至跳入碧漓海子畅游,当然,须休养半年之后。”
“你怎知不会害死他?像有狐人一样。”一样是切割血肉,杀人与救人,看来那般相似。仓促间柏根老人觉得抉择是件困难的事,他已经足够老了,可听到紫颜的话,竟拿捏不定主意。
紫颜微笑,眼角流过一道光,“以我的性命担保。”侧侧悬了一颗心,禁不住伸手拉他的袖子,手到半空又停下,缩了回来。他的笑容一如以往淡定从容,她默默地想,这便是无事。
“你真能救他?”床边那个一直不做声的中年男子忽然开口。柏根老人对紫颜道:“这是孩子的父亲,特雷塔,我们以此称呼飞鸟。他是我们族里跑得最快的人。”
“不。”飞鸟难过地摇头,揪紧的眉令他看上去仿佛又是哭,又是笑,“阿杰那才是,他从小就比野兔更灵敏,能快过鹰的追逐。可你看看他,连路也走不了……实在是太不公平,不公平!”他靠近紫颜,搓着双手,眼中多了一份热切,“如果你真能救他,我愿意赌一回,阿杰那一定也愿意。”不等紫颜承诺,他急急倚在床边,对了儿子说起若鳐语,像在哀求、自责、鼓励、催促,说话的腔调大起大落。少年眼角滚出两行泪,艰难地点了点头。
柏根老人同情地望了他们,对紫颜道:“他认为是他没有陪妻儿出门,才会发生惨剧。唉,今天先到此为止,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如果确有必要,明日再安排你为他医治。”他留意凝看紫颜的神情,想,也许这个人的到来是天的旨意,在阿杰那经历了多年苦难之后。
紫颜和侧侧坐在一张石桌边,这是若鳐人最高的桌子,印刻了部落尚水的花纹。两人若有所思地吃着野果和杂粮,忽然同时开口。
紫颜道:“要拿我的镜奁来。”
侧侧道:“得知会他们一声。”
对视而笑,侧侧道:“你不怕他们担心?”紫颜托了腮,悠悠地道:“长生说起来不小了,磨炼他的心性也好。你不想看看若是没了我,他会何以自处?至于萤火,没了我很知道该如何,左格尔更不用操心。”侧侧苦笑,“长生究竟有多大年岁?看去还是没长大。”
紫颜垂下眼帘,喃喃地道:“等得太久了……他不喜欢易容术,我总想着慢慢诱导,有日他就会像我一般迷恋。但是越来越来不及了,谁知道我哪天会倒下,就像……”他蓦地止了声,掩嘴笑道,“呀,又说了不该说的话。”浅浅的笑荡过来,像要遮去所思所想。
易容是一面惑人的镜,人的理智亦是。举手投足,偏要点缀升平,只要心念稍动,谁都是那个戴了假面的人。侧侧按下忧思,像是没听见晦气话,戳了他的额笑道:“好在没先遇上有狐族猎人,否则你我就成猎物被捕了去……”
“你怕我遇见他们,又出高价买了若鳐人肉,对不对?”
侧侧沉默。
“猎人们如是杀人的凶手,应有律法去处罚他们。我只要有一丝机会,仍会将买来的材料用于易容,不论它的来源如何,是否人的躯体。”紫颜淡淡地说,“本来终我一生,就在和人的肉身打交道,不会像你们对这个大惊小怪。你知道么,师父年轻时曾做过多年仵作,剖过大量尸体,可惜我没他这般走运。”
侧侧讶然,“我没听爹爹说过。”想起当年紫颜买人肉时姽婳在场,应不会活生生割了若鳐人,便问,“那时你花五百金,究竟买了多少?”
“若鳐人刚迁徙到这座山时,因水土不服有大批族人过世,他们在碧漓海子将这些人水葬,有狐族猎人就偷偷捞了几具尸体卖钱。我买的人肉,听说是最新鲜的一具尸身上的,甚至都没下水,分量倒不多……多下来的金子,请猎人安葬了那人的残骸。”紫颜淡淡地道,“虽然那个若鳐人非因我而死,死后的皮囊损了更没什么打紧,叫鱼吃了一样死无完肤,但我明白他们族人的心意,我也算对不起他们。”
“你为何不说清楚?”
“太麻烦。”紫颜眼底掠过一丝疲倦,“何况对不起他们的人太多,若真的受一刀,也是应该。”
侧侧吃惊地望着他,这是易容师的悲悯,还是彻悟因果后的决断?他全然不顾念个人的安危,紫颜心中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又或者他了无牵挂,也就不顾惜自身。她只觉微微的混乱,看不透他玄奥内心的所思所想。她不认为那些罪赎虫真能看破人的罪恶,柏根老人是否明白了他的心意,才放弃了对他的惩戒?
她放弃了猜想,叹道:“易容一点也不风花雪月,幸好没由我继承衣钵。”
紫颜微笑,转了话题道:“若鳐人既然修建了庞大的地道,就请他们帮我取镜奁吧。”他站起身,拂去衣襟上食物的碎屑,走到在不远处看顾他们的甲虫面前,“你能上去为我拿一件东西么?我要用来救红草。”
甲虫忽然问:“你会不会失败?”他粗糙的皮肤里映出微微的一抹红,紫颜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甲虫有多大年纪了?四十、五十?这个部族以长寿闻名,他大概看够了若鳐人流离之苦。
“谁都会有失败,”紫颜盯了他微笑,“只是如今我,已经很难遇上。”甲虫点点头,问清了营帐的位置和镜奁的形状,领命而去。
柏根老人盛了湖水泡的清茶,送到两人桌上,他的眉眼大见和缓,对两人多了一份热情,“地下憋气,难为你们了,不过住久了,反而忘了原先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们藏在地底,日子可比在以前好过?”侧侧问。
“再恶劣的地方,住久就惯了,只要能平安活着。三年前我们挖好了大部分地道,多谢那些野山豚和穿山甲,还有食土的巨金虫,这个地下王国足够隐秘和坚固。如果阿杰那和他母亲不是偷偷外出,到海子边去捞鱼,本不会再有惨剧发生。这几年滞留在山里的猎人越来越少,零星还能看到一两个,多半是空手而回,以为若鳐人不在此地了。”
“山间处处是陷阱,猎人也会是惊弓之鸟。”紫颜若有所思地道,“没想到那些陷阱是你们布置的。”
“只有想法子逃脱命运的摆布,才能躲开不幸。”
一劳永逸的法子。人间乐土。可永远会有意外。红草是一个意外,他们的掉落也是,如果他们是心怀叵测的来访者,若鳐人是否能逃脱灭顶之灾?侧侧转头看紫颜,他让千姿保护了丌吕族人,让皎镜庇护波鲧族少年,但如今,又能如何襄助若鳐人?
他不是神。
饭后,紫颜回去探视红草,侧侧满怀心事,从发髻拔下一根绣针,反反复复地端详。指尖可拈花簇雪,这是她唯一熟稔的技艺,无法拯救任何人,却使她从孤独与悲哀中解脱。柏根老人留意到她,多看了两眼,侧侧笑道:“我给族长绣个椅垫。”
她不由分说讨来了一块薄皮料子,因手头没有绣花绷子,索性将皮料四角钉在凸起的泥墩上。乱针叠鳞,彩花雕绣,些小的空隙被针线巧妙穿过,偷天换日。不多时,一幅云川图蔚然其上,将呆板的皮料衬托得有了仙气。
“这是你心里的某个地方吧?”
侧侧摇头,“我随手绣的。”
“那一定是很重要的地方,你只是忘记了。一切奥秘都在人的心底,有的人能找到,把过去的记忆印下,有的人一辈子迷迷糊糊,再也想不起来。我们一族以前可能生活在水底,或是地底,我们靠近了大地的心,就过得很幸福。”柏根老人抿了一口湖水泡的茶,水气氤氲里,他像一只野猫诡异地凝视着侧侧,仿佛随时会“喵呜”一声不见了。
“这幅画儿真是好看,你的心看见了,才能画出来。”
他把侧侧的刺绣叫做“画”,侧侧不在意,只想着他的话。也许真如他说的,她绣过的纹样,不过是前世的记忆,它们本来就在那里,等她一点点缝制拼补,完成最初的模样。她又想到紫颜,他替别人易容时,是否也在绘制谜一般的前尘?
此时在另一处,紫颜为红草搭了脉,一脸和蔼地说着话,飞鸟忙不迭地从中翻译。要对红草周身用刀,必将费时多日,他须让父子俩对他深信不疑。尤其是要消除红草的畏惧,让少年肯全身心地将自己托付给他,紫颜破天荒地在红草面前温柔可亲地闲聊,直至慢慢消去了对方将被再次剖开身体的恐慌。
飞鸟在红草的床头奔来跑去,拭汗、端水、松衣、盖被、喂食,浑不知疲倦。紫颜不时瞥他一眼,想,这个父亲真是辛苦。这时,红草咕哝着回了一句,飞鸟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