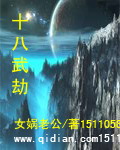十八年后一好汉-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云箴呆呆怔怔,“聊天儿。”
“聊什么了?”
“很多,小时候的事,一起的事,气氛很好,就像以前还没有淑宁时那样。然后我就说,我爱他。”
“他呢?”
“说他知道。”
“这就完了?”
“他还说淑宁的事只有他一个人念念不忘地揪着也挺没意思的,就算两清了吧。”
“就算?”
“其他的他说考完试再说,我想也是,十几年都熬过来了,不差这十几天了………怎么就风云色变了呢?”
别说你,谁要能搞清楚羊印颉想什么,我就拜他为师。
我拎起云箴又回到宴上。
牧观和小羊已经坐在了一起,有说有笑地正说着什么。我端起一杯酒就蛮插进他们中间。
小羊笑,“你看,我就说他想揍我,牧观兄,你可得保护我。”
牧观笑着应他,“我试试。”
我压着火,“你们早合计好了吧。”
小羊摇头,“我有预谋,牧观兄是被拖下水的。”
“我自己也想去。”牧观私下握住我的手,“别生气,回去再说。”
“我走了。”我生气。
“去哪儿?”
“回家。”
我回家就奔院里,将衣服扯了随便扔在地上。
清紫上前拾整我衣服,“少爷怎么了?明天还得穿呢,牧观少爷呢?”
“死了!”
“少爷,”清紫上前掩我的嘴,“可不能胡说。”
我抱住清紫滚到了床上,埋在她的胸前。
清紫一声惊呼,随即就掩住了嘴,“少爷?”
我问:“清紫,你什么时候也走?”
“清紫不走,一辈子都服侍少爷。”
“不能瞎说。”
“朕赐婚就是了。”
我和清紫立刻坐起来。
云礼阴着脸,和着外面透进来的清白月光十分骇人。
清紫匆匆跪了,然后匆匆掩的胸口退出房中。
我没有动。
云礼也不以为忤,坐到我的床边,“生气了?”
“皇上怎么来了?”
云礼把我按倒,并排躺在我的身边,“朕当时很犹豫,才那样说话的。那个羊印颉,”云礼的口气突然很冷,“竟然连天家也不放在眼里,不挫挫他的锐气,让他明白明白什么叫‘生杀予夺’,来日必定成害。”
我不敢作声,因为云礼很生气。
“至于牧观———”云礼柔和了许多,“他倒是总叫朕意外,不过让他出去历练一下也是好的,总在朕身边,成不了大器。”
“皇上还有什么谋划?”我最不喜欢看的就是云礼年少的脸上老气横秋。
“你还真生气了?”云礼翻身捏住我的下巴,“就好到那么舍不得?”
“舍不得。”
云礼噗地笑了,压上来舔了舔我的嘴唇,“就放出去一年,总舍得了吧?”
我默不作声。
云礼跳下床,“朕得回去了,等秦卿走了,你就来朕身边做贴身侍卫吧。”
“臣———”
“别欺负朕了,”云礼按住我的肩膀,“朕还本想将秦牧观挑个错处流放了,然后用铁链子把你拴身边呢。就怕你不乐意,又要给朕见红。”
云礼说完自己先笑了。
我跪下来,“恭送皇上。”
“撵朕走?”云礼还笑着,“好,朕走。”
他转身出门,我抬起头,正看见镜子中映出他敛起笑容,换上一张阴沉的脸,然后一闪而过。
云礼从来都是一个有心计的小孩儿。
我怎么就招上他了?
送走了云礼,我又躺了一会儿。
清紫敲敲我的门,“少爷,牧观少爷来了。”
我不作声。
门外又敲了几次,没有声音了。
我气得直磨牙!秦牧观,你就这德性了是不?我不主动,你就死活不动是不是?你动一下会怎么着啊?
我蒙着头睡觉。
迷迷糊糊的又听见清紫说,“牧观少爷,您也歇下吧,少爷应该睡了。”
静了片刻。
清紫又叹了口气,“那我给您拿张毯子,现在夜凉,冻病了少爷要心疼的。”
我下床拉开门,牧观就笔直地站在廊下。
我问,“你干啥?”
他答,“等你。”
我就怕了你这清清淡淡的劲!
我拉住他的手就拽进屋里,将他透着凉气的外袍鞋袜全扒了塞进早被我捂暖的被子里头。
“宝友。”他握住我的手,“你知道为什么小羊———”
“别提他。”
“他是为了你———唔————”
牧观的唇舌还带着琼林宴上的淡淡酒香。
硬闯进去时他痛苦的表情让我泛出一股惩罚他的奇佳妙感。
“为了我?我就那么讨人喜欢?”
牧观勉强浮上一丝笑,“他说,你必定要去打仗的,雀翎必然是后方,他要先行一步,周全准备。”
“所以你也跟着去,也是为了我?”
“我———”
他静了半刻,第一次挺腰迎了上来。
我们翻滚在一起,拼了命地把自己往对方身子上送。
恍惚间我觉得天地间就剩下了一个,他中有我,我中有他。
我顺了顺他汗湿的头发,将他搂在怀里。
他埋着头,动了动嘴唇,最终却没说出来什么。
算了,我知道他心里有我,那就成了。
不就一年么?也很快就会过去。
春看桃花夏赏柳,秋送雁归冬温酒。
不就,一年么。
一别三年!
========================
50
春节过后,十五未至,天稀稀落落地又下了几场雪,偏赶着我当值的日子,盐面子突然就变成鹅毛片了。
佳仪追出来给我加了件毛坎肩,拉着我的马道,“宝哥哥,今天一定一定要早点回来啊,二哥今天回来,说是大哥给家里准备了好多好多礼物,我们等你回来先挑。”
我笑笑,“哪件都好。”
佳仪笑着弯起眉毛,“二哥和我就是想看看,今年你还能不能挑出来大哥想送你的东西。”
“好。”我翻身上马,“要是没事,我就请个假回来。”
佳仪用力地点点头,跑回到廊下冲我挥手。自打牧观走了,他们就住进了我的家里。
这两个孩子都隐约知道我和牧观的事,他们不反对,似乎,也算赞成。我爹的心思我不知道,我娘,似乎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自打三年前我把牧观关在院子里死缠了三天,她就再也没张罗给我娶媳妇的事。
我进了宫,宫里也正放着年假,人少得清冷,云礼戴着毛皮帽子窝在暖炕上,见我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他顺势握住我的手揣进自己怀里,“嗬,真冷。”
“我就着火盆捂就成了。”
“朕就巴望着为你着个凉,让你衣不解带地照顾朕。”云礼斜起眼睛白我一眼,细长的眼底带着只有我才看得见的幽怨。“高兴了吧?这么老实?”
“什么?”
“也学会和朕装模样了?秦牧观要回来述职,你不高兴?”
“啊?”
云礼闪过一丝疑惑,“他没和你说?”
“大概,是要给我个惊喜吧,哈哈。”他确实没和我说。这些年,他和我说的话越来越少了。
“瞧你言不由衷的模样。”云礼凑上来,亲了亲我的嘴唇,偏头嘟囔道,“怎么裂了?一会儿下去擦点油。”
“皇上,臣想请假。”
“不舒服?”
“不是。”
“朕看你和朕单独一起就浑身不自在。”
“看看,连以前那耍皮子的功夫却退步不少。”
云礼站起来,“和朕去泡温泉,泡完了放你回去。”
我起身恭恭敬敬地跟上。
云礼脱了衣服,就让宫女们都下去了。
等人走干净了,他就来解我的衣服,“穿这么多干什么?”
“有点儿冷。”
云礼解开我的亵衣,手指顺着我的身子摸了一遍,然后拉起我一起走进了池子。
进了水,他的手就会放在我那儿。
我照旧闭着眼倚在池子边上挺尸。
云礼自得其乐地摸着我,又把我揽进怀里抱着,“宝友,朕想好了。”
我用鼻音哼着回他。
“今年就把秦牧观调回京城来。”
我没有反应。
我也不知怎么了,竟然平静得跟没听到一样,估计也是搁云礼这祖宗身边呆多了吧。
云礼咬了咬我的脖子,“不高兴?那你朕再说一个你爱听的,朕决定攻打凤凰谷了,安插你在中军。”
果然。
他来了,然后我走了。
我闭着眼缓缓道,“臣想做先锋。”
“急什么,有你的仗打,而且保证让你打大仗。”
“皇上——”
“朕意已决。”
云礼说罢,安抚似的亲亲我的脸颊,“这么大一场阵仗,总要牺牲一些人,你不要多想,朕会安排一个适当的时机让人进局,保证不让别人议论你捡别人便宜,把功劳作实。”
“臣,谢主龙恩。”
“真谢朕就————”他手下加了一把劲。
我没吱声。
他也索然无味儿,“行了,朕再自己泡会儿,你先走吧。”
我爬上岸。
云礼背着我淡淡道,“明年,朕会大婚。”
“恭喜皇上。”
“滚!”
我拾起衣服快步滚了。
交了值牌出宫,雪竟然停了。街上又做开了买卖,临近十五,各种花灯元宵算命摊子摆得到处都是,我一时兴起,也下马沿街慢慢地走。
佳仪喜欢兔子灯,牧砚的镇纸好像缺了一角,我娘前天还唠叨着说想给我爹再缝两只皮护手,清紫好像很喜欢春节送她的绒花,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样的。
往年过节,我、小羊、云箴都会上街来瞧漂亮姑娘,如今小羊走了,云箴去年也终于巴巴跟着去了,今年只有我一个人了。
说起来,我还没和牧观一起逛过街。
我眯了眯眼,看到前面灯摊上好像有个认识的人。
不算漂亮,但很清秀的脸,清澈澈的山涧水一样的目光,以及眉间的那一颗痣
娘的,少爷我矫情什么,上啊。
“借过借过。”我挤到他眼前。
他抬起头,“宝友?”
一瞬间我的三魂七魄整十个家伙又全飞脑瓜子顶上去了,心花肠花肚子花全部怒放灿烂了。
我一把抱起他,“真的是你?”
“是我是我,先放下我。”
他红着脸紧张地四处张望。
我摘下皮帽子扣在他的头上遮住他的脸,“没看过女扮男装啊?少爷撞见心上人了,心里高兴!”
人群里暴发出一阵哄笑,还有人凑份子叫好。
我将人往怀里一带,“娘子,咱们回家,你可不能跟我赌气再跑了啊。”
牧观垂着头,拉着我匆匆向前走。
身后又人怪叫,“可别把你娘子再气跑了啊。”
我回身摇手,“一定不能。”
牧观走得更快了。
我乐得不敢怠慢,拐着他进了酒楼。
“你怎么———”
我爱他又气又恼的表情,“我见着你高兴,你怎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
牧观不说话,只是抿了一口热茶。
我凑过去,轻轻地,吻住了他的唇。
“宝,宝友。”
我搂着他抵在椅子上,毫不犹豫地伸进他的裤子,“你知道这三年我怎么熬的么?”
我他娘的没出息地哭了。
牧观愣住了,轻轻拍了拍我的背。
“你发誓以后都跟在我身边,寸步不离。”
“宝友你……”他失声笑了出来,“你怎么还是———”
我抱着他跨坐在我的身上,“你不是心里有别人了吧?”
他蹙了蹙眉,抓着我的肩膀低头闷哼了一声。
久别胜新婚。
51
等我收拾好了就去叫小二点菜。
菜上齐了,牧观却只喝了些肉糜粥。
“多吃点。”
“嗯,”他给我也夹了一些。“印颉和小王爷那边,还是老样子。”
我垂头亲他的唇上的粥汤汁。
“印颉去欢馆鬼混,小王爷居然也跟着一起去陪着。”
“嗯。”
“印颉喝八岱王儿子的满月酒,小王爷就化装成路过的镖客,也上去凑份子,说是印颉总和土匪们称兄道弟,怕他喝多了胡混,气得印颉拎了把柴刀一路追着他到山下,最后好歹在营门口砍下一片衣服才算罢手,都成了我们那儿的笑话。”
“哦。”
“入秋的时候印颉染了疟疾,烧得糊里糊涂的,还挣扎着去盯麦收,小王爷又心疼又看他糊涂,就拿军粮糊弄了他一下,骗他回家养病,结果等印颉醒了,一张状子就告上来,又是骗瞒朝廷命官,又是私调军粮的,到底折腾得小王爷在他的大堂上被罚了二十杀威棒。”
“是么?”
牧观笑了,“小王爷也趁机在印颉的房里赖了大半个月,印颉一开始还去睡书房,可没两天降了霜冻,衙里炭火实在不够烧两间屋子,印颉冻得受不了,就跑到我这里来躲了好几天。”
“呵。”
“哪里躲得过去呢?小王爷带着一队兵就过来了,我那的客房都不够招待,若论职务,有些人比我还高,叫我陪同巡察,我也只能一道出府,结果…………”
我不作声。
“到底叫他们把两个人挤到一间房里去了。印颉走之前问我,是不是有些事真是命中注定,改也改不了?我都不知道———”
他健谈了,可我不高兴,“牧观,你为什么总在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