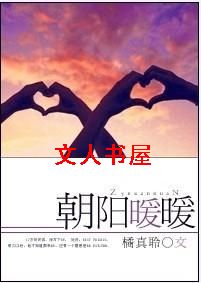金鸡朝阳-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滴酒未沾,这么一叫骂心里的苦痛和愁闷倒发泄了出来,说不出的通畅。她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捋袖伸手,戳着我的胸口,骂道:“你个穷乡巴佬,滚你妈的蛋,几杯酒钱还害的老娘发脾气,没碰着过的事,你妈的!”我也跳了起来,破口大骂,那动作言语幼稚的像个孩子。那女的一击掌,朝天一声吼:“十三太保!”
不知道哪里就冒出一队人来,我数数,还真是十三个人。我大叫:“鬼日的,原来是家黑店。”那女人早溜了出去,十三个彪悍的男人围了上来,先下手为强,我从吧台上抓过一只酒杯,猛砸出去,那些人不约而同的往后退了一步,我一个翻身,坐上了吧台,双手一撑,滑到了另外一头,起身纵跃,翻了出去。正自高兴,酒吧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一窝蜂的堵住了门口。
“黑店?还讽刺呢?你狗日的讽刺我是不是?别想走了,今天不剁了你老娘以后没法子混了。”那女人在后面喊,“这全都是我的人。”
“我是酒仙。”一个男的说。
“我是酒鬼。”又一个男的说。
“我是酒妹。”一个女的说。
“我是酒施。”又一个女的说。
……
我吓了一跳。
“还讽刺呢?砍死你!”众人齐声吼。
我脸上抽筋样的难看。
“喂,要不要帮忙?”一个好熟的声音。我扭头一看,是张柏兰。她笑吟吟的看着我,说:“怎么搞的?要闹事也不要闹的这么大场面,难收场啊!”我说:“你冒出来顶个什么用,只不过多个人挨打而已。”她摆了摆手,说:“你老小瞧我,看着!”她双脚在地上一跺,身子纵起,双手抱住了舞池边上的大铁柱子,右脚一点,左脚借力一撑,扑了出去。那十三个人立马分成两队,一队围向她,一队向我袭来。我看这些男人个个肩膀宽阔,臂粗拳大,是经过长期训练的打手,我怕她吃亏,忙奔了上去。那些人动作也还利落,将我从中截下成双重式围攻,前面一重成三角位置攻我面门和左右腰际,外面一重成四方阵形待第一重退后,立马抢上,分攻我前后左右,如此反复数次,成了车轮战。
百忙之中我看了一眼前面的张柏兰,她上蹿下跳,左冲右突,却不在那六个人的攻击范围之内,正值庆幸,我左肩上挨了一拳,身体失去重心向右边摔去。在我身体旁边倒着一把椅子,我一个打挺起身去抓,没想后面伸出一只脚来将那椅子踢出了丈外,我转身一看,是个老头儿,他手里还拎着个酒瓶子,见我转身瞪着她,慌忙退到那堵门的人群里面了。
“都住手!”张柏兰执了匕首抵在了那女人的咽喉上。
我上前就是一个上勾拳,将那把我打飞的男人打的吐牙血。那些堵门的人顿时大喊大叫,甚至有些恸哭不已,如丧考妣。我看了直笑,那十三太保却心有不甘,有再攻的冲动。
不知道哪里跳出来一个女的,大叫:“误会啊,误会。”她拉着我,一脸兴奋的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打量了她一眼,摇了摇头。她跑到被张柏兰制住的那女人面前,说:“盈姐,这肯定是个误会,我认得他的,他是燕燕姐的朋友。”她又转向跟我说:“我叫明明啊,上次在我们宿舍,两个追你的人,我有让菲菲和佩佩咬他们的,你忘了?”
我顿时恍然,忙应道:“记得记得。”我摆手示意张柏兰放了那女人,说:“今天就看燕燕的面上,放了你。”那女人啐了一口,说:“这话我说还差不多。”
那十三太保和堵门的人哄一下散了。我拉了张柏兰出门,问:“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她偷偷扭头往那酒吧里看了一眼,拽着我迅速的折了回去,说:“我想了很久,要找到老爷子制造动力饕餮号催情药的基地和冰工厂,必须从那些贩药或吸毒者入手,再顺藤摸瓜一步步的寻过去,这样机会就大的多了。”我和她又进了酒吧里面,在进门的那一瞬间,我仰头看了看酒吧的招牌:舞棚酒友快活居。门旁边还立着一块显眼的牌子,上写‘欢迎新老会员鼎力加盟,敦请警察与吝啬鬼止步,谢谢!”
一间包厢内。
张柏兰说:“我就是跟一个女的进的这间酒吧,刚才就因为你的事把她给跟丢了。”
我问:“谁呀?贩药的还是吸毒的?”
她说:“吸毒的,跟她两天了。这时候,好像犯了瘾,正到处寻人买毒品呢!”
包厢的门吱一声响了,我和张柏兰敏锐的躺到了卡拉OK大音箱的后面,探头看去,却是盈姐和明明,后面还跟着个蓬头垢面时不时痉挛似的猛吸着鼻子的女人。张柏兰抓着我的手,轻声说:“就是她。”
“盈姐,给我一点吧!”那女的跪在地上哀求。
“我真的没有了。”盈姐说。
“盈姐,你不能看着我这么痛苦死吧?想当年,我们大家一块从村子里头出
来的时候——”她又猛吸一下鼻子,很吃力的说:“那时候穷,我连自己的一条换洗裤子都留你穿的,你现在不能把我给忘了啊,盈姐。”她用手使劲的来回搓揉鼻子,很明显的看到有鼻血的流出。
明明在一旁看的不忍,插话说:“盈姐,我看英子她快撑不下去了,你就给她一点吧!”
盈姐无奈道:“你又不是不知道,上次在找朋友酒吧,萍儿和兔子喝酒闹事,黄山就那事指明了要断我们一个月的货。”她看了看开始在地上挣扎的英子,皱眉道:“早叫她不要沾那玩意儿,不听!”明明说:“那别的什么人那里可以买点应应急嘛,你跟道上的人都熟。”盈姐不耐烦道:“黄山那厮都发了话,谁敢卖给我们呀!”明明忽然说:“盈姐,老爷子不是最近推出了动力饕餮五号嘛,听说那里面就含有冰晶。”盈姐一张脸沉了下去,说:“那东西你敢用?春药和冰毒一结合,可是冰火两重天,尤其是我们做这一行的,英子她以后想把毒戒掉就难如登天了。”明明说:“那怎么办?”盈姐搓了搓手,一咬牙,说:“到外面叫两个人进来,把她绑了,再给她灌水。”
正文 第十章 游离 (下节)
(更新时间:2007…7…5 21:19:00 本章字数:4410)
那英子蜷在地上一个劲的抽搐,像极了一条狗,一条被人割破咽喉却还残余一口气可以倒在地上挣扎两下的狗。我看不见她的脸,却可以想到那张扭曲的不成人样的面容,是那样的惨不忍睹。我忽然想起了郦一茜,那个可怜的女人,都好久没见过她了,不知道她现在成什么样子了?或许死了也不一定,我想,我还是该去看她一回的,哪怕真死了,到她坟前献束花也好。
明明领了两个男人进来了,抄了绳索。明明问:“盈姐,要不要拿块毛巾堵她的嘴?我怕她受不了会咬舌头。”盈姐扬了扬手,说:“先灌水,”她想了想,“还是灌酒,灌酒比灌水好,赶紧!”正说间,那英子癫狂的从地上蹿起身来,抱着头使劲的往一边的矮几上撞,厚厚的玻璃碎了,她额头也是血肉模糊。盈姐一急,上前去抱住她,那英子猛一个转身,一手勒住了她的脖子,一手抓了块玻璃片抵在她的咽喉上,她手控制不住的颤动,看那盈姐的喉咙上已被扎出了口子,血顺着胸口流到衣服里面。
明明大叫:“英子,你别乱来啊,别——”
“你闭嘴!”她的鼻血不知道什么时候止住了,却换成了粘稠的鼻涕,在人中和嘴唇上结下的小血板块上流下来,和了口水变的一塌糊涂,像个不能自理的孩子。她的两片嘴唇不停的打颤,嗓子还哆嗦,说:“我……不想杀你……盈姐……你不要逼我……快交出来……那五号……”
盈姐脖子里憋着劲,一动不敢动,小心翼翼的说:“英子,那东西伤身的,你——”
“快拿出来!”她手里的玻璃片似乎又扎进去了一点,那血汩汩的从那玻璃尖尖的口子里涌出来,流的更急了。
明明在旁边喊:“盈姐,英子她疯了,你快给她吧!你看她的眼睛……”
那双紧紧绷着到不能收缩,凶悍而邪恶的眼睛,那里面的瞳仁深邃的如同黑暗崖洞里隐藏栖栖的乌鸦。我正为这双眼睛感到恐惧的时候,盈姐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一粒药丸,递了给她。我咬着嘴唇静静的睁大着眼睛,几乎都感觉不到张柏兰那手指上尖尖的指甲在抓着我手腕的同时快陷到了肌肤里面的疼痛,她一样的紧张。
英子的癫狂迅速静止,紧绷的可怕瞳仁在慢慢的收缩,变的萎靡不振,整个身体也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的垂落到地上。盈姐一手捂着自己脖子上的伤口,一手取掉了她手里握着的那块玻璃片,急道:“快,快点把她绑起来。”话音刚落,英子从地上又蹦了起来,一张脸涨的血一样的红,眼神是春色无边的,如同被千万只蚂蚁附满她的身体,让她疯狂的双手迫不及待的摩搓她每一寸如火烧一样充满欲望的肌肤。那疯狂、那冲动、那强烈的爆发、那不可压制的需求,又一个可怜的女人。我闭了眼睛。
自然,她没有翕张着嘴唇到乞求渴望得到解脱的地步,她没有变成一匹狼。那两个男人,抱着她去了旁边的一间房,接着,就是那不可压制的释放出的满足的声音。
我和张柏兰一句话没说,什么事也没做,从酒吧里偷偷的遛了出来。我大口的喘气,莫名的悲哀,只有迎风奔跑,冲刷着我全身的疲惫和杂乱的思想。
两天后。
我和张柏兰还是去了舞棚酒友快活居。她永远像个影子,一进门就隐身术一样不见了。我还是去吧台先叫了杯啤酒,下意识看了看两天前来这的时候坐的那个位置,有人了,一个女的,说不上漂亮却也生的丰满,谈不上妙龄还算年轻的这么一个女人。她双手叠在吧台上,俯着身子看着面前的一杯啤酒正出神,我看她很认真的发着愁,想必也是在揣摩那一醉解千愁和借酒消愁愁更愁哪个对哪个错吧?
“你好。”我挪到了她旁边。
她看了看我,说:“不好。”
我问:“失恋了?”
她惨淡的笑了笑,说:“我做鸡的。”
我莫名其妙的‘哦’了一声,又莫名其妙的问了一句:“生意不好?”
她叹了口气,像是遇见了知音人一般,一手搭上我的肩头,诚诚恳恳的说:“不容易呀!我们这一行竞争性也是蛮大的,长相稍微逊一点,年龄稍微大一点就马上会被淘汰掉。这不,昨天又新来了一批,个个花枝招展的,唉——”接下来她就是一声比一声重一声比一声幽长的叹息。
我举起酒杯,往她酒杯上碰了碰,说:“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喝他个痛快!”
她煞有介事的摇了摇头,说:“你也知道,我这可是卖肉钱呐!”接着又是一声长叹,说:“今非昔比了,换了两年前,几杯酒钱我是断不会放在眼里的。”她捧着酒杯凑着嘴呷了一口,一脸豪爽说:“既然你有这个心,要我陪你喝个痛快,我也就不能扫了你的兴,这次你请了,我舍命陪你喝。”她一仰脖子,一口饮尽了。我看她喝的太猛,酒或许还没下肚,就对那吧台里的服务生吆喝了起来。
我趁她喝的兴起的时候,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很久没生意可做了?”她脸红脖子粗的也不知道喝了多少,不过我敢保证今儿这一晚上别的要进洗手间的朋友可要憋死了。她憨憨的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连笑的力气都没了,看她这阵仗,像个酒疯子一年半载没碰过酒一样,比那刚从牢房里放出来的犯人见了肉还要厉害。我摸了摸口袋,这次是要大放血了。她不停的叫着干杯,我没有敢跟她碰杯,更没有敢跟她干杯,生怕被她莫名其妙的劫了财呆会还要被莫名其妙的劫了色去。
张柏兰来叫我,临走时我还没忘很真切的对她说一句生意兴隆。为了自己以后别再碰到这样的糗事,我也祝所有的妓女们个个生意兴隆,个个都能做金鸡,财源滚滚。
“她,谁呀?”张柏兰问。
“一个朋友。”我随口敷衍说,又怕她追问,忙问:“上次那女的找到没有?那基地和冰工厂的事具体查的怎么样了?”
她神秘的笑了笑,说:“你猜我怎么要她说出来的?”她在我面前摊开了手掌,上面是写着卖药人的地址,还有几句乱七八糟的暗语。我说:“要是我出马,也可以叫她开口的。”她轻蔑的笑,说:“你就是牺牲色相也难让她告诉你,我这一手可是部队里秘传的催眠术,百试不爽。”我故作惊惶道:“少女情怀总是春,你不会什么时候对我催眠,强暴我吧?”她一拳向我捣来,说:“这催眠只对意志力很薄弱的人才管用的。”我笑着跑开了,大声道:“不是百事不爽的吗……”
一条胡同。
一所复古式建筑的宅院,门前站了一个女人。远远的,便闻到一股比狐骚味还恶心的恶臭,我料定是那个女人身